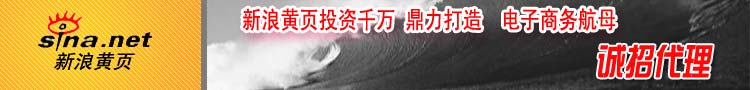
|
|
|
|
|
个人权利是公共物品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06日 01:03 21世纪经济报道
刘晖 为什么历史中很多变故并不是由最绝对贫困者引发,而是那些看起来得到不少利益的群体?对此,世界银行进行了一个名为“最后通牒游戏”的测试。 最后通牒游戏由提议者与响应者组成,前者负责分配,比如说分配一笔1万元的现金,后者可以接受或者拒绝。如果接受,分配方案按提议者施行,如果拒绝,游戏结束,双方谁都不能拿到任何一分钱。 按照理性人和经济人的假定,唯一的均衡只可能如此发生:无论提议者将怎样小的份额分配给响应者,他都应该接受,否则他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在无论是在哪种文化环境中测验,这个结果几乎没有发生。而最可能被后者接受的区间,是提议者建议分配的比例在41%到60%之间。 “对公平的根本性偏好深深根植于人类的选择当中”,《世界发展报告》如此写道。人们愿意什么也得不到,也不愿意放弃机会均等和程序公平。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则将问题推进了一步,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有助于保障这种“平等”(或者较少的不平等)? 规则的理由与成本 如何才算“公正的行为”?比如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行为算不算公正?按照布坎南的解释,公正的行为就是不违反已事先表示同意规则的行为。在这里,同意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不管是明示还是隐含,规则的合法性置于首位。此后,才有可能进行“同意的计算”。 根据如此推理,布坎南不会同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行为,因为这其实剥夺了他人的应得之物,就像一个裁判把冠军没有判给跑得最快的人而是他人,无论他是胡来,还是考虑到种族、肤色等另外因素。 如果应得之物还属于公众内心所固有的观念,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间,优先的顺序是什么,其间会隐藏着什么样的悖论? 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首要的任务是做大蛋糕,因为蛋糕不够大,或者甚至是没有,谈不上任何分配正义。问题是,在做大蛋糕的时候,是不是会侵害他人的份额,就像我们常说,总有人要去承担阵痛或者成本,但是承担成本的人应该如何得到补偿?另外,分配这种行为本身的成本是多大?会不会发生为了做一个蛋糕,打碎了太多的鸡蛋? 布坎南还列举了一个分蛋糕的模型,比如说,在对蛋糕提出要求的A和B之外,还有一个有分配权的C。假定把C界定为和前两者一样,都对蛋糕有着相互冲突的要求,那么最大可能是,他会将整个蛋糕据为己有。如果假定C能够在善心准许的范围内对A和B进行转移支付,那么处理公正和效率这个冲突将成为关键。就单方面分配结果选择而言,任何有关此类问题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分配者存在着道德风险。当然,批评者会提出,授予代理人支配的权力,并不等于无条件地授权给他们把收入进行任意支付。那么,约束何在? 其实,这时的约束已经不是经济上或者蛋糕尺寸上的硬约束,而是博弈规则上的约束,是这些规则决定着转移支付的规模或者方式。因此,布坎南的结论是,无论是守夜人式的“最小国家”的制度安排,还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都意味着会产生符合不同分配要求的格局。 布坎南还设想了这样一个案例:政府对某一个产业进入实行管制,从而导致特定群体的收入变化。而假定过了一段时间后,政府取消了这些保护性的管制,但是蒙受损失的人未必是以前从牌照中蒙受收益的人。结果,无论是当初的实行管制,包括此后的取消管制,都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 因此,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无论是归因外部性,还是私人产品的垄断因素,都不足以构成强制性实行市场干预的理由。而在立宪原则下的制度安排,不仅可以保持元规则的基石作用,而且具有实现“帕累托改善”的可能。 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定价 有市场,就有赢家和输家,如果能保证机会均等和程序公平,愿赌服输。当然,对于绝对贫困者,政府不能卸责。问题是,对于像教育、医疗和住房这样公共性很强的物品,就没有那样简单。这几类物品固然还具有差别消费等级,有的(比如说住房)还具有投资属性,但是对于一个公民,它们共同的特性是基本福利。有其教,有所养,居者有其屋,这些话都说明,这是分配正义的底线。 这一点,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早有说明,其间的道理并不晦涩。市场存在着相当一类的物品,比如说盐,盐价贵,也不能不食,就像人有病,不能不医。盐价便宜,也不能多食,有事没事多吃它几公斤。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就像殡仪馆,人之将死,不能因为价贵,等上那么些天,等便宜了再死。学龄儿童到了入学年纪,自然应该受到教育。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当如此。 公民享受教育、健康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是生存的最基本的尊严。至于生活得是否体面,那要交给市场。公民的生存需要必须运用公共资源来满足,它是对风险厌恶的社会偏好的反应,是从天赋人权这个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底线公正和底线伦理。 按照阿玛蒂亚·森的社会公正观点,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自由展开的。人类发展不光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自由的发展,这既包括工具性自由,又包括实质性自由。关于实质性自由,森引入了“可行能力”(capability)这个基础概念。一个人的可行能力也是一种自由,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的可行能力或实质自由的提升。 在实证研究中,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公共性支出越高,越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增长变为发展。尤其是需要提及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未必意味着全是政府生产,政府具有某些方面的供给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监管责任。许多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比如说国防,是因为政府支付的成本最低。而在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像铁路等服务已经变成私人企业,政府主要是实行监管责任。 说到铁路,春运将至,对于中国人,春节回家,有些像吃盐一样。而对于铁路部门,平时的运力不能储存,因此高峰期间曾希望以提高价格来熨平需求。研究表明,对于这类刚性需求,即使是价格提高到市场出清水平,依然存在着套利机会,涨价解决不了倒票行为,价格区间越大,套利的空间越大,反而还会产生福利扭曲。对于很多低收入者来讲,无座位或者硬座的车票,对其是基础福利,不宜涨价。 “关于增长,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但是对于发展,我们却知之甚少”,卢卡斯这句感叹,在今日今时的中国,显得意味深长。
【发表评论】
|
精彩专题频道精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