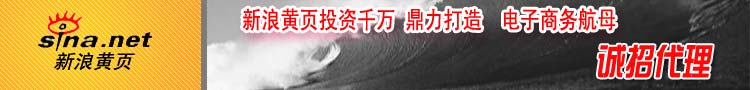
|
|
|
|
|
杜聪:要尽量维护受助人的尊严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23日 15:41 新浪财经
 2006年9月23日,国学传统与现代文明——第三届世界华人精英会深圳论坛在深圳观澜盛大举行。新浪财经独家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以下为香港智行基金会发起人杜聪先生发言: 杜聪:90年代的时候在华中地区很多的农民因为贫穷去卖血,因为不卫生的采血办法,很多人感染了爱滋病,经过现在好几年现在都很多已经死亡了,留下来一大批的孩子,变成的孤儿。 问题非常严重,在一些爱滋病高发区,在常年人口里面达到40%以上,这是一个村里40%以上的常年人口要么感染的爱滋病,要么因为爱滋病死亡。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蓝色的区域,(PPT),根据联合国的报道,1998年他们关闭了地下的血站,充公了288包血液,抽样调查了100包的样本,其中发觉99包都是有问题的。在好几年前我曾经去过几个贫穷的农村,我去访问了很多的家庭,这是其中之一,我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母亲因为爱滋病死亡了,只剩下一个大女儿,还有母亲和他的儿子。这个母亲见到我的时候,说你快救救我的儿子吧,但是他的儿子也感染的爱滋病,很快就要死亡了,我们去了之后他就死亡了。我觉得很难受,因为我以为这样的人间苦难,这样的场景我只是在一些非洲的图片里面看过,没想过在离北京几个小时路程的地方也会这样的苦难,我跟他母亲说,“也许我来晚了,我不能为你的儿子做什么,但是我要确保你的女儿有一个读书的机会。”也就是我们这几年工作的精神,希望能把受爱滋病影响的孩子,给他们一个读书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捱过这个灾难。 过了几个月以后,我回去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女孩子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得到我们的帮助可以读书,这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在学校的照片。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间的苦难,如果你想想,祖宗三代人都是在经历他们最惨的一个局面,从爷爷奶奶这一辈人有什么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惨,我认识的这些爷爷奶奶生了5、6个孩子,都一个个死亡,当你要安享晚年的时候,你要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个死亡,而且要重新沿成父母,要照顾你的孙子孙女。作为中间这一代人有什么可以比得了爱滋病更惨?在你风华正茂的时候得了绝症,而且死得没有尊严,没有足够药物的治疗,而且我觉得最惨他们不安心,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尽父母的责任,留下来还没有成年的子女变成了孤儿,为他们的前途而担心。 作为孩子有什么可以比变成孤儿更惨?在你年纪很小的时候缺乏父母的关爱,变成孤儿,没有教育的机会,没有营养。还要因为爱滋病变成孤儿受到很多邻居同学的歧视。 这位奶奶有4个儿子,4个媳妇,中间这一代有8个人,8个里面7个感染了爱滋病,已经死了6个,几乎整个中间这一代人被毁掉了,所以就剩下4个孙子给爷爷奶奶去照顾。 我很敬佩这些孩子,因为他们不仅仅需要负担起做家务,做很多体力的劳动,要照顾病床上的父母,要做饭,还要去上学。他们还要承担一个很重的精神的负担,因为他们要眼睁睁地很无助地看见自己父母的死亡,我们一般人可能要到4、50岁才要经过送父母最后一程这个人生很重要的阶段,但是很多人到了4、50岁还是受不了这个打击,但是这些孩子10、8岁就要经过这个阶段,我肯定他们会有很多的心理阴影。 我强调无助,是因为如果我们的父母生病我们可以送他们去一个好的 医院,煲汤给他们喝,不一定让他们好过一点,让我们好过一点,因为我们尽了自己做子女的责任了,而这些孩子很无助,所以看见他们很有内疚的感觉。如何地救助 ,智行基金会98年创办的,97年的时候我去过西藏旅行,我很欣赏导游说西藏的用两件法器,一个代表智慧,一个代表慈悲,在培训和尚的时候,藏传佛教都要培训这两个人生的部分。我很欣赏这个部分,因为如果我们只有智慧,没有慈悲的心就不会去帮助别人,也不会人间有情。但如果我们只有慈悲没有智慧,也不能很有效率地去帮助别人。如果我只有慈悲,我只有天天抱着孩子哭,在爱滋村里面也救助不了他们。所以我们慈善的工作也要结合这两者。 我想想,其实西方社会跟中国社会有很多慈善方面的工作是很类似的,也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比如说社会里面很大部分的资源跟慈善的目的都是放在教育、健康、卫生、儿童的发展,还有解决贫穷的问题上面。这几个月我们有看见克林顿总统,比尔盖茨等等,他们都是集中在这几个领域里面。但是差异还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差异我等一下最后会说,可能并不一定是东西方社会的一个差异,只是我们在经过一个不同程度的社会的发展,如果你看美国社会,1920年代的时候,慈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跟现在中国可能分别没有很大,但是也是经济社会很多方面都冒起一些很有钱的人,领先成立了几个大型的基金会,还有社会里面也做了很多法律各方面公民社会的配套。 在这之前可能教会发挥了很多慈善方面的作用,但是民间非宗教方面的慈善社会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以为今天会有胡润的慈善榜的分享,所以我就没有把这些数据放在里面,他做了很详细的分析,中国的国民总产值是多少用于作慈善的,中国登记的多少商业里面多少个曾经捐过县,都发掘中国的慈善捐献确实比很多其他的国家要低,无论是公司的比例,或者是总数的金额。但是,这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不一定是跟关于老百姓的传统捐献的精神。 还有一个差别,可能现在中国的法律跟会计 审计的要求还没有达到一个高的门槛的水平,这也导致了很多人不捐献的一个缺乏信心。因为在一些外国的国家,如果你捐一百块人民币,捐几十块人民币,监管跟申报都非常地严谨,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是香港注册的慈善机构,有一次我们在街头作为一个公募,结果筹了七千多块钱港币。因为香港的法律规定,我们做公募一定要再找一个会计师和审计师去审计,专门为这个公募的活动做一个审计,审计的结果也要在一份中文报纸,一份英文报纸里面刊登广告。结果我们花了三千多块钱满足政府的要求,但是我们只募了七千多块。你可以说政府这样说让老百姓浪费资源,但是只有这样严谨的社会规定,老百姓才会对慈善机构放心。因为捐赠一百块钱的老百姓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审查,但是如果政府有一个很严谨的要求,每一个捐一百块钱的人,或者是捐一百万的人都会对这个制度有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西方国家很多的捐献跟税务的安排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税务很重的地方,免税的捐献对企业和个人来说确实是很大的吸引。西方的慈善组织可能有很多是有宗教背景,还有很大的宗教的原动力在后面,这可能在中国,慈善机构没有一个意图,我做善事,我来帮助,人你信教,这个可能很少。 而且在西方国家,可能喜欢高姿态地捐赠的人和机构都很多,他们作为一个个人的宣传也好,作为一个企业的宣传也好,都是很普遍的。这也没有什么道德的批判,我觉得他们反正做了好事,捐了钱也应该让人知道的。但是在中国,我跟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交流,如果要做善事,都希望比较低调。他们有几个考虑,可能是他们个人财产的一个隐私的问题,也可能他们担心,我捐了给你,有一百个团体就来找我了,以为我捐钱,以为我有钱,所以他们不想很高姿态做这个工作,跟外国有一些分别。 刚才也说到慈善机构的问责和透明度的公开,因为法律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我不排除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会有人拿着老百姓对某一个领域,比方说爱滋孤儿的同情而去非法敛财,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制度的不健全。这还是害了整个领域,因为有一些好的组织,有一些不好的组织,因为缺乏监管,有不好的组织浑水摸鱼,我们监管部了,导致老百姓捐赠人对整个领域失去了信心。 还有在外国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的,就是一个平体,以前慈善机构都是各自为政,现在有一些慈善机构的监管平台是民间的,跟政府脱离的,是纯自愿性加入的,很多人把这个跟商业界的中华总商会、英国人商会,或者是一个股票市场的概念一样,既然私人公司要有一个股票市场做一个平台,英国人在大陆的公司要有一个英国商会做平台,为什么慈善机构就没有这样的平台?现在在西方国家这也是非常普遍的,他们也用他们客观统一的标准去评估他们会员的可行性、透明度,还有他们工作有没有效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 刚才提到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捐赠,和相关的基金,这里面有几点跟我们中国很相近的,我们以为不会发生的,原来是这样的。比如说WarrenBuffett他有三千多亿的人民币,他愿意把85%捐赠出去,他本身有自己的基金会,他把八成的钱捐给全世界唯一比他更有钱的人所创办的基金会,而不是壮大自己的基金会。他的意思是既然有人成立了那么完善的一个架构,一个体制,我没有必要重复这个架构,我把钱捐给他,让他管理就好了。我觉得这是很聪明很伟大的一个做法,WarrenBuffett是一个很成功的投资人,他这样的决定,他做善事宁愿不用自己的名字名留青史,而把钱给了一个比他更有钱的人帮他做善事。 他都有子女,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成立的基金会,他们都得到一部分的他的财产,但是远远都不够比尔盖茨基金会那么多,比尔盖茨基金会是一千万股,他跟他太太的是一百万股,他的子女是32万股,这跟一千万股是差很多倍的。他不是把自己的财产全部转换成现金捐给他,因为他说几千亿的财产一下子用不完的,我宁愿以股票的形式每年捐赠我5%的股票给你的,你用当时的价值来兑换。因为他心理面有一个把握,在我的基金里面的投资,每年回报会超过5%,所以我把钱捐给你,一年之后剩下的95%,经过我的投资,那个总值又会恢复到一个水平。我再又捐5%给你,这样他的财富就可以滚动地来做善事。 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对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捐赠,在一个西方国家居然都会有的条件,就是比尔盖茨跟他太太两个人之中,其中有一个要在生,没有死亡,而且活跃在那个基金会的行政里面,他才会继续地捐赠。所以我们现在都要向天保佑比尔盖茨两夫妇,现在他们经常去非洲谈一些项目,坐一些小型的飞机,他们两个不要死掉,如果他们死掉WarrenBuffett的钱就会再捐给他们的基金会了。很多人很惊讶,因为比尔盖茨是一个目前全世界最大、管理最完善、人才最多的基金会之一,我们一般人正常的逻辑都会觉得,如果比尔盖茨死了以后这个基金会还会继续运作的,就好象他的微软公司一样,应该不会受到影响。我的基金会也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在他们的这个层次不会发生,有捐助人指定,我继续支持你的工作,但是你要继续在这个基金会里做主席,如果你离开了我就不再捐钱了,因为我相信你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好,换了其他人我就不再捐赠了。 这我们的小的基金会里面可以理解的,人的因素很大,但是在他的基金会居然会发生同样的事件,而且要求这个条件的人是全世界被誉为最精明的投资人,他是赚最多钱来投资的一个人,居然也会这样要求,这有一个讯息,哪怕是一个管理得很完善,很大的基金会,作为全世界被誉为最聪明的投资人眼光里面,你老板走了,我对这个几个会没有信心了。所以,在西方还是一个人智的因素成份非常重要。 过去十年特别是美国,还有很多联合国的机构,都有一个趋势,就是非常以结果为目标,就是以前做善事,现在中国也属于这个阶段,没有人做很多对善事的有没有效率的评估,只是你做了善事就好了。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看见西方越来越要求有硬指标的善事,你救助了多少个人,你帮了他们具体什么。而且定量地,可以量化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一个虚拟的,说我帮了什么,具体怎么帮,有没有数据,有没有分析,越来越要求有这样的一个量化的结果。 我觉得跟商业机构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过去十年在慈善领域里面捐钱的人很多都是商界的人士,他们很重视结果,所以包括比尔盖茨他带领的基金会,都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指标,项目定期要做评估,如果达不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钱花得有没有效果,这是一个很大的商业界的推动。 我以下举几个例子,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走的,但是这个方向还是不足够的,这个方法也还是不完美的,但总比没有。比如我们在华中地区有三千多个学生,每个学期他们都来,这个月是我们第九个学期的开始,我们从四年前开始从一个省、一个县、一个村,到现在发展到四个省、七个县、50多个村,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都可以量化的。 受到我们帮助的孩子,从一个村的127个,到现在增长到3500个,这是硬指标,绝对可以量化,这个成绩我本人是非常骄傲的。 还有一个例子,这个孩子本身有爱滋病,后来通过我们的帮助,跟克林顿基金会的药物,还有我们的社区关爱,他活下来了,而且他的爱滋病也治好了,里面有好几十个本身有爱滋病的孩子,通过药物的帮助,还有我们社区的关爱,他们的免疫细胞的增长从去年刚开始平均80个有爱滋病的孩子平均从136增加到400多,这是几个月的增长,不能骗人的,很科学的一个指标,成绩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很多对慈善机构捐助的一些人,很大的要求,很希望看见的一些数据。 我们的成功也非常荣幸在去年这个时候总统克林顿亲自来了中国,他第一次到河南省,专程飞来探望我们的工作和孩子们。而且他带了一个CBS的主播,他们做了一个节目,这个孩子很健康的,有一个很明显的健康方面的变化。 可能中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是,当我们不断地追求、寻求硬指标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硬指标的服务是不是对我们的目标人群真的是最好的。 比方说,可以跟人说我们救助了300个孩子,但是把300个孩子放在孤儿院,跟300个孩子放在社区,让他们自己不同的学校读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数据是一样的,都是救助了300个孩子,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背后对孩子的影响,一是在孤儿院里面很多心理问题的长大,一是放在普通学校和跟一般没有心理问题的孩子长大,所以硬数据背后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你的目标人群是不是得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有一些机构现在不断地追求这个硬指标。这个怎么去平衡他的心理状态呢?我们觉得孤儿院好,但是有很长的时间。 我们的想法有两个方法救助孤儿,我们都不认同。一是建一间孤儿院,自己给爱滋病孤儿的学校,让他们在里面长大,好像监狱一样,很难去完成社会化的过程,我们觉得这个不好。 分散领养我们也缺乏一个社会工作者的监管机制,所以也不能很定期地做家访,两个都不是很好。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孩子在当地的社区里面成长,给多一些支援,让他们跟自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一起住,然后把他们放回以后的学校里面,让他们跟没有爱滋病的孩子一起长大,这样他们可以完全逃离爱滋病的阴影,不需要有标签。 这个孩子本来放在爱滋病的领养家庭里面,后来受到养母的虐待,后来我们把他放在一个寄宿学校里面,他们都不知道他是爱滋病孤儿,而且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死于爱滋病,而且可以得到一般孩子得到的教育,这是很好的方法。 但如果我们凭硬指标工作的话,忽略了如何救助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很多孩子有很多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通过画画做一些心理方面的辅道,让他们有一些疗伤的作用。还有我们鼓励他们写日记,把心里面的东西写出来,我们做成纪念册。 这是很难评估的,不能量化的一些东西,也是慈善新的趋势。在外国,十年八年不断盲目地追求硬指标,也有很多的慈善顾问也改变观点了,觉得我们不一定用硬指标评估,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得到目标人群的反馈,目标人群觉得生活有没有受到改善才是一个指标,并不是一个一定量化的指标。 我们的工作还加了一个,如何能在最高的程度底下维护我们帮助的人的尊严,我觉得也是一个我很重视的一个地方,你帮助人不能高高在上的去施舍人家,而是站在平等的角度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尽量维护他们的尊严,这不是一个硬指标,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这样的工作也需要评估,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评估,而且需要很多的技巧来评估。我举一个例子,还有几个工作,刚才我说的其中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希望直接能得到你帮助的人群的反馈,今年我很高兴,因为在我们资助的八十几个大学生里面,他们有十六个今年暑假愿意回来帮我们回来做暑期工作,他们的任务就是回去他们自己的家乡,去做家访,跟他们同一个村的中小学生也是爱滋病孤儿,受爱滋病影响的孩子,家家户户地去发营养品,去发文具,同时给他们很多的鼓励,要他们好好读书,不要放弃他们的人生。 我们的雇员每天都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做毕竟是外面人的,孩子会觉得,“哎,你们外面的人没有经过我的穷,没有经过我的痛苦,不会了解我,你是大学生,你是城里面的人,不了解我。”但是如果我们动员一个他的邻居,也是爱滋病孤儿,回去说“不要放弃,你看我,我父母也是因为爱滋病死亡的,我就住在一个村,我是你的邻居,我们一起长大的。现在我考上大学了,有一个智行基金会供我读书,你也不要放弃,你也可以的。”这样的效果跟说服力就很强了。 所以我们尽量让他们能救助其他小的朋友,而且他们可以直接给我们反馈他们的工作,孩子的需要,我觉得这个不但是单方面的我们直接帮助这些孩子,而且受助人跟捐助人可以由一个很好的互动。 我们开学的时候高耀洁老师也来跟孩子讲课,我们家家户户动员孩子们去发礼品,我真的觉得经过四年以后,这些孩子都慢慢长大了。这是我们制作了一些幻灯,有一些考到国家的奖学金技术研究院。如果我们没有供他念大学,他可能念完中学出来工作,现在我们帮他捱过了大学这一关,他们就很争气,考到全免的国家的奖学金。很多时候,人就是差一点点。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难关,如果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有人帮我们一点点,我们捱过这个难关,可能我们的命运,我们的路就完全不同了。 里面有一个念法律的,有两个是念医学的,他们未来都会是社会很好的人才。如果我们社会人士不帮助他们的话,他们不能读大学,不但是对他们命运的一个浪费,一个糟蹋,也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资源的糟蹋。因为我们有一些很有潜力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人,就是因为没有钱,没有机会就浪费了他们的才华,到最后损失的还是国家。 这是我前两天去哈佛演讲,我遇到一个老师,他是在中南美国家海地,也是跟华中地区很相近的条件,病发率很高,但是农村很穷的地方,他要发爱滋病抗病毒的药,但是医疗性很低,农民的教育很低,如果找医生做很难做,所以他想起了动员农民家家户户去跑,督导他们吃药,而且给他们很多的鼓励和爱心。结果我回来中国以后把这个概念跟当地的防御站一起商量,做了一个村的试点,效果非常高,刚开始的时候46个病号吃药,但是后来过了几个月变成了90几个人吃药,而且都吃得更好。当时吴仪副总理去了那个地方,听见了当地的官员汇报,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她觉得要全面地铺开,政府接手了,从一个村变成24个村,都用同样的办法来做这个模式。 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钱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站在最前线,我们对当地的情况最了解,而且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创新的工作出来,给政府看。因为政府可能有资源,有钱,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没有最前线的一些反馈。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好的成功的工作出来,有领导来看,觉得可以了,他来铺开,这个影响力受惠的人士更大的,我觉得这是民间慈善团体可以发挥很多的领域。 我经常用这个比例,中国是一个500个单位的毛坯房,多层公寓,我们是一个 装修公司,我们的资源有限,但是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个单位装修得很漂亮,作为一个样板,我们把这个样板做好了带吴仪去看,她说这样很好啊,我们500个单位全部铺开用这个方法去做。她有钱,她有毛坯房,可能没有想过原来可以这样装修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最终得受惠的不是一个单位,而是500个单位。我要说一点,现有一些慈善团体太过努力地做这个单位,太豪华了变成一个皇宫,用的是进口的水龙头和家具,但是带吴仪看了以后非常好,但是铺不开啊,只是这个单位的人受惠了。这要引起我们的思考。 最后一个领域是企业的社会也是在西方国家这几年增长非常快,在中国现在慢慢悠人知道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捐钱那么简单。如果看第一个,传统的商业机构做善事,就是一个捐助人把钱给了慈善机构,慈善机构把钱花在受惠人身上。比方说某某人给了智行基金会一百块,我们用这一百块帮一个孤儿助学,这是最简单,最传统的模式。 但是现在有一些企业的参与,他们的参与非常创新,而且要面临一个更复杂更大提升的可行的工作,比方使捐助的机构或者是捐助人可以捐钱或者捐一些资源给慈善机构,慈善机构也可以帮助受惠的人,但是受惠人可以由更大的互动,不但跟慈善机构有互动,而且跟捐助机构有互动,捐助机构可以把他的企业文化和就业都提供给这些人。 我举一个例子,某一个公司可以除了捐钱给我们之外,渣打银行除了捐钱之外,我们暑假的时候有一些孤儿的夏令营在中国不同地区举行,他把孩子领到自己的银行里面,跟他们介绍他的业务。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去一个大城市的银行确实是一个可以大开眼界的机会,而且他们都介绍银行的工作,也许有一天,他会提供工作的机会给这些孩子。把他们企业的文化告诉这些孩子。所以,并不是单方的帮忙,而是双方的帮忙。 而且企业也可以动员他的员工,培养员工服务社会的精神。渣打银行的员工也陪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动物园、去科技馆、艺术馆、博物馆,也体现了一个企业员工的互助关心社会的精神。这个远比写一张支票给慈善机构有利。而且也带动了整个社会很多人参与这个事业,不但是钱,而且动员了员工,现在有好几个企业把一些18岁以上的孤儿雇佣,给他们一个就业的机会,而且有一些在工作里面字得不错。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我们跟酒店和一个豪华的度假村,跟美国运通旅行社,港龙航空和旅行社一起搞的活动,他们没有捐钱,他们只是捐最优良的服务,他们把房间和旅行的服务捐给我们,我们重新包装,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邀请我们捐助人一起参与的一个旅行筹款的募集活动。里面还有很多商业方面的考虑。 很多人认为大企业才能参与这个活动,其实中小型的企业也可以参与,除了金钱以外,可以是一些服务跟产品是作为一个捐赠的途径,而且产品的捐赠也是远远比写一张捐赠的支票要好。我们现在跟一个做玻璃的很有名的生产商去谈,去做一件专门为爱滋病孤儿琉璃的产品,可能到最后,捐赠的钱跟他写一张支票给我们差不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产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而且买这个产品的人感觉到我为孤儿做了事了,而且他买了这个产品,把这个琉璃的产品送给他心爱的那个人,那个人也是变成这个善业的一部分了,可以动员社会上更多的人去关心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并不是离西方或者对慈善有很大发展的国家很远,其实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小型的非政府组织的贸企,可能因为法律的规定不能变成一个合法的慈善机构,但却是亿一个非政府组织,但是用合法的方式去生存。我觉得现在的条件除了政府的法律层面没有很大的规定,让一些组织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组织浑水摸鱼之外,还有一点,这些组织很多都是以一个人的个人魅力来做起来的,而且有一些可能很幸运能变成一个中小型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如果要把这些以个人魅力吸引到一群人的,特别是在环保领域里面特别多,或者一些维权,有一个律师,一个环保人士等等组成的这些小组,要他们变成一个规模更大,更能延续发展的一个慈善机构,我觉得有一个很长的路。这在商业街也有的,一个中小型的企业,我是一个餐厅老板,我弄的北京烤鸭很好吃,但是我只是一个店,但如果现在要铺开,我要开分店要做连锁了,就出现很多管理上的问题。 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厨师,你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人,但是你能不能把你的善业就好象一个商业的模式一样,发展到一个更大规模可延续的机构。我觉得中国的政策改不改,也是现在很多非政府组织面临的一个门槛,他们自己要过渡和发展的问题。香港台湾也经过这样的时期,有一位商人也是几十年前从一个人开始,香港也有一些组织是几个人发起的,但是经过几十年变成一个很大规模的慈善组织,我觉得也是一个发展的必要阶段。 感谢大家!
【发表评论】
|
精彩专题频道精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