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冯明
储蓄过剩和投资需求相对不足、社会财富规模庞大和财富所能附着的媒介投资品相对不足成为中国金融行业面临的基本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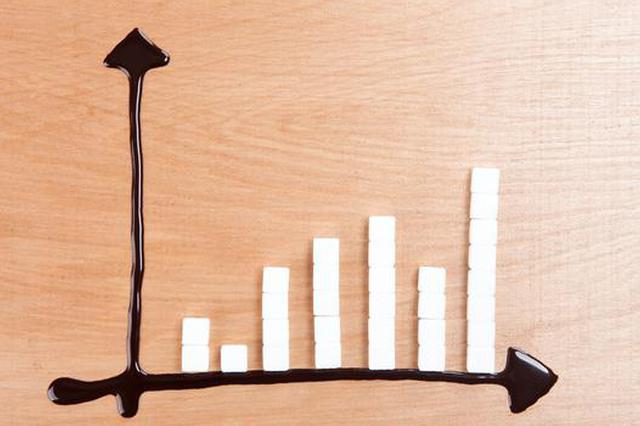 冯明:如何管理大规模的社会财富
冯明:如何管理大规模的社会财富中国金融行业面临的基本矛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中国曾经长期是一个储蓄不足的经济体,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之后数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储蓄相对过剩的经济体。储蓄过剩和投资需求相对不足、社会财富规模庞大和财富所能附着的媒介投资品相对不足成为中国金融行业面临的基本矛盾。特别是“四万亿”之后,这种格局性变化更为凸显。
金融是连接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之间的桥梁。基本矛盾的演变导致实体经济对金融业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型。原有的金融服务供给与新经济环境、新经济结构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中国金融业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管理和分配如此巨大规模的社会储蓄和社会财富。这既是中国金融业的挑战,也是中国经济的挑战。该挑战既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5年和2016年高达8.35%和8.5%,超过美国、日本等通常意义上金融业先进的发达国家。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过度了,提出应当抑制金融发展。但实际上,8.5%的高占比只是金融业“虚火”旺盛的表现。中国金融业不是发展过度了,而是发展不足、发展不良。“大而不强”这一曾经对中国制造业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金融业。当前真正应当担心的问题不是金融业占比过高、金融业过度发展,而是金融能力不足。中国应当大力加强金融能力建设,将其作为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一部分。只有加强供给侧的金融业能力建设,才能使得金融业适应于新经济环境和新经济结构,才能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解决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
(一)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基本矛盾在发生变化
从增量层面来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意义下的储蓄率曾经一度超过50%,现在仍在47%以上,高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年储蓄规模在3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些储蓄无非流向两个用途:一是净出口,也可以理解为对外储蓄。但是中国目前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高达14%,未来继续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二是国内投资,而国内很多传统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投资需求也有限。这是基本矛盾在增量层面的体现,简言之,可以概括为储蓄过剩和投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
从存量层面来看,截止2016年底,全国储蓄存款余额高到59.8万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将近30万亿元。根据招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6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量达到165万亿元之巨,是当年GDP的两倍多。另有测算显示房地产市值更是高达约300万亿元,约为当年GDP的四倍。如此巨大规模的社会财富都要找到相对应、可附着的媒介资产;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中缺乏足够的媒介资产可供这些财富去附着。所以在过去几年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量的资金苦于找不到投资机会、找不到可附着的媒介投资品,追着投资机会和产品“东奔西跑”,除了造成房价快速攀升、股票债券价格大牛大熊之外,大蒜、生姜、糖等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品也被当成投资品去“炒”。这是基本矛盾在存量层面的表现,简言之,可以概括为巨大财富规模与财富所能附着的媒介投资品不足的矛盾。
(二)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结构在转型
在微观层面,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条件下的资源跨时空配置。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下,金融的本质是连接储蓄和投资的桥梁。在储蓄和投资决策不分家的时代是不需要金融的。比如在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储蓄决策同时也就是他的投资决策——今年打了1000斤粮食,当年吃掉950斤,留下50斤种到地里明年吃,那50斤既是这个家庭的储蓄,也是他的投资。但进入现代经济之后,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越来越分离,所以对金融需求也越来越大。
储蓄决策的本质是居民对消费进行跨期平滑。所有的储蓄都一定要附着在某种媒介之上,以便未来能兑现为消费。被附着的媒介可能是纸币、存款、股票、债券,也可能是房产、黄金、白银、煤炭,抑或是比特币、大蒜、红酒、字画等等。问题在于,当储蓄规模过大时,经济中就会缺乏足够多的媒介可供附着。尽管理论上货币和存款可以无限增加,但是,货币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存款过多了银行不一定能找到相应的优质贷款投向,房子建多了房价可能会跌,“蒜你狠”曾经一地鸡毛,红酒字画等另类投资品毕竟规模有限,金银等贵金属的价值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受到挑战……
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下,投资是企业和家庭增加生产性资本存量的过程。例如企业扩建厂房、更新机器设备,目的是生产更多或者更新的产品。再比如家庭购买房产,因为房子在未来可以“产出”住房服务。投资行为取决于边际资本产出、需求、以及资本折旧率等因素。需要澄清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的“投资股票”或“投资理财产品”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下实际上是储蓄行为,而非投资行为。
既然金融是连接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之间的桥梁,那么金融业务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于储蓄行为的金融业务,一类是服务于投资行为的金融业务。
在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面临储蓄不足、投资需求旺盛的基本矛盾,中国经济对金融的核心需求是: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储蓄、集中社会资源,然后利用这些储蓄资源去搞建设。而当前,在基本矛盾转化为储蓄过剩、投资需求相对不足的时候,中国经济对金融行业的需求则更多转向如何管理巨量社会财富,如何高效地配置储蓄资源,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投资。以前是项目等钱,资金来源是制约,为项目融资是金融业的关键着力之处;现在是钱追着项目跑,优质项目和投资机会是制约,理财成为边际激增的金融需求。
换言之,中国金融业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管理和分配如此巨大规模的社会储蓄和社会财富。这既是中国金融业的挑战,也是中国经济的挑战。不论横向来看,还是纵向来看,该挑战都是艰巨的。纵向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中都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储蓄和社会财富需要被管理过;横向来比,我国现在的储蓄规模也明显大于其他国家。所以说,这个挑战既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三)中国金融业发展不足,而非发展过度
2017年3月中旬以来,一行三会监管新政密集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增速考核。银监会连发7份文件,部署针对商业银行“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的全行业大检查。证监会收紧基金子公司设立门槛,提出资管业务的“八条底线”,完善保本基金风控指标和监管要求。保监会发文要求各保险公司清理规范通道类业务,防范监管套利,严格保险资金运用,并对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提出八大禁止情形。
金融监管风暴成为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一大主题词。与此同时,金融监管引发广谱利率上行,短期内对金融市场带来紧缩效应,也导致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抬升。一时间,对金融行业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如金融空转、资金脱实向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等。
毋庸讳言,这些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存在一定的现象作为基础。但是,面对这些批评,我们首先需要思考:这些问题真的是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过度造成的吗?还是金融背后或者金融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
不妨试想,如果没有2011年之后私募、理财、信托等影子银行体系的兴起,中国经济的储蓄-投资传导机制会更顺畅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会更高吗?如果今天商业银行贷款仍像过去一样占到社会融资规模的80%以上,那样的金融体系能够适应2013年之后宏观经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吗?能够服务于新经济动能的成长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恐怕只会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错配,导致更多的储蓄资源被浪费。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一个人每天吃过多的食物、又不运动,但并没有转化为肌肉、身高也没有长得更高,而是脂肪不断堆积、虚胖。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当然批评新陈代谢系统,职责它为什么不把食物转化为身高和肌肉,而是堆积成了脂肪、积聚高血压风险。但是这种批评意义不大,因为根本原因在于入口上吃得过多、而出口上不运动需求不足。事实上,他的新陈代谢系统比一般人负荷更大,更努力工作。就像中国的金融业一样。
当中国经济在进行剧烈结构转型的时候,实体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相应地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结构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抛开这一历史背景来批判金融业并不合理,容易造成舍本逐末的错位,甚至在政策制定上树错靶子。
金融创新过程中滋生了不少问题,比如通过加杠杆和期限错配积聚金融风险等。但金融永远是跟不确定性和风险相伴而生的,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就没有金融。真正应该担心的不是金融风险,而是金融业缺乏对风险定价的能力。
况且,没有金融创新,结果会更好吗?如何有效管理和配置海量社会储蓄和财富、将其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这是上述诸多批评的根源所在,但这一问题并非金融业造成的。恰恰相反,金融创新的过程整体上就是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如果没有金融创新,风险并不见得会下降,因为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只会更低。我们不应当把金融发展不足的结果当成是批评金融业、限制金融发展的理由。
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经高达8.5%,2016年为8.35%;比美国、日本等通常意义上金融业先进的发达国家还要高。这一数字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过度了,提出应当抑制金融发展。
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金融业不是发展过度,而是发展不足、发展不良。8.5%的高占比只是“虚火”旺盛的表现。“大而不强”这一曾经对中国制造业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金融业。当前真正应当担心的问题不是金融业占比过高、金融业过度发展,而是金融能力不足。中国应当大力加强金融能力建设,将其作为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四)加强金融能力建设,适应新经济环境和新经济结构
基本矛盾的变化导致中国经济对金融业的需求结构在发生转型,原有的金融服务供给与新经济环境、新经济结构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这意味着,金融业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适用于新经济环境和新经济结构的金融能力建设,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解决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
关于供给过剩时代亟需加强的金融能力建设,下面举三个例子。
(1)加强新经济资本化的能力
一个经济体中最优质的、成规模的投资品,往往来自于其新兴行业。比如说90年代中期房改之后的房地产,以及房地产企业、家电企业的股票;再比如2003年之后互联网行业和2012年之后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对于前者,房地产的确成为了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年里最重要的投资品之一和规模最大的财富附着物;但需要说明的是房子天然具有投资品属性,其资本化过程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很低。
而对于后者,尽管互联网革命如巨浪袭来,带来生产和生活的根本性变革,中国也幸运地走在互联网革命浪潮的前列,诞生了很多优质的企业。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欠缺和金融能力的不足,大量的优质互联网企业的资本化并非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以中国互联网行业的“BATJ”四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为例,无一例外,都不是在中国本土上市的。其中,腾讯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阿里巴巴、百度和京东分别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上市。以“BATJ”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是中国经济新动能的代表,也是中国经济最优质的资产,但却“肥水流到外人田”,大部分国内居民无缘投资。
虽然理论上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作为金融能力的替代——只要资本账户开放,国内居民就可以通过资金跨境流动的形式投资于海外上市的优质中国资产。但对于中国这样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而言,寄希望于通过开放资本项目来替代金融能力建设很可能是舍本求末、得不偿失。况且,在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健全、金融能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过快开放资本账户还容易导致投机资本跨境流动过于频繁、汇率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甚至引发金融危机等负面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于1980年代以来主流的倡导资本账户开放的思想提出的深刻反思,目前尚未有定论。
(2)加强国债市场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重塑宏观调控能力
在投资需求旺盛、资本相对稀缺的过去,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是较强的。主要依赖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等一系列需求侧管理工具。但在当前资本相对过剩、投资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原有需求侧管理工具的有效性受到影响,需要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审慎管理加以配合。另外,在储蓄和资本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会增加,更容易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形,更容易发生金融风险。这也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能力和中央银行监测、管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债市场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金融市场,是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而我国目前的国债市场规模还比较小,产品结构不够全,流动性有待加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分割。国债市场的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他层级金融产品的定价能力,并制约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调控的能力。
主要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大都是以基于国家信用为主导的。美国国债占美联储总资产的比例在次贷危机前为85%,尽管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由于三轮量化宽松(QE)期间购买了大量MBS资产有所下降,但是美联储总资产始终仍是以国债为主的“内部信用”为主的,“外部信用”所占比例不超过3%。相比之下,中国国债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总规模中的占比仅为4.5%,“外部信用”所占的比例在2014年底高达82.4%,2016年底仍将近67%。考虑到(1)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中国政府债务率低于上述几大经济体以及国际警戒线、(3)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的占比远高于一般国家,等因素,基础货币投放依赖于外部信用、国债在中国央行资产总规模中如此低的占比不能不引人反思。
过去两年间,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已经开始由基于外部信用转向基于商业银行信用。2014年底到2016年底,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券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由7.4%上升至24.7%。但这只是第一步,未来还应推进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向基于国家信用方向的转型。尽管除了个别民营银行之外,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都是国有银行或者是由国有资本最终控股的银行,具有“类国家信用”的属性;但是,商业银行信用仍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信用。商业银行的本质是公司制法人,理论上存在破产倒闭的风险。况且,基于商业银行信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会拉长信用传导链条、降低金融体系的效率。一些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以及广义基金(包括各类基金、企业年金、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等)开始扮演类似于中央银行的职能,向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发行”基础货币。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而言,其流动性来源不再单纯依赖于中央银行,而是开始依赖于大型商业银行和广义基金。大型商业银行和广义基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小型商业银行的“中央银行”。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1.0体系正在转向“中央银行+影子央行+商业银行+影子银行”的货币创造2.0体系。
(3)加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能力和引领国际金融市场预期的能力
在经常项目下,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经济体,资本项目的渐进开放也已列入中央政策日程、正在有序推进之中。中国每年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石油、铁矿石、铜、农产品,是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买方,但这些大宗商品几乎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且中国在定价博弈中并没有充分利用好作为最大买方的优势地位。这当然与具体产品门类的市场结构有关系,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能力不足的制约。
例如,由于国际市场上绝大部分大宗商品是美元定价的,因而不论是大宗商品的买方、卖方、还是金融投资者,都必须关注美元汇率的变化。而市场上受关注最多的美元指数——ICE美元指数[1]——却是以1973年美国对外贸易情况构建货币篮子的,仅在1999年因欧元区货币制度转变做过一次调整。ICE美元指数的篮子货币包括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6种货币,权重分别为欧元57.6%、日元13.6%、英镑11.9%、加拿大元9.1%、瑞典克朗4.2%、瑞士法郎3.6%,多年以来恒定不变。时至今日,ICE美元指数不仅在篮子币种选择上,还是在权重设定上,都已经无法客观、全面地反映后来美元币值的动态变化。但遗憾的是,正是这样一个创立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早已过时的“阑尾炎”指数,至今依然让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参与者不得不时刻密切关注、神经紧绷。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更合理的、时效性强的指标被推出、作为替代。
随着中国社会储蓄和总财富规模的增加、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程度的加、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加快构建能够反映全球经贸格局动态演变的“新美元指数”或者“人民币指数”等指标变量,供金融市场参考和使用。例如,可以考虑在上海市场、香港市场或者法兰克福和伦敦市场,推出相应的以新指数为标的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也是现代国家金融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1] 又称“美国洲际交易所美元指数”,ICE是美国洲际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的简称。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青年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