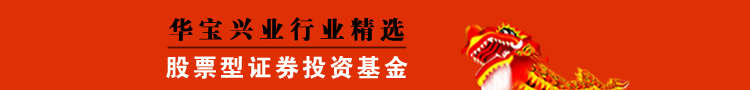 |
|
|
|
第一期:1977-改变命运的开端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8日 19:21 经济观察报
徐友渔 1977年9月,邓小平再一次恢复中央工作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 1977年是改变命运的开端,对国家是如此,对个人也是如此。 虽然严格说来,关键的变化发生在1976年的9月,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历史正在展开新的变化。但社会和思想的惰性是巨大的,“照既定方针办”和“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还是照旧。对于像我这样远离政治中心,只能感到灰心失望,看不出人事变动与方针政策的变动有关系。当我能够感觉到变化正在酝酿、发生时,已经是过了1977年的上半年。 恢复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 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1977年恢复高考都是一件标志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事。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从停止高考开始的,整个运动期间,“教育革命”的口号不绝于耳,高校是受文革蹂躏最重的地方,如果真有拨乱反正的想法,也应该从教育领域开始,尤其是应该拿大学招生的办法和标准开刀。 我还记得,1966年6月中旬,正当文革的烈火在神州大地燎原之际,《人民日报》发出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升学制度,紧接着,北京四中全校师生致信中央,响应女一中发出的倡议。《人民日报》在6月18日发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决定招生暂停,以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废止现行办法,将来的办法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要突出政治,要走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同时还配发社论,称“旧招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 从此之后,中国的大学停办多年,文革期间,大学成了批评斗争校长、老师、“牛鬼蛇神”、“阶级敌人”的场所,成了用刀枪搞武斗的战场。到了1968年7月,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1971年,“四人帮”炮制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提出危害深远的所谓“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学教师和这17年培养的大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73年的大学生招收本来打算略有改进,在推荐、选拔、突出政治的原则之上加一点文化考核,这一点小小的变化在全国成千上万渴望进大学的青年中不知激起了多大的兴奋、多少期望,他们除了勤奋好学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本事来满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标准。但是,“四人帮”连这一点稍微像话的变动都不能容忍。他们利用辽宁青年张铁生在文化考核时交白卷一事发难,把白卷先生树为“反潮流的英雄”,再次掀起大批判的浪潮,广大青年的学习和上进热情受到无情嘲弄。 文革积重难返,拨乱反正需要大手笔 上学读书需要考试,上大学需要比较严格、全面的文化考核,这本来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是,文化大革命把最基本的是非观念颠倒了,更何况,关于高校的种种方针和措施,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和亲自指示的,任何变动,都涉及到是不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都涉及到是不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问题。 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了一部以批判邓小平为主题的电影《决裂》,其中情节的矛盾焦点就是“什么人可以上大学”的标准问题。影片鼓吹的观点是,知识不但不重要,而且往往是负面因素,考核的标准是“是否忠于革命路线”,即忠于文革那一套,影片主人公豪气冲天地举起自己的手,气壮如牛地说:手上长满老茧,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这句话和这个形象,完全就是文革时政治标准的象征。文革时搞文化专政,万花凋谢,这部宣传“革命路线”的电影在全国发行,几乎每个人都熟悉它的观点和情节。这一套现在看起来是邪说谬见的东西,在文革中是如此有威势和深入人心,以至于被许多人当成天经地义。我记得,当我向一个在大学担任系主任职务的亲戚表示自己还有上大学的希望时,他异常肯定地说:“你们还要上大学,想都不要想!”他指的既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标准,也包含年龄。在这些搞教育的人看来,年近30岁,早就过了读书的年龄。我听了他的话既伤心又寒心:在这些心地不坏的人看来,我们被文革耽搁了,这一辈子就算完了。 确实,1976年秋季中南海内的剧变似乎与社会生活、与老百姓的命运前途没有关系。个人迷信仍然大行其道,只不过在“伟大领袖”之外又加了一个“英明领袖”。甚至到了1977年的2月,权威的宣传机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其重要社论中还在鼓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后来以“两个凡是”载入史册的口号使不少人对所谓“第二次解放”产生的欢欣鼓舞发生怀疑:是不是“四人帮”没有打倒,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 回归正常来之不易 到了1977年7月,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恢复职位,他复出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从报上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科学家和教授们纷纷发言,揭露和控诉文革的破坏,提出许多恢复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正常秩序的建议。希望的火苗又开始在心中闪烁,虽然我这时已经年满30岁,但我不甘心。 我从小把上大学看成一件神圣的事,我父亲早年毕业于武昌师大,1925年去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文学院,1927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经历、见识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刚上小学,他就教我外语和古文(他年轻时曾经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上世纪50年代在四川大学当俄语老师)。在我年届30时,虽然完全谈不上孔老夫子的“三十而立”,但人生观也相当成熟和坚定,我经常向朋友们宣称,人生一世,官可以不当,钱可以不赚,但大学却不可以不读,不读大学是终生遗憾。 我想读书的动力是太大了。我承认,在下乡的艰苦日子,在回城当锻工的时候,我抓紧学习具有功利的目的,我想通过掌握丰富的知识来获得某种工作岗位,从事或多或少带创造性、研究性的工作。事实上,不论在乡下还是在工厂,我的确利用我的知识优势得到一些好处。但是,我的读书动力更具有一种精神性的根本目的,面对文革的种种倒行逆施,我逐渐产生了一个明确的想法:我们这一代必须抗拒愚昧,必须首先把自己从蒙昧和野蛮中拯救出来。我曾和一群知青朋友争论,他们一小群人抓住机会就玩,以朋友关系的亲密无私追求善和美,抗拒文革中普遍的冷酷和残忍,对我整天读书不以为然。我对他们说,“真善美”三种价值中,求真为第一位。有人要剥夺我们天生受教育的权利,要让我们成为没有头脑的机械工具,我把这当成精神强奸,我激奋地说:喜儿受了黄世仁的凌辱要反抗,我们不拼命追求知识就太没有血性了! 6月底,教育部提出改变以选拔和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通过考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个办法实际上是把我们“老三届”排除在外,让我们成为文革的牺牲品。我和妻子得知这个情况时,觉得这不公平,这个办法对培养人才不利,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利。我们连夜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我们的看法和希望,并寄给物理学家杨澄中,请求他转交。我们并不认识这位科学家,只是天天看报纸,感到他的发言思想很开放,对于文革破坏教育、科技、文化的后果认识非常深切。 虽然我们的呼吁信很可能没有送达到邓小平手里,但最后国家的政策确实如我们所愿,我们获得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我后来听说,有关人员曾对邓小平说,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恢复高考当年来不及,要改也得到明年。但邓小平非常坚定,决定打破常规,坚持当年就改。他说,看准了的事情不能等,招生工作会议,重新开一次就是了。 进大学真不容易 1977年秋、冬之交的日子,我是在紧张的备考中度过的。坦率地说,这段时间我信心十足,说夸张一点还有几分趾高气扬,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优势很大。 听不少人讲,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却历尽波折,甚至饮恨终身。虽然国务院的通知规定高校招生原则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领导并不支持大家去报名参加高考,甚至以种种理由(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问题)刁难和阻止。我去厂部教育科报名本来还有点忐忑不安,作了要大费唇舌的打算。因为报名条例并不是说任何人想去考都可以,对于年龄大的人,要有一定专长,表明是个人才。我过分认真地对待这个条件,背了一大包书去,证明自己自学过英语、日语、德语和大学的化学课程,让主管干部考我。结果人家哈哈一笑,大笔一挥,轻轻松松就批准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所在的四川省或成都市的政策特别宽松,似乎任何愿意参加高考的人都得到了批准。因为我后来发现,不少在文革前1965年参加过高考而落榜的老高中生也参加了考试,从文件规定的条件看,他们明显不属于有高考资格。几乎每个大学都收录了这些1965届的高中毕业生,看来,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刻,敢于冒险和打破常规的人是会得到额外好处的。 我也听说,一般在工厂或其他单位上班的人都感到备考时间来不及,因为通知很晚,而且不能撂下自己的工作不管。但我比好多人条件要好一些,因为我干的锻工活很重,一个班真正干活的时间决不可能是8小时,空余时间比较宽裕。 荒废10多年后第一次面临“开科举考”,许许多多的人还真是手脚无措,合适的教材成了极度稀缺的资源,久违了的读书习惯要想恢复也并非易事。对于我,这一切都毫无问题。作为一个极其规矩的好学生,我把自己从初一到高三的所有课本都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这样的课本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另外,这么多年我一直保持刻苦学习的习惯,甚至觉得10多年前学得的知识并没有忘掉多少。 我就是在这种占尽优势的心理下参加高考的,不用说,我填的志愿都很高,一副即将进大学,以后当科学家的架势。 但是,出乎意外和令人尴尬的是,我落榜了。其实,以我的见识和阅历我应该有所预料,但我对“新时期”和“国家急需人才”这些话太当真,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次高考和文革前一样,仍然有“政治审查”这一关,而且标准和文革前一样,所谓“家庭出身”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强打起精神在车间干活,并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几个一起复习功课并考上重点大学的亲友送到学校(77届新生入学已经是在1978年初)。在难受的日子,一股激奋之气在心中油然而生。我认定,新的时代就要到来,我还有其他机会。 到了1978年3月初,我居然接到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的录取通知。虽然我的志愿上没有填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但我十分高兴,这使我摆脱了落榜的羞耻,而且,我从来就非常喜欢数学。 据说,是邓小平知道有不少学业不错的考生因故落榜而叫补招的。许多大学还不肯,说是校舍已经满了。邓小平说,那就招走读吧。我相信这是真的,只有以他的眼光、魄力和威望,才能够再三打破常规。可能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那么急切的心情。 难忘的大学校园生活 我入校时,学校已经开课一阵了。走读生刚进校时不那么自然,似乎低人一等,补招进来的,牌子是不怎么硬。但界限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们人很多,而且其中有人学业相当优秀。比如走读生老蔡原来是中学英语老师,他的水平之高,可能超过不少英语系的教师(他现在在美国一个大学当系主任)。我的英语也比较突出,远在数学系公共英语课教师水平之上,我去上了几次课,她就建议我参加一个免修的考试,通过之后就不上这门课了。 走读是相当艰苦的,因为学校离家很远,在城市另一端的郊区。我们纷纷在学校附近的农民家租房,住得比学生宿舍宽敞、舒服多了。这一带的农民经营花木,我们好像是生活在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的花园中。不久,学校安排出了校舍,我们搬进校内,头上的“走读生”帽子彻底摘掉了。 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不像正常时期那么单纯,比如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相比,几乎年长一倍。学校把年龄大的学生分在一起,称为“大班”,这里面真是藏龙卧虎,什么出类拔萃之辈都有。比如大班有个同学姓邓,文革前是高中生,进大学前一直在中学教数学,而且一直在钻研数学,他进校后就免修所有的专业课,几乎成天窝在寝室里写数学专著。他声称,他在学校呆4年,也就是图个文凭而已。他的水平显然比一般的青年教师高许多,他偶尔自习课时到教室里来指点一下同学,为的是调剂脑子,也从大家的赞叹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除了邓姓同学这种数学天才,大班生中不少人是以前的中学教师,或者单位的领导、骨干,他们学习轻松,多才多艺,常有惊人的表现。比如,有个同学写剧本、排话剧,学校文艺汇演时引起轰动,拿了第一,弄的本该独占鳌头的中文系同学很没面子。另一个同学会作曲,精通几样乐器,他创作和指挥排演的歌舞,在汇演时一举成名。还有一个同学是优秀的男中音,表演节目时一曲“拉兹之歌”,使得“再来一个”的呼声不绝。甚至我们学校保持多年的跳高记录,也是数学系大班的一个同学打破的。大班学生的种种不俗表现,使得小班的同学非常敬佩,而且把他们的崇拜流露于言表,这使得大班的一些人心里非常舒坦熨贴。 77级学生入校后,普遍产生了一个问题,是校方和老师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经过严酷考试筛选,怀着“天之骄子”心态进校的77届新生与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之间的冲突在各个学校都发生了。新生对未经考试就读大学的人表现出公然的鄙视,“工农兵”们也不服气,学校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使双方相安无事。我们数学系教训新生的办法很特别,系上举行一次“摸底测验”,试题相当深,以至于大半同学不及格。这么一来,大家感到自己其实并没有多么了不起,也深感学习负担很重,自然失去了没有了“工农兵学员”的心思。 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77届学生中出现了“陈世美”,一些人“中举”之前“落难”在农村或基层单位,草草结婚,生子育女,一进大学,周围是如花似玉、天真清纯的“小班”姑娘,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另度一春的欲念。记得那时学校领导、年级主任或班主任经常接待前来哭诉、哭闹的“秦香莲”,流言和故事飞快地在同学中传播。当年《人民文学》上有一篇小说“杜鹃啼归”,讲的就是这种事,影响很广。据我观察,我校的“陈世美”们似乎没有人成功地谋得新欢,除了暴露自己的不忠,只落得学校的处罚和同学的批评、议论。 经历文革摧残的大学校园在70年代末显得生机勃勃,思想空前活跃。最吸引我的是各种课外讲座,数学教授们的讲演我几乎一场不缺,值得回味的是,他们讲完专业问题之后,总要小心翼翼、自责地补充一句:“我这次没有阐述马克思《数学手稿》中的光辉思想,这是我今后要努力学习和改进的。”我读过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那根本不是数学著作,而是黑格尔哲学概念的搬用和演绎,但教授们感到不发挥马克思的思想总有一种有罪感,就像几年前发言、写文章不引用毛主席语录就没有正确性一样。四川著名作家雁翼的讲演很大胆和刺激,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其实,历次运动整知识分子,下手的还是知识分子。”在讨论“真理标准”的开始,四川大学一位哲学教师来做报告,谈到她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似乎有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紧张气氛,我不明白,为了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 我们都有类似于劫后余生的感觉,特别珍惜现在的机会,学习极其刻苦用功。不过,据我的体会,数学恐怕是各学科中最难学的,因为面对数学的高度抽象和推理的极度复杂艰难,勤奋和刻苦基本上无济于事。特别是,因为合格的教师奇缺,急需人才,有关部门决定我们大班变为快班,用最难的教材,抽调本校最好的教师,把本来4年的学习任务3年完成。这一下,使不少人叫苦不迭。我周围的许多同学原先在单位都是佼佼者,听惯了赞扬的,现在学习吃力、掉队,内心的沮丧和折磨,我能够感觉得到。特别是,人们经常听到隔壁寝室里政教系的同学聊天、拉琴,感到非常不平,他们口出怨言:数学系这么苦,人家这么悠闲,到头来工资还不是一样? 又一个新的开端 不管是乐也罢,苦也罢,我在大学本科生涯还不到一半就离开成都到了北京,我被学校破格特许考研究生,于1979年秋季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这是又一个新的开端。北京的生活、气氛与故乡大不相同,尤其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节奏飞快,刺激性事件接二连三,令人目不暇接,有时甚至使人喘不过气来。比如,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前人山人海,“星星”画展叫人眼界大开。 开学典礼就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在一个豪华的大礼堂中举行的。当社科院一些领导从大门鱼贯而入时,我和其他人立刻发现了其中有王光美,他们缓步前行,和过道旁的同学一一握手,碰巧,我就坐在过道旁。当我和王光美握手时,听见她缓缓地说:“谢谢同志们”,感到意味深长。当他们就坐后,满场的人齐声喊叫,希望王光美发言,推辞几次后她站起来说:“我知道,同学们的热情,并不是冲着我来的。”这时刘少奇还没有得到平反,这一幕当然意义非同小可。 我所在的哲学系有一个“毛泽东思想”专业,其导师有哲学所的所长。他以前是部队的军级干部,他经常来和学生见面,说话大胆坦率。那时党内高级干部正在讨论和争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系列未定稿,他把各种议论、看法告诉自己的研究生,我们立刻听到第二手消息,引发种种兴奋和猜测。 从1977年开始的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是我的生活的一个新开端,它们刚好和我们国家告别过去,走向新的一轮现代化途程的开端相重合,我想,也许是凭这一点,我至今习惯于把自己的未来和祖国、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 作者介绍:中国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形形色色的造反》、《告别20世纪》、《不懈的精神追求》等10余部。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发表评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