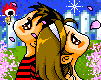| 为什么汽车产业政策的生命力如此顽强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28日 16:16 《商务周刊》杂志 | |||||||||
|
为什么汽车产业政策的生命力如此顽强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实际上,政策制定和审批部门的研究人员对汽车产业的理性判断,对政策的实质影响极微。各种力量的参与使得政策变得越来越复杂 □记者 王晓玲
6月9日,日本富士重工首携旗下斯巴鲁、森林人、翼豹、力狮等产品在第八届北京国际车展上亮相。但富士重工并非要在中国的合资企业贵航云雀汽车有限公司中生产这些车,而是仅仅在中国进行销售。 有报道认为,富士重工已经准备抛弃这只“云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资料显示,云雀在2003年共销售1296辆,在全国400万辆的总销售额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更有媒体指出,云雀目前已处于半停产状态,富士离去后,云雀面临从汽车产业被踢“出局”的命运。 但就在这则消息出现不到一个月前,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正式出台,按有关部门的说法,这个政策同10年前的94版产业政策一样,其目的“一是维护国家利益,二是维护行业利益,三是维护国内所有生产企业的利益”。 云雀作为当年“三大三小两微”八个定点汽车企业之一,正是94版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却倒在新《政策》出台的重大“利好”之后,真是十分有趣。 尽管这绝非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似乎当年的定点企业并非政策的真正受益者。10年间,中国市场车价奇高,巨大的社会成本,养肥的却正是他们的对手。 “40%的外国资本,控制了50%的国内市场,拿走了70%以上的利润,这就是中国汽车产业的现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广指出,与产业政策扶持民族汽车工业的本意正好相反,外资才是中国市场真正的获利者。 但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基本沿袭94版政策老路的新汽车产业政策经历了一年的讨论后,还是正式发布了。比政策内容的修改更重要的,是政策能够延续、出台的动因。 去年在我国出版的《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一书中,收录了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控制的政治经济:美国的食糖业》。安妮·克鲁格观察了美国1934年到1990年的食糖业,几十年来美国政府通过食糖计划对国内及进口食糖的管制,不仅造成国内食糖价格高于国际市场、而且食糖生产者并未获得超额的利益,但奇怪的是,这个计划仍然不断得到业内企业的支持,而且通过国会听证。 克鲁格在分析政策控制经济活动的影响时指出:首先,与被其所替代的机制相比,这些来自政策的控制,充其量是以成本更大的方法取得其目标。其次,政策假设的控制受益者,常常完全不是实际的受益者(如果有受益者的话)。再次,控制的成本在政治决策中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曲解,至少在最初时是这样。 但是,尽管有着这些已经确认的结果,控制依然我行我素,对于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真正具挑战的正是去探索其中的原因。 在中国复杂的汽车市场中,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种竞争: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间的竞争、合资企业内中外间的竞争。不应该怀疑94版政策的制定者是希望通过政策保护,使国内企业能够获得长久的优势,赢得与跨国公司的竞争。 实际上,此前的中国市场里,前两种竞争还不显著,当时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合资企业内的中方与外方之间。在以市场换技术为指导思想的合资中,三大中只有一汽的“红旗”勉强支撑,其他两家早已没有了自己的轿车品牌,可以说在竞争中彻底失败。 以民族工业为由而被国家政策所保护的“三大三小”,虽然曾在垄断特权下获得了垄断的超额利润,但现在看来,它们继续支持产业政策却未必符合企业的长期利益。 目前,政策导致的垄断正在被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打破。继去年大众宣布将在中国投资60亿欧元,今年北京车展前后,各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公布了新的投资计划。通用汽车公司刚刚宣布要在3年内新投入30亿美元资金,到2007年将年产量增长一倍;福特汽车公司则谨慎地宣布了其在中国市场新增10亿美元投资的计划,目标是将其产量增加3倍;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与其北京的合作伙伴签订了价值12.3亿美元的合同,其余世界汽车市场的巨头——丰田汽车公司、日产汽车公司、本田汽车公司和现代汽车公司,也都宣布了总值约为100亿美元的新投资。 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上文章的说法,中国将陷入汽车狂潮。这对于10年来为垄断市场支付了巨大成本的消费者无疑是一个福音,但不能忘记,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产业目标应该是中国自主汽车企业、自主汽车品牌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从长期看来,由于产业政策中规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方股份不能超过50%,那么计算一下以上投资额,未来三五年内,几家中国企业要维持当前的股比,也至少需要投资200亿美元以上。这真让人担心,如果将投资如此集中于合资企业,那么在新政策中被寄予厚望的中国汽车企业如何才能实现“2010年汽车生产企业要形成若干驰名的汽车、摩托车和零部件产品品牌”的政策目标?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按新汽车产业政策走下去,基本没有多少人相信该产业目标能够实现。 那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新政策能够获得几大国内企业坚定的支持? 安妮·克鲁格对食糖计划的观察中也产生了同样的疑惑:“从更长的时期来看,肯定没有什么国内经济利益相关者从食糖计划中受益;获益至多是短期的。尽管这样,也必须质疑,为什么各种各样的游说集团努力寻求美国国内食糖面积的扩大。” 当然可以用“有限的理性”来解释利益集团在长期和短期利益间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克鲁格指出:“即使有了个人理性,一个集团的利益也不必然会达到最大值,首要问题是个人当事人以他们自己的自利采取行动的程度。” 作为“寻租”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克鲁格当然不会忽略政策供给者的作用。克鲁格认为,一旦一种政策工具出台,“就意味着将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会遵照其行动,并且力图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预测的方式去利用政策。”这使政策变得越来越复杂,牵涉其中的力量也越来越多。 在中国这显然更为重要,虽然我们无法像格克鲁格那样,分析国会听证会的记录,但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实际上,政策制定和审批部门的研究人员对汽车产业的理性判断,对政策的实质影响极微。 作为国务院的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相关研讨会中对产业政策曾经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汽车工业相关新政策的制定中,政府不相信市场,仍然希望用宏观调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刘世锦在年初的采访中对记者强调,10年产业政策调控在付出巨大社会成本后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标,“新的产业政策已经没有发布的必要。” 但智囊的判断并没有影响到该政策获得批准。 新汽车产业政策出台后,记者采访了发改委下属研究机构的一位研究员。该研究员认为,新一版汽车产业政策仍然没有搞清中国汽车工业的定位,“新的产业政策仍然是要汽车工业以三大为中心来重组我们的企业,但三大什么也没有,一没品牌二没产业链,基础是空的。” 但专家们承认,各部门在政策的制定中,很难完全站在国家的高度,“所谓国家的高度,也就是一种超然的态度,也就是各部门完全不考虑部门的利益,而只关注汽车产业的长期发展、命运”。 “总之,汽车产业政策的制定是个利益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产业问题。汽车产业政策考虑很多的平衡因素。”该研究员称指出。 但最重要的是,政策最终能够在国家的高度被最高层通过。克鲁格也不禁问道:为什么在政治舞台上,在那些即使是不涉及利益纠葛的决策者眼中,某些荒谬的谎言被证明是可信的,或者被认为是可信的? 在去年的一次汽车产业政策研讨会上,面对反对者的质疑,一位发改委的官员这样辩解道:“在对外政策上,我们就是要为国内企业撑腰。中国的最大企业与国外公司相比,在企业间的竞争和平等谈判上,都处于非常弱的地位,政府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给国内企业撑腰,我们会永远处在被动地位。也有人说我们在保护汽车企业暴利,对消费者不负责任,如果站在消费者角度上,我们确实有愧,但从长远和发展的角度看,如果企业不赚钱,怎么才能发展?企业高利润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而汽车行业只有持续的高投入才能高产出。在没有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高投入从哪来?” 这种曾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称之为“神话”的观点,为什么被认为是可信的呢? 安妮·克鲁格的这一段话或者可以作为注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本身也有‘它自己的生命’,一旦一项政策出台,政策内部的人们(政策的供给者)、和政策外部的人们(政策的需求者)都向专用于这个计划的知识投资,否则你根本无从置喙。结果政策趋向于延长它们自己生命周期,给制度变革带来困难。随着计划变得更复杂,信息成为进入的障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非专家集团参与决策过程形成了一种重大的障碍。” 在经历了10多年的口诛笔伐之后,汽车产业政策自己也像有了生命力一样,这真是一个让人泄气的结论。 |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产经动态 > 《商务周刊》2004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