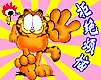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财经》杂志:职业金融家阶层兴起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9日 10:26 《财经》杂志 | ||||||||||||||
|
《财经》杂志8月5日封面文章: □ 本刊特约研究员 陆磊/文
任何一个重大的决定都将产生多重的影响。高盛进入中国,开启了一条引入外资市场化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路径;与此同时,一家世界一流的投资银行与一个中国一流的投资银行家发生了不同寻常的结合。 与以往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比较,该事件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信用主体的转化;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一致;三是风险锁定下的激励合同。而这三个层面所体现的含义绝非仅限于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准入,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银行家阶层的真正兴起。 信用主体的转化将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制度发生深刻转型 已有的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无非采取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中金公司合资模式”,即摩根与建行合股组建新机构;二是“战略投资模式”,如国际金融公司(IFC)参股民生银行和南京市商业银行;三是“独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模式”,如汇丰、花旗等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我们可以发现,除第三种模式不涉及信用关系外,前两种模式的信用主体都是单一的——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机构存量。 但是,高盛向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三家公司股东个人贷款,开创了信用主体转化的新模式。 信用主体的转型不仅仅是一种投资花招(trick)或新的业务增长点,而是潜移默化的体制变迁。确切地看,从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从而渐进地展开金融体制改革的20年中,无论境内还是国外投资者普遍持有“国家信用严格高于机构信用,机构信用严格高于个人信用”的传递性(transitivity)观念。合资和战略投资模式依然是以上传统观念的现实体现,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三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事实:一是国有金融机构的低效率与安全性的离奇组合;二是我们拥有世界性大银行但不具备世界性的银行家;三是存款人、投资者和境外机构对国家信用和国有机构的高度信赖甚至依赖。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维持这一体制和观念所需要的成本是否国家所能承受。金融业值得思考的现象有两点:一是2004年上半年银行类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18.1万亿元,增加1.43万亿元,依然是社会融资的绝对主体;二是股票市场流通市值1.26万亿元,半年缩水574亿元。银行类机构的绝对可信赖与证券类机构的不可信赖成为金融市场的主流观念,这必然阻碍中国的资本形成效率,加大间接融资过度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那么,在资本市场上,什么主体是更可信赖的信用对象? 高盛发现了以方风雷为代表的资深投资银行家,并选择了不与现有机构合作,不依赖国家信用,而依赖银行家个人信用的路径。直观地进行判断,这些银行家个体的信用市值价值数千万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高盛的另辟蹊径并不意味着中国现有金融市场问题多于成就。恰恰相反,只有在金融业渐进转型和逐步优化的过程中,银行家群体才可能突破自身所代表的“机构标识”而浮出水面;同时,只有金融深化到一定程度,外资机构才可能对银行家个人实施定价并完成信用交易。如此看来,中国的金融转型毕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致化将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动存量重组 高盛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将采取直接赋予经营者部分所有权的新模式,这在我国的企业改革领域绝非新生事物。但是,基于对个人或小群体控制金融机构并由此引发道德风险的审慎考虑,我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允许金融机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这种思考不是没有道理的,2000年以前的城市信用社整顿中,大量的案例体现为信用社的实际控制者因“自我融资”导致整个机构陷入支付困境和局部金融风险。在我国金融改革和监管当局对如何设计激励合同而伤透脑筋之时,高盛率先采取了对经营者贷款,并以此作为经营者持股来源的制度安排,这无疑是值得分析的。 一方面,金融业永远面临两种道德风险的权衡取舍(tradeoff)。一种是始终困扰我国金融业的两权分离、两权制衡导致的积极性低下、等靠要政策问题。无论在证券市场还是在银行改革中,把经营责任推给所有者和监管当局是始终存在的痼疾,于是出现了央行不断无奈买单的局面。另一种是两权合一导致的经营者(也同时是部分所有者)与存款人、投资者等无辜第三方的矛盾,即经营者可能滥用吸收的公众存款或投资。证券公司一度普遍存在的挪用客户保证金,部分高风险银行类机构滥贷款以追逐高风险-高回报项目都属于此类。 因此,理论上,我们只能在两种道德风险间寻求相对平衡。 但是,这里是存在价值判断的——哪一种道德风险是可控制的,或者说是成本更低的。我们认为,后者比前者好,这是因为,后者是可以通过激励合同约束的微观行为,比如监管的优化、业绩考核等。而前者,除了制造低效率金融体系外,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个貌似安全但需要不断需要货币发行来填补的黑洞。高盛之所以选择了后者,是因为作为一家世界级的投资银行,他们显然对自身的激励安排和治理结构具备充分信心。 另一方面,管理风险而不是回避风险是银行家的基本职能。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银行家阶层,一个直观的判断依据是,金融机构没有形成自主风险管理能力。尽管当前经济存在过热迹象,但熟悉金融业的人都应该对1997年至2001年间的金融机构高存差(或称“惜贷”)记忆犹新。这一现象直接阻碍了中国的资本形成和经济效率,其体制原因就是外部监管约束强化后金融机构发现信贷或投资是一桩“不划算”的买卖。高盛通过直接赋予经营权和股权,事实上直接赋予了银行家以风险管理权,发现收益等于发现风险,并有效地管理它。 风险锁定下的激励合同将设定新的金融业竞争标尺 当然,任何理性的机构投资者都不愿意过度承担风险,高盛也不例外。但是,它采取了一种风险锁定前提下的激励契约安排——买入期权。对于中国银行家持有的股权,它采取先安排贷款,后实行期权的方式。一方面,它的风险是锁定的,无非是数千万美元资本金。另一方面,它赢得了持续监测中国资本市场运行和这些银行家绩效的时间。 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一家机构的得失,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一制度安排的样板效应。在整个事件中,监管当局和机构自身的利益取向是不同的,当局希望此事成为一个样板,或者成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真实起点;而机构自身的目的是盈利,因此希望至少在短期无法被竞争对手复制。 如果就此进行理性的预期,我们可望看到中国机构投资者将在客观上被置于新的行业标准基础上:第一,中资金融机构将不得不真正面临既有外资管理与资金实力,又配比以强力本土银行家的机构冲击,由此不得不按新的行业标准竞争,中国投资银行业的颓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清扫;第二,哪个银行家可能成为方风雷一样的QDII(qualified domestic invested individuals)——“合格的境内被投资对象”(这是笔者的自创术语)。 20世纪80年代企业改革以来,中国毕竟涌现出了新兴企业家阶层,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快速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但是,在金融改革20年来,我国没有出现真正的金融家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金融体制改革始终面临极高的道德风险,始终无法摆脱机构层面的群起群落(如城市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的整体兴起和全行业整顿)。尽管我们不能十分肯定,但是职业金融家阶层的兴起将有可能造就一个权责对称、道德风险较低、稳健经营的新型金融组织架构,并由此提高中国的资本形成效率和金融安全。■ 相关报道:
相关专题: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财经》2004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