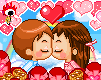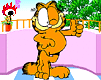| 文化研究中的假命题与文化研究困境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 13:37 中评网 | |||||||||
|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曾与李登贵先生就有关问题有过多次讨论,李登贵先生还为本文提供了不少背景材料,笔者在此谨致谢意。 内容提要:(1)近年文化研究热的产物是一些假命题,而鲜有实证性分析。(2)主流经济学倾向于从社会功利意义上解释行为文化,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更为这种解释提供了有力支持。现代经济学认为,行为文化是人们为降低人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而产生的一系列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兴起一种文化研究热,一批学者(包括少数经济学者)试图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中解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疑惑。笔者不敢简单否定这种“热”的意义,但在总体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缺乏批判性思维而耽迷与引经据典的“考据派”学风。有的学者则是以书斋里幻想出的概念联系,来替代现实事物之间本来的联系;还有的学者甚至把玩着一串串概念,在搞填空游戏。分析中国社会的过去与未来不联系中国的文化,是不适当的;但如果在这项研究中不采取批判性立场,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文化问题呼唤实证性研究。本文试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对近些年我国的文化研究作一评论。 一 讨论文化,首先遇到文化的内涵问题。对文化内涵理解不同,将影响文化研究中的交流与讨论。概念是语言的要素,语言以方便交流为准则。类似如文化内涵理解上的混乱,如果发生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那将是不堪设想的;好在是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只限于一个很小的圈子,尚不至于导致社会生活的混乱。但这个状况无疑会阻碍对问题深入研究。 从已有文献看,文化问题论者大多不给文化一个定义,而少数定义是很值得商榷的。梁漱溟曾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梁漱溟,1949,1页)。梁漱溟这个定义很难用来讨论文化问题,至少多数文化论者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这方面的经典表述来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L.F.墨菲,他认为,“文化是知识和工具的聚集体,我们以这些知识和工具适应于自然环境;文化是一套规则,凭这些规则我们相互联系;文化是知识、信念、准则的宝库,据此我们力图理解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墨菲,1986,33页)。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广义的关于文化的定义。若依这个定义作一个简单的分类,文化可以包括工具形态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符号文化三个层次。 从我国多数学者的论述看,目前约定俗成的文化定义似乎是墨菲定义中的行为文化和符号文化,只是某些论者对此二者不加区别,并更多地只在符号意义上谈文化。本文遵从约定俗成的惯例,所谈文化是指行为文化和符号文化,并将注意二者的区别。 我们先来讨论行为文化。从亚当.斯密开始,主流经济学便倾向于从社会功利意义上解释行为文化,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更为这种解释提供了有力支持;“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也包括了它在行为文化研究中的成功。概言之,现代经济学认为,行为文化是人们为降低人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而产生的一系列行为规则;行为本身不是文化,对行为的约束才是文化。汪丁丁曾归纳过经济学家对文化的认识,认为由不确定性产生的“公共领域”(契约对人们的行为不作明文规定),有可能存在多种解,为了使那些有利于提高福利的均衡解更容易出现,便需要一种文化,使人们在不确定性情况下找到决策的焦点。焦点的存在减少了人们选择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这实际上讲得是行为文化。行为文化的存在,与人的利己本性和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二者衍生的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关。行为文化的意义在于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仅从行为文化形成的条件上看,可以将其依四种形式划分。一是由国家强制实行的行为规范,包括各种法律与正式的制度安排。二是人们通过教育部门、社会舆论部门和教会等机构进行知识、信念的传播、训导,而形成的具有理性化特征的合法性观念体系,这种观念告诉人们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从而形成人们价值准则的重要依据。诺斯将这种观念体系称作意识形态,并将其看作是决定设发展的重要变量(诺斯,1981,53页)。三是道德伦理观念,这是被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认可、尊重的行为规范,虽具有非强制性,但仍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四是由宗教情感和教会机构的权威等因素所决定的行为和礼仪准则。 再看符号文化。符号文化是具有某种历史继承性的、表征人类对自身与环境认知水平的特殊信息系统,具体表现为文字、有声语言、形体语言和各种艺术形式等。符号文化不同于知识,它只是知识的形式外观;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价值准则和道德信仰等行为文化通过符号文化来表达。符号文化的功能在于给人们提供社会交流的工具,起到降低社会交易费用,从而降低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作用。一个团体,一个社会群落,乃至一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统一的符号文化,人们借此达成相互之间的认知,减轻陌生感和恐惧感,增强信任感,从而达到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符号文化越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其降低社会交易费用的功能就越强。经过学者系统化的符号文化表现为典籍文化。目前我国的文化论者大多在典籍文化的意义上谈文化。 二 翻阅近些年我国文化研究文献,可以从中发现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民族的发展命运。这个判断乍看起来无可指责,但从论者的论述看,这个判断是文化问题研究中的最重要的假命题(以下简称“民族传统文化差异命题”),且其他诸多假命题都与这个假命题有关。 (一)民族传统文化差异命题忽视了民族文化的共性 民族传统文化差异命题认为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有重大差异,并决定了民族的发展命运,在近代则决定了民族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差异。在这个命题之下,论者通常强调不同民族在基本价值判断和心理倾向方面的差异。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也有少数国外著名经济学家过分强调民族的文化差异。布坎南曾说:“我想在斯拉夫民族与非斯拉夫民族之间有着一种根本的差别”(肖满章采访布坎南,1995)。【诺斯明确地批评他所谓新古典主义的人性假说:“大团体在没有明显收益补偿个人参与付出的大笔费用时,确实在行动;人民确实在投票,他们确实参加了匿名献血……我们所用的成本收益计算过于有限,未能抓住人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其他一些因素”(诺斯,1981)。强调文化意义的学者大多怀疑主流经济学的利己人假说。中国某些经济学者对文化的强调可能与诺斯的思想有关。】 多数重要经济学家拒绝“文化不可知论”,否认民族的实际文化传统有重大差异。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一切人类的心理偏好是一致的。斯蒂格勒和贝克尔的研究认为,个人的偏好没有重大差别,爱好差别可以简化为费用的差别(M.W.里德,1987,1-454)。这种看法也被舒尔茨所接受:“……这种偏好和动机在多种不同社会都基本是相同的”(1964,26页)。这个判断的意思是说,人们的心理偏好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后天教育以及环境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在满足相同的偏好时,支付的成本会很不相同,出于利益的考虑,人们会找到一个均衡点,使得心理满足的边际效用与实际的货币支付的边际成本相等。由于实际的货币支付的边际成本在不同民族之间可能有重大差别,所以不同民族表现出不同的外在心理偏好。 经济学强调人们之间的共性。我们已经熟悉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的“经济人”假说,把经济人描述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这个假说有两层涵义,一是说,人总是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人是利己人;二是说人可以把握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人是理性人。一般而言,这个假说是一个具有普遍现实性的假说,但这个现实性却经常受到怀疑。由于许多怀疑不无道理,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了这个假说,使这个假说的内容大大丰富了。 一方面,从利己人这个层面看,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者是追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这个效用应该满足行为者各种各样的偏好,不仅可以满足诸如对苹果、橘子等有形物品的偏好,甚至还可以满足伦理上的偏好。这样一来,经济学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行为差异看作是偏好或者效用函数的差异,甚至少数人的些微的利他主义,也被看作他们的特殊的效用函数,而不是背离一般原则的特例。此外,人的利己主义特性在斯密那里尚未包含损害他人的意思,而现代经济学的许多作者则认为,在条件适当时,利己人会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搞机会主义。 另一方面,从理性人这一层面看,现代经济学已不再坚持行为者有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算计能力,而是认为经济行为者通过估计每种结果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效果,来估价他的行动的预期效用。行为者当然受到信息获取成本以及自身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尽可能地作出合理的决策。基本观点仍然是,经济行为者是理性的,他们在各种约束的限制下,追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 人的理性甚至是一种心理倾向。著名“心理分析学派”学者C.G.荣格在1933年的著作中说:“根据我们理性的假定,凡事都有它的自然规律与可以觉察出来所原因。对此我们深信不疑。象这样的因果律就是我们人的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不允许任何无形的,专断的和所谓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喜好秩序井然的人难免会厌恶偶然事件的发生。偶发事件经常会打破常规,使预料的事情失去常态,因而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我们对无形力和偶发事件都感到厌恶,因为他让人感到好象有某种鬼神或外在之神在作祟。……由于这些都违法理性原则,所以自然会被唾弃”(荣格,1933,123-124)。按照这个观点,人类还有厌恶冲突、寻求秩序的心理倾向。 中国古代就有利己人假说。尹文子云:“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仪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得不肖者触地是焉”(转引自梁启超文)。《庄子.盗跖篇》称: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待就,故不待师,此人之性也。大儒孔子和管仲,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只是被后来的论者忽视而已。 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的假说。上述关于普遍人性的理论可以看作一种假说,相反的理论(如性善论等)也可以看作一种假说。两种假说似乎都可以找到例证而获得支持。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以前一种假说为基础来设计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常常在功能上具有可靠性;而以后一种假说为基础来设计制度,常常导致一个失败的结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公有制的人性论基础是性善论,其效率之低下、贪婪人性之无以制约的结局以人所共知。事实证明,关于普遍人性的理论对社会发展更有解释能力。 关于普遍人性假说的理论还得到心理学研究的广泛支持。例如美国《读者文摘》的一项调查发现道德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无关,而与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有关。杂志社在亚洲3个超级都会、5个大城市和6个普通市镇总计放了140个皮夹子,每地放10个。每个皮夹子里都有人名、当地住址、电话号码、家庭照片、便条、优惠券,以及折合10到50美元的当地货币现款。类似的调查在美国和欧洲也作过。尽管捡到皮夹子后归还的人都声称是道德的力量使他们这样做(似乎不归还的人不道德),但统计分析的结果却十分耐人寻味:诚实与否与民族无关,在华人圈中,新加坡人为诚实之最,归还与不归还之比为9比1;香港人最差,为3比7。欧洲人的归还比率为58%,比亚洲人只高1个百分点;美国的归还率略高一些,放了120个,归还80个,归还率为67%。诚实与否与贫富关系也不大。较富裕的汉城、台北与较穷的印度城市几乎没有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归还率与放皮夹子的场所有关系。留在医院的5个皮夹子归还4个,留在银行、邮局的13个归还10个,放在旅馆大厅里的4个悉数归还,留在教堂、庙宇、忠烈祠、神社、清真寺的10个有8个回来了。但是,抛在市政厅和其他市府机关附近的有一半没有归还,而留在街上、公共场所、公园的13个,有10个杳无音讯(约瑟夫.里夫斯,1997)。对于这个测试报告,合理的结论应该是:除过受监督可能性较大的场所之外,凡是人际关系较为确定的场所,皮夹子归还率较高;反之,则比较低。这是因为,在人际关系确定性程度较高的地方,道德失误引致的惩罚较重;而道德显示则不仅会得到赞扬,还会增加交往圈中的威望,产生实际利益。任何一个民族或人群,一旦有可能较容易地逃脱道德的惩罚,道德对它们的约束力就会下降。 日本学者千千岩英彰对世界各民族的颜色偏好作了研究,他发现世界各国人民最喜欢的是蓝色,其次顺序为红、黑、白、绿、黄。对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的5500名年轻人进行调查,让他们看47种颜色(包括金和银在内),结果是蓝色和红色任何国家都非常喜欢,据此可以认为,人类对颜色的审美意识是基本相同的。在对关于颜色的记忆、形象、意义、喜好以及配色的评价等7个领域43个项目的资料一并进行计算后,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在那一个国家,70%的人的看法是相同的。作者认为,大概30%的人的个别性对那个国家的色彩文化作出了贡献。这项研究也说明,各民族的基本心理倾向是基本一致的。 (二)民族传统文化差异论者被假象所迷惑 许多被论者所强调的民族文化差异来自一些假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典籍文化差异产生的假象。典籍文化是经过学者系统化的符号文化。典籍文化在过去大多数时代由官方提倡并反映在历史典籍中,特别由古代“圣人”所勉力传播。世界主要文明国家在历史上遗留下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的一部分典籍由于官方或其它重要社会势力(如宗教)的推崇,对民族历史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典籍的作者被尊为“圣人”,他们倡导的人类行为规则被当作(只是被当作,不一定实际上是)民族行为文化的代表。 典籍文化与实际的行为文化是不同的。在历史上,一个民族的文化典籍陈述的价值观是一套,而人们的行为文化可以是另一套。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在文化研究方面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民族的典籍文化与实际的民族行为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不讨论清楚,关于文化问题的一切研究都可能走入歧途。多数文化问题的研究专家常把一个民族的典籍文化看作民族的行为文化,把民族间典籍文化的差异看作民族行为文化的差异,然而这一等式决没有普遍性。行为文化与典籍文化之间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历史上的学者不一定将本民族的行为规则研究清楚,并将其真实地记录下来;历史上的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也不一定反映民族的真实情感和社会的本来面貌。学者们的作品难免渗透自己和自己所在阶层的价值观,甚至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其价值观的诠释。学者们不是圣人,他只愿意说出那些在他看来对他生前死后最有利的话;虽然某些学者对“真实”有特殊的偏好,但这仍不能保证他没有思想上的片面性,因为人的生活范围和知识积累的状况总是要限制人的眼界,学者们也不例外。所以,一个民族的典籍文化,首先是一个符号文化系统,它是否反映民族的行为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个传统,是极不确定的。但是,学者们很难这样看问题,他们倾向于把民族的典籍文化看作实际的民族的行为文化。这一认识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相沿的历史研究不得不依靠文化典籍之外,还由于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学者行为”在起作用。学问是学者的看家本领;为抬高学者的地位,必要抬高学问的地位,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学者们一生为自己的学问而投资,日子越长,越有理由希望得到高额回报;同时靠新知识获得回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便没有了学习新知识的利益驱动。由于这种基本的学者行为,使学者们极易夸大自己所掌握的文化典籍的意义。例如,梁漱溟先生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别,并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便犯了以民族典籍文化替代民族行为文化的错误。实际上,儒家经典的伦理本位,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任何一个民族在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时期都不可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而一切现代社会恐怕都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在较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的血亲共同体内部,才会有伦理本位的文化类型。 我国学者秦晖、苏文先生曾对文化差异假象作过深入分析,他们认为,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种族性的;现在人们列举的种种“中西文化”差异,其实主要不是什么中国与西方“人性”之不同,而是自然经济下的农民共同体与商品经济下的独立个性之不同。当然有超时代的民族传统存在,然而只要认真分析就可言发现,真正的传统大多属于民俗学范围(1991,224)。举例来说,有人讲“东方道德文化”、“西方功利文化”,但实际上宗法共同体中的“天然首长”常常无道德可言,而契约社会中的政府关于却往往处于道德自律中。关于文化研究中的皮相之见多不胜数,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人把典籍文化与实际的社会主流文化混同起来了。秦晖、苏文先生在这一点上非常清醒,他们没有被中国文化典籍的教义所迷惑。他们注意到,宗法农民的实际伦理观念常常与儒家的正统教诲相冲突,士大夫们耿耿于怀的“礼义廉耻”,在农民中未必有很大的约束力。中国农村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搭伙计”、“拉帮套”等“性散漫”现象虽然不合乎礼教规范,但却很受农民认同。毛泽东的调查曾发现,苏区许多地方农民在翻身解放后马上立法“申明禁止捉奸”(290、272-273)。实际上,此种社会文化与典籍文化的背离现象,中外历史无不皆然。当然,笔者的这些分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典籍文化的意义,事实上,一种典籍文化的存在会对民族历史发生影响,包括对民族社会的稳定发生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会改变民族历史的基本进程。限于本文篇幅,此问题这里不能再作讨论。 对西方历史与现实的大量的经验观察也证明,民族之间的典籍文化的差异并不真正反映民族之间实际的行为文化的差异。韦伯把基督教精神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也是一个假命题,然而,这个假命题引得国人如痴如醉,有的学者由不得把中国的问题也和中国的宗教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宗教典籍所反映的价值观也并不代表民族的实际的行为文化。经济学家廷伯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基督教国家或政治家的基督徒式的说教,和他们的行为之间存在巨大反差:真正地履行了基督教教义的人是少数例外,其中不是传教士”(1984,361页)。宗教产生的心理根源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因此,宗教具有降低不确定性的作用。伟大的费尔巴哈曾说:“宗教的整个本质表现并集中在献祭之中。献祭的根源便是依赖感----恐惧、怀疑,对后果、对未来的无把握……而献祭的后果……则是对后果的有把握,自由和幸福”(费尔巴哈,1845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宗教的存在反映了人们试图规范这种关系的愿望,尤其反映了人们关心彼岸世界、试图与彼岸世界对话的愿望。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宗教具有加强人们之间相互认知的作用。共同的崇拜对象、普遍接受的教义规则,可以成为人们之间相互认知的符号,从而可以降低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至于各民族教义在其本质上并无重大差别,如果有什么差别,它也不是问题的原因,而是问题的后果。 近些年曾有不少学者把中日经济发展的差异归因于中日之间民族文化的差异,这种观点受到严肃学者的尖锐批评。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说,“认为日本人天生就比别的民族更具有忠诚心是不妥的。一个人在一个公司工作,主要不是来自对公司的忠诚,而是因为工作调动会给个人带来很大的社会损失”(转引自杨明方文)。事实上,日本人的所谓纪律与“团队精神”主要与现代工业的压力特别是日本的竞争地位有关。曾有过这样一个历史片断:1915年,一位澳大利亚专家在访问日本后写了一个报告,报告称:“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或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素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当年的极度无望,与今天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林毅夫先生评论说: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它们正在改变。……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林毅夫,1989)。 现在人们赞叹欧美人在工作岗位上的敬业精神,似乎也与文化传统有关。事实上,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后,曾普遍出现被圈地运动驱赶出的农民不愿到工厂就业的情形。人们在工厂挣够每周的生活费后,就不去做工了。因为工人怠工是普遍现象,许多工厂的注册工人的人数是实际工作人数的两倍。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1817年,马撒诸塞州Medford的一个造船商因为取消了工人的上班饮酒特权,工人全部辞职(Robert Schrank,1979)。现在欧美工人的敬业精神也是大工业造就的。 (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命题妨碍了对文化问题的实证研究 笔者反对某些论者夸大民族间行为文化的差异,但并不否认这种差异。笔者只是主张对行为文化的差异要作实证研究,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用虚幻的概念联系来替代客观的真实联系。 中国学者研究文化差异问题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来自揭破“李约瑟之迷”的诱惑,这原本是无可指责的。“李约瑟之迷”实质上是民族命运之迷。民族命运无疑与民族的文化传统(绝不仅仅是典籍文化的传统)有关,但绝不仅仅与此有关。论者多抓住一个事实片断,甚至抓住一部文化典籍中的某个符号,便以为发现了民族命运的某种基因而陶陶然乐在其中。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少学者在传统文化问题上妄自尊大(以当代新儒家为代表),似乎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祖宗都曾有过,而外国一切不幸祖宗都早已料定。一位著名学府的“文化大师”竟言之凿凿,说伊拉克的战败是因为不懂得中国古人讲的“兵不厌诈”,其无视事实、囿于纸面学问的拙劣触目惊心。 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幻觉可能与中国人的治学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治学态度有关。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化典籍是一个大大的故纸堆,终生修学不尽;其中自有颜如玉,自有黄金屋。儒学是一个大泥潭,而对儒学的社会需要则是饕餮之徒;人们一旦栽了进去,信息获取便永远得不到饱和,而其他信息便没有时间去获取。于是,一个儒生便益发迷恋故纸堆,并由此幻觉出一个虚假的民族精神出来,而这个民族精神是绝不能与其他民族共同享有的,否则,终生的学问投资便要化为乌有,岂不痛惜!民族文化差异的观念一旦形成,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治学态度,要人们益发热情高涨地去啃故纸堆,实证研究态度便到爪哇国去了。 三 上述夸大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把民族命运归结为这种差异的假命题,派生出了其他一系列假命题。下面拟扼其要者作一评论。 (一)“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本体文化” 对这个假命题本文事实上已经作过某些评论,下面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讨论。 我国学者许纪霖、朱学勤先生对中国儒家文化有过深刻分析。诚如他们所说,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倡导“天下为公”(《礼记》),给人制定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道德标准和追求“千年至仁之人极”的社会理想。但这套说教“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搞出来的理论多少偏于炽热的情感,而缺乏客观、冷静的知识论支持”(许纪霖,1990)。这套伦理价值观被用来诠释政治,结果是“以道德规范代替政治设计”,创立了一个“内圣开外王”的假逻辑(朱学勤,1990)。他们还认为,在欧洲文化中,说教功能主要由教会来承担,而民间却保留了对客观事物进行实证研究的传统。他们的这些论点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我们不能在官方倡导的儒家文化与实际的民间文化之间简单地划一个等号;真正的民间文化与其在典籍中去找,不如在野史或民间话本中去找。作一比较,会发现《儒林外史》、《红楼梦》与欧洲近代小说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并无重要差别。 如果作深入分析,这个命题的虚假性并不在于把儒家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的本体文化,而在于把儒家典籍的一部分内容,即“以仁为本”的内容与中华民族的本体文化等同起来了。事实上,儒家典籍还有不少与“以仁为本”完全相反的内容,这就牵涉下面一个假命题。 (二)“儒家学说‘以仁为本’” 儒家学说“以仁为本”的虚假性为许多论者所忽视。无疑,在孔子的学说中包含了大量“以仁为本”的思想,但也有不少与此相反的重要思想,只是后一种思想在后来被统治者及其御用理论家给扼杀了。朱伯昆先生就曾指出,儒家学说包含了功利主义传统(朱伯昆,1994)。 《大学章句》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排列着“物格、知至”的训导,意在强调研究客观事物。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去远也”(《论语》,阳货篇),很接近贝克尔关于人的偏好与行为的分析。他的“执柯以伐柯”(《中庸章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也很接近马基亚弗里的思想。他评价求(人名)“不知其仁”,却认为这个人“可使为其宰”(《论语》,公冶长篇),说明他对为政之道持有非价值观的看法。孔子虽然倡导以“仁义”治理天下,但他却往往以利己人假说来判断事物发展的后果。子贡从诸侯国赎回一名鲁国人,但却推辞应得的酬金。孔子批评说:这次你就做得不对了,酬金是为了奖善,取酬金无损于你的德行,而不取酬金今后鲁国人就不愿意再赎人了。另据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感谢他,子路欣然收下。孔子评论说,从今后鲁国勇于救人者会越来越多(《孔子家语》)。这两件事说明,孔子对一般人作“性恶”的评价(与孟子不同)。另一被人们看作是儒家的政治家管仲,大体上也持这种看法。在儒家学说的后来发展中,有陈亮、叶适、颜元和戴震等人继续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只不过不能占主导地位而已。 中国古代其他一些重要文化典籍也有类似的实证分析思想。《吕氏春秋》云:“名号大显,不可强求,必繇(用)其道。治物者不于物,于人;治人者不于事,于君;治君者不于君,于天子;治天子者不于天子,于欲;治欲者不于欲,于性。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乃天地之数也”(《吕氏春秋.不苟论.博志》)。这一段话所言“性”,虽已超出了我们这里所讲的人性范畴,但从行文前后看,无疑包括了人性,这个思想与现代经济学的“利己人”假说相当一致。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类似记载不胜枚举。 从另一方面看,欧洲古代先贤们也不只是注重实证分析而与价值分析无缘。事实上,他们的学说也包含了“以仁为本”的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写了《理想国》,而“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钟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马克思,1867,1-405)。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提供的东西大体上也是一种规范分析,在科学方法上并不比孔子高明多少。他认为获取利息是非自然的、最坏的行为,完全是从价值观出发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与孔子运用的语言符号不同而已。他的这个结论在后来成为中世纪教会借贷取息的理论武器。 概括地说,中国和欧洲早期学者的思想都有丰富的发展可能性,都有“以仁为本”的思想,也都有实证分析的科学精神。为什么中国与欧洲后来的主流理论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呢?答案仍离不开对中国和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自然基础的实证分析,限于本文篇幅,这只能留在以后进行讨论。 (三)“中国文化传统以‘天人合一’为宗旨” 儒家文献中的“天人合一”主张被某些现代论者看作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传统,并认为欧洲文化传统与此相反,是人与自然的对立。有人甚至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所在。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天人合一”充其量是儒家典籍的某种主张,由此断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独有传统,是绝对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正如我国学者罗卜先生所指出的,在把握主客关系(“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东西哲学及文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罗卜,1994)。中国古代就有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之说,而欧洲近代则有培根主张以人类而知识进步实现对自然的征服。“天人合一”文化传统论更不能解释当今现实。中国这样一个有“天人合一”文化传统的国家其环境污染已经是触目惊心,而有天人相争文化传统的欧美国家却在大力保护环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难道是它们各自背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一种真正的文化传统难道就这样不堪一击,轻易会被背离?如果一种文化连自己都救不了,又何谈拯救人类,侈谈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文化是中国文化”?显然,论者的逻辑地位是及其脆弱的。 (四)“儒家学说导引了东亚、东南亚经济奇迹” 这个假命题是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内涵。二战以后,日本经济率先出现高增长,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经济奇迹。近二十年,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经济也在崛起,令世界瞠目。面对这个辉煌,学者们当然要作“研究”,政治家们也要给出一个说法,要找出其中的奥秘来。找来找去,要看什么东西我有,而欧洲人没有,最醒目的当然是“儒家传统”了,这似乎很合乎逻辑。“国学大师”或自认为是“国学大师”的先生们喜欢这个说法,在这里,“儒家资本主义”可能是次要的,曾经倍受冷落的看家学问突然间显赫起来才是要害。当然,维护道统是要挂在嘴上的,不然何以惑众?政治家也当然喜欢这个解释,想想看,儒家传统在近千年里变成了书斋里的供品,而对其发源地中国社会的衰变则一筹莫展,爱莫能助,突然在近几十年里由几位英明的政治家力挽狂澜于大厦将倾之时,使儒学发扬光大,由“精神变物质”,政治家自然顺便可登堂入室,由凡人变为当代圣人,这是何等的荣耀!于是,学者和政治家奏响了复兴儒学的交响曲,高扬起儒学统治21世纪的旗帜。一时喧闹,竟也成了气候。 其实,这个命题在逻辑上并非无懈可击。类似东亚的奇迹早在两百年前的欧洲已经出现过,翻开《共产党宣言》,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当时英国经济成长的赞叹。为什么儒学令东亚奇迹姗姗来迟,难道因此需要指责儒学?不论当今的东亚奇迹,还是以往的欧洲奇迹,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跳跃式技术进步加上资本积累推动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至于东亚奇迹的出现晚于欧洲,则与技术进步的社会条件形成较慢有关,后一原因又有其历史逻辑。如果说有什么文化传统帮助东亚经济崛起的速度更快一些,也恐怕与“有教无类”的历史承因有关,但这也不取决于孔子的倡导,而取决于东亚的传统社会结构。揭示这些关系还需要更深入的实证分析。 相当一些文化研究者也许由于抽象思维力的欠缺,总是忽视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共性,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也染上这个毛病。曾几何时,经济学家还在赞叹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但日本人在几年前发现这个制度有了问题,要改。文化研究者信息滞后,有的还在赞扬它,还说这是“以仁为本”的思想的体现。又曾几何时,经济学家炮制出一个东亚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还没等这个“理论”炒热,突然出现了一个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少数危机不重的国家或地区也顾不上什么推己及人的儒学传统,眼看邻居失火,也不去救一把。这种理论上的笨拙,已经到了滑稽的地步。倒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给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出了解救药方,但也无非是促进经济自由化,减少国家干预这几味常见药。笔者由不得又想起马克思引述过得话:“这里就是罗斯陀,就在这里跳吧!”亚洲的金融危机就是“罗斯陀”,传统文化如果能治病,就在此时大显身手吧,何必要等到21世纪! 四 关于文化研究,真正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传统文化典籍对人民发挥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估价这种教化作用。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当前充满假命题的文化研究不仅不能给我们以帮助,反而徒增害处。这也是历史经验。 正统的儒家文化传统从教化人民、改造社会的功能上看,其意义是十分有限的。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但政府和学者们常常倾向于夸大这种教化作用,而一旦作用没有实现,便茫然不知所措,乃至导引出反传统思潮。这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困境所在。面对这个基本困境,诸如“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之类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要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作深入讨论。 政府和学者进行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主要在于制造和传递某种信息,整合大众拥有的那些零碎的关于行为合法性的意识,使之系统化,统一化,并变得更方便交流,其作用恐怕仅此而已。行为合法性意识的内容,即意识形态的内容,主要通过家庭教育以及人的后天生活过程中发生的人际博弈来形成。行为合法性意识的形成甚至与受教育程度无关。人类行为学的研究,包括本文前面介绍的例证,都证明了这一点。 任何一个社会均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即社会大众拥有并认可的一种系统的关于行为的合法性意识。意识形态离不开政府与知识界的推动,但不能认为政府和知识界可以任意进行意识形态操作。能够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必是在运作中社会成本较低、而社会功能较强的意识形态;否则,任政府怎么操作,被操作的意识形态都不会被社会所接受,或只有被接受的假象,而事实上成为衙门与书斋里的供品。即使推广一种功能卓越的意识形态,其操作本身也有一个成本问题。 从意识形态操作的角度看,一个政府依其目标在建立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若立足于给公民传递“不应该做什么”的信息,并辅以对违规行为的制裁,意识形态构建的成本会相对低廉,新加坡实现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正原因正在这里,而不是什么“以仁为本”。但若政府立足于给公民传递“应该做什么”的信息,并将这种信息教条化,且树立榜样以供仿效,则意识形态构建的成本会相对高昂。因为应做之事的潜在范围广大,与戒条相违与否的监督成本高昂;而不该做之事的范围可以比较确定,对违规行为监督的成本相对低廉。后一种情形下的政府目标容易转变为法律,而前一种政府目标只能通过劝戒来实现,公民逃避较为容易,因此说谎和失信客观上得到鼓励。此外,公民之间的信息结构与禀赋不同,偏好也因此不同,进一步说,决定其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点也不相同,若只告诉其应该做什么,多数公民就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进而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也将不能实现。 中国儒家文化典籍中的有些伦理内容明显地反映了秩序化社会中民众行为文化的实际运行状态;在秩序化社会中,它不仅会为中国人所奉行,也会为西洋人所遵守。但正统儒家学说的错误在于把它奉为永恒不变的“道”,而对其功利意义缺乏认识。这种学说在科学史上没有价值。除过这些伦理内容之外,孔子的许多关于为人处事技巧的分析很精彩,表现了其很高的心理学造诣,为后人称道亦理所当然。问题在于恰恰是儒家学说的伦理内容变成了官方操作的对象,成为治国工具,甚至到后来获得独尊地位,成为科举考试中的进身之阶。这种操作注定产生虚伪性,使儒家典籍变成一堆对于大众行为文化意义不大的文化符号,甚至变成专制王朝的文化包装。因为在社会动荡时期,民众必然普遍地奉行机会主义行为,政府的道德劝说无法起作用;而在有序社会中(如村社共同体和现代法制社会),不用政府劝说,民众自会奉行合理(也合乎伦理)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本来隐藏在民众之中。所以,正统儒家文化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由政府操作在本质上是效率很低的,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只是表现在政府形象的塑造方面,或者如前所说,也只是能够加速文化符号的传播,降低语言交流成本。 在社会动荡时期用正统儒家教义来教化民众,孔子为我们提供了不成功的教训。《论语.雍也》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亲传三千弟子尚且如此,罔论其余“小人”如何。孔子仙逝,若干弟子继续传道讲学,到了子思时代,世风仍不见好转,子思喟叹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其他历史时期也是如此。我国学者谭其骧先生历数儒学炽盛的各个时代,均为积贫积弱、人欲横流的时代,并得出结论:“儒学对当时世风、政治无补”(1994)。 现代史上不少国家花大力气给国民灌输所谓“科学世界观”,以期对国民意识进行根本改造,由此也踏入了一个经世济国的误区。首先,给一种学说冠以科学世界观,将其绝对化,本质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即论有科学世界观存在,它也不能替代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更不能消灭人之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也不可能靠科学世界观消灭人的宗教感情。最后,科学世界观的形成要一大量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为前提,而这是需要成本的。在谋生知识的获取也无足够财力保障的情况下,难以想象国民会为了什么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投入时间和财力。在象征科学世界观的某些文化符号的掌握不再成为人们政治上进身阶梯时,社会出现对这套文化符号的蔑视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改造一个社会,使之变得有序、和谐,要靠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来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使人们之间的合作成本降低,而只要合作成本足够低,理性的人们就会找到合作的方式,并掌握合作的规则,其表现便是全社会的和谐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是逐步进化的,因为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是逐步实现的。我们当然欣赏“千年至仁之人极”的境界,也欣赏“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新儒家理想,但实现这些目标不能靠“继往圣绝学”来实现,而要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党国英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