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华莘
本文是2020年11月20号《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期刊发表的纽约大学Sterns商学院系列研究论文之一的《Responsible Investing: The ESG-Efficient Frontier》的翻译文稿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和总结ESG投资的资产定价模型和归因分析。

三、ESG的均衡资产定价 (Equilibrium asset pricing with ESG)
3.1 ESG调整后的CAPM
(注:这个部分内容主要是纯学术的理论建模,涉及很多数学公式,故下文以图像显示。这个章节讨论了三类ESG投资者的信息偏好对CAPM均衡价格的影响。)




该均衡方程如下图所示(详见附录)
3.2可验证的理论预测结论
总而言之,上述的ESG-SR有效前沿理论模型做出了以下几个预测:
1)风险、预期收益率和ESG之间的选择集合是可以通过ESG-SR前沿来总结归纳的。
2)利用ESG信息并通过可以改善 ESG-SR前沿来增加投资者的Sharpe Ratio。
3)基于投资者的信息集,具有较强ESG偏好(或者较高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应该选择具有价高ESG得分和(边际)略低的Sharpe Ratio的投资组合。
4)即便是偏好平均ESG得分的投资者,其也应该最优地选择在几乎所有证券中都具有头寸(多头或者空头)的投资组合(相对于偏好的歧视性的标准模型所隐含的更严格分离要求而言)。
5) ESG投资者应该选择以下四个资产的组合:无风险资产、标准切线组合、最小方差组合和ESG切线组合。
6)ESG得分较高的证券应该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a.ESG投资者的需求增加,将会降低该证券的预期收益;
b.不同的预期未来利润,如果市场对基本面的这种可预测性反应不足,则可以提高预期收益;
c.潜在的来自投资者的更多的资金流,可能会在短期捏提高证券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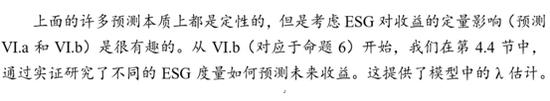

四、实证研究结果(Empirical results)
4.1 ESG度量与数据
ESG是一个广义且笼统的术语,因此,本篇论文考虑了四个替代变量指标变量,它们涵盖了ESG的不同方面。本文的目的不是在它们之间做对比,而是讨论市场会如何定价ESG的不同因子,并以此举例说明本文的理论模型如何为ESG投资者提供指导和帮助。
本篇论文使用的四个ESG替代变量指标变量是:
1)环境(E)的度量:低碳强度(low carbon intensity)。为了衡量一家公司的“绿色”程度(即ESG中的E),本文计算其碳强度(CO2),并定义为碳排放量与销售额的比率。碳排放量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衡量,本篇论文使用的是“范围1的碳排放量”(公司的直接排放量,例如:来自公司自身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直接排放量)和“范围2的碳排放量”(购入能源的间接排放量,例如电)。本篇论文不包括“范围3”(其他间接排放量),因为这些排放量很少被公司报告,并且在不同的数据提供商的估计是不一致的(例如Busch,Johnson和Pioch,2018年)。本篇论文在CO2变量前加个负号,以便更高的因子值表示更好的ESG(碳强度越低,越是“绿色”的公司)。这些数据来自Trucost,可获得数据的时间跨度2009年1月到2019年3月。
2)社会(S)的度量:非罪恶股票(Non-sin stock)指标。一些对ESG敏感的投资者回避某些“罪恶”行业的股票,例如烟草、赌博或酒精(与ESG中的S有关)。本篇论文考虑一个“非罪恶股票”指标,对于有罪股票,取0值,否则取1,因此较高的值表示更高的ESG得分。在Hong和Kacperczyk(2009)的文章中定义了罪恶行业,这一指标适用于本篇论文最长的样本期,即1963年1月至2019年3月。
3)治理(G)的度量:较低的应计项目|利润(Low Accruals)。本篇论文使用一种可根据会计信息在较长样本期内计算出的治理指标。具体来说,本篇论文查看每个公司在1963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应计资产项目|数值。应计项目|利润实质上是尚未收到相关现金的会计收入。本篇论文在应计项目前加负号,以使较高的因子值表示更高的ESG得分。从会计文献中得出的想法是,应计项目|利润低表明企业对利润的会计处理较为保守(例如Sloan,1996年),而治理较好的公司则倾向于采用更为保守的会计流程(例如Kim等人,2012)。实际上,经验研究表明,受到SEC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公司往往在被采取此类措施之前具有异常高的应计项目|利润(例如Richardson,Sloan,Soliman和Tuna,2006年),而应计项目|利润较高的公司也有较高的利润重述可能性(例如Richardson,Tuna和Wu,2002年)。
4)整体ESG的度量:MSCI 的ESG评分。机构投资者最广泛使用的ESG得分之一是由MSCI计算得出的,此变量的样本期是从2007年1月到2019年3月。MSCI给出的评分是对每家公司ESG概况的综合评估。本篇论文在行业调整的基础上,整理每家公司E、S和G特征的总得分,评分范围为从0(最差ESG)到10(最优ESG)。
本篇论文将上面这些数据集与以下其他相关数据或模型结合使用:包括XpressFeed数据库(用于股票收益和市场价值),Compustat数据库(用于计算公司基本面),13f持仓报告(由Thomson Reuters汇总)中的机构持仓头寸,由日内数据计算出的下单量,以及用于计算ESG有效前沿的Barra US Equity(USE3L)风险模型。
4.2 ESG-SR前沿的实证研究
使用前文的方法,本篇论文计算了两个ESG替代变量(E和G)的ESG-SR前沿。本文没有为S因子构建ESG-SR前沿,因为此变量是0-1二元变量(罪恶股票/非罪恶股票)。为简便起见,本篇论文也忽略了整体ESG的前沿,因为它与E的前沿类似。
从基于CO2排放的环境替代变量的ESG-SR前沿开始,图4分别从不了解ESG和了解ESG的投资者(分别为实线和虚线)的角度显示了S变量的有效前沿。此外,本篇论文区分了所谓的事前感知前沿(图4.A, Ex-ante)和已实现前沿(图4.B, Realized)。对于前者,投资者每月都要按照先前的定义计算风险和预期收益,然后得出ESG-SR前沿和相应的有效前沿投资组合。图4.A 仅显示了这些感知前沿的时间序列平均值。图4.B的事后前则沿显示了这些投资组合的已实现夏普比率。
图4:用碳排放作为E的替代变量的ESG有效前沿

资料来源: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图4.A中的两个ESG-SR前沿非常接近,这表明本文使用的环境替代变量对解释平均收益不是很有帮助。而且分布模型在事实上也证实了这两个前沿在碳得分为0附近达到峰值,这表明投资者在A和B切线投资组合中的样本股票的碳排放约为平均水平(本篇论文在4.6节的回归框架中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当查看图4B时,这一发现更加惊人:两个前沿彼此重叠,这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碳强度水平下,两个前沿上的投资组合的夏普比率基本相同。
但更重要的是,即使ESG替代变量对预测组合收益不是特别有用(如图4所示),ESG-SR前沿仍然有意义。例如,本文可以使用有效前沿来量化M型投资者面临的选择取舍,他们愿意牺牲一些夏普(Sharpe)比率来改善其投资组合的ESG状况。在图4B的背景下,此类受ESG激励的投资者寻求碳排放量更少的投资组合(绿色投资组合)。从切线组合向右移动两个单位(即向更绿色的投资组合移动,以使投资组合中的样本股票向“更绿色”的方向移动两个标准差)会使最优夏普(Sharpe)比率降低约3%。夏普比率的这种适度降低可能是一些ESG积极的投资者为如此大幅度减少CO2而付出的代价。当然,如果投资者进一步推动绿色投资组合,那么其所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例如,从峰值移动4个标准差会使夏普比率降低约10%。
图5展示了使用了G(治理)替代变量下的ESG有效前沿。不了解ESG的投资者的前沿与了解ESG的投资者的前沿非常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本篇论文的G替代变量预测了样本中的收益回报(如4.6节中进一步讨论)。为了理解图5.A,我们首先注意到,不了解ESG的U型投资者在ESG得分为0.25时使夏普(Sharpe)比率最大化,这意味着其投资组合中的样本股票接近该ESG度量的平均值。这里的ESG几乎是中性的,并不奇怪,因为U型投资者仅使用价值因子(Price-to-book ratio)的信息,而对G的任何敞口只是偶然地通过PB ratio与G之间的弱相关而产生的。
图5:用Low Accruals作为G的替代变量的ESG有效前沿

资料来源: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此外,这个Ex-ante前沿是在0附近对称的,这意味着该投资者认为以正的G得分值为目标的成本与以同样幅度的负得分值为目标的组合成本相似。例如,将G得分定位为比最优情况高两个标准差(即从0.25变为2.25),则会使U型投资者的夏普比率降低约9%;而以G得分为目标,将G得分定位为比最优情况低两个标准差(即从0.25变为–1.75)会使夏普比率降低7%。
相比之下,A型投资者的前沿却截然不同。如图5.A所示,前沿在G得分为2.25时达到峰值,这意味着,对于意识到ESG的投资者而言,最大化夏普(Sharpe)比率意味着要寻找G得分值远高于市场的投资组合。而且,A型投资者的ESG-SR前沿显然是不对称的,这表明降低投资组合的G得分对夏普比率的影响要比增加G得分的影响大得多。例如,从最优点的两倍标准差的增加(2.25到4.25)会使夏普(Sharpe)比率降低约3%;在相反方向(2.25至0.25)进行类似移动的D代价是9%,是3%的三倍。
图5.A中的前沿相交是由于以下原因:让A型投资者接受负ESG得分要比U型投资者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A会考虑到G对于收益的正向预测作用。两条曲线在G得分大约为0的位置相交,这个解释也是很直观的,因为此时的最优投资组合对于两个类型投资者(A型和U型)而言基本相同,因为他们都无法获得他们不同意的G得分。
图5 B展示了构成图5 A有效前沿的ESG投资组合的已实现夏普(Sharpe)比率。从图形和数据来看,A型投资者的已实现的前沿(Realized frontier)与他们的事前感知前沿(Ex-ante frontier)非常相似,这是因为驱动有效前沿的ESG得分被明确纳入A型投资者的收益预测中,并且本篇论文的事前风险和期望收益模型可以很好地捕捉事后实现的收益。
相反,U型投资者在图5B中的已实现前沿与其在图5A中的Ex-ante前沿具有不同的形状,这是因为U型投资者忽略了G变量可以预测收益。U型投资者的已实现ESG-SR前沿看上去与接近0值ESG得分的A型投资者的前沿类似,这是因为他们的投资组合在该范围内更相似。但是在其他ESG目标中,U型投资者选择投资组合时是在市场风险敞口、价值和G变量得分之间进行次优选择。
图5.B还展示了使用基于G (治理) 的ESG投资组合的成本和收益。使用G变量信息的好处可以通过查看A型投资者的已实现的夏普比率来衡量,这个SR值要比U型投资者的已实现SR高出11%(在图5.A中则高出12%)。与之相比,M型投资者使用G变量信息的偏好成本可以用SR值的降低幅度来衡量,即当目标ESG得分高于A型投资者时,夏普比率会有所降低。
ESG投资实证研究:组合有效前沿与资产定价归因之三
【接前文】 本文是2020年11月20号《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期刊发表的纽约大学Sterns商学院系列研究论文之一的《Responsible Investing: The ESG-Efficient Frontier》的翻译文稿的第三部分,主要讨论和总结了筛选法,以及不同ESG因子对公司基本面、投资者需求、交易活跃度、证券估值和预期收益的统计回归分析与实证结论。
四、实证研究结果(Empirical results)
4.3限制条件的影响:筛选ESG最差的股票
到本章节为止,前文的实证研究和模型应用已经可以指导投资者将资金配置在不受限制的ESG投资组合中,而且可以做多或者做空任何股票。
但下文的内容将考虑对ESG敏感的投资者( ESG-sensitive investors)所面临的现实限制和限制条件。在这些组合投资限制中,最常见的是筛选出ESG特征最弱的股票(即通常所说的筛选法,从可投资范围里删除此类股票)。图6显示了如果应用前文在图5中使用的与G(治理)相关的替代变量时,股票筛选法对ESG-SR前沿产生的影响。图6显示了三个不同的ESG-SR有效前沿:1)用于不受限制的投资者A(与图5A完全相同);2) 是投资者除去具有最低ESG特征的10%的股票;3)是去掉20%具有最低ESG特征的股票。
直观的观测就看得到明显的结论:ESG的排除限制条件会降低投资组合的预期绩收益。筛选比例为10%的ESG组合有效前沿明显低于不受限制的投资组合的ESG-SR前沿,而筛选条件为20%的组合有效前沿则更低。这意味着,对于任何期望的ESG得分水平,在筛选后的股票集合中国最大可获得的夏普比率将低于不受限制股票集合的最大可获得的夏普比率。
图6:股票筛选法对ES-SR有效前沿的影响

资料来源: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更有意义的发现是,夏普(Sharpe)比率降低的幅度。为了确定夏普比率降低幅度的比较基准,一个有用的经验法则是,在某些假设下,夏普比率与股票数目的平方根(the square root of investment breadth)呈现近似线性的关系(Grinold和Kahn,1995年)。这意味着股票数量减少10%(20%)会使夏普比率大约降低5%(10%),即这也致相当于ESG得分下降约–0.5的幅度(The Magnitude of Penalty,惩罚幅度)。当ESG得分接近零值的时候,这个夏普比率的惩罚幅度只有基准度量的一半左右,这是零ESG得分意味着最优化的组合里不会包括ESG得分非常低(或者非常高)的股票。而ESG得分显著大于零的时候,这个夏普比率下调幅度则明显高于根据经验法则的平方根得出的惩罚幅度。例如,假设投资者寻求获得较高的ESG得分,则剔除ESG最低的20%的股票会使组合夏普比率降低25%以上,而部分原因是卖空低ESG的股票带来的好处。
从图6得出的另一个相关发现是,在剔除最差的ESG评级股票之后,夏普比率最高的投资组合(切线投资组合)的ESG得分较低。如前文所述,不受限制的投资者A在投资组合的ESG得分值为2.25时,夏普(Sharpe)比率得到优化。当剔除10%的ESG最低的股票后,夏普比率则在ESG得分为1.5时,达到最大化。而当去除20%的ESG最低的股票后,夏普比率则在ESG得分1时,达到最大值。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实证结果, 这意味着,与那些允许在组合里纳入这些有着较低ESG得分的资产的投资者相比,将低ESG评级资产排除在其投资范围之外的投资者,却更可能会以更低的ESG得分建立其最优投资组合。这一发现实证背后的逻辑直觉是,低ESG资产是有效的组合资金来源,因为市场允许不受限制的投资者做空这些资产,从而得以建立更大的高ESG评级的证券多头头寸。
此外,低ESG得分的资产可能是高ESG得分资产的有效对冲工具,并有可能通过增加对高ESG证券的投资来帮助投资者提高整体投资组合的夏普比率。通过筛选法,投资者可以最优地选择不让高ESG得分的资产在组合中占据过大的头寸。
4.4实证研究:ESG可以预测未来的基本面吗?
同经济学的其他信息价值一样,ESG信息能够产生正的超额收益的必要条件是它与未来的基本面相关。为了测试这种可能性,本篇论文将ESG替代变量与未来的基本面相关联,并在图表7中考虑了两个基本指标变量。在图7A中,本文考虑了“会计收益率”(accounting rate of returns),这是Richardson等人(2006)定义的净经营资产收益率。在图7B中,“资产毛利率”定义为收入与销售成本之差占总资产的比例,如Novy-Marx(2013)所述。在图7A和7B中,这些公司的基本面信息均在ESG变量之后的12个月进行了测算,并用这些未来12个月的盈利数据与现有的ESG因子评分进行统计回归分析。另外,对于第4.1节中定义的四种ESG替代变量中的每一种,本文提出两种计量规范:1)基于具有确定的月度影响值,且标准误差聚集在公司层面的汇总样本;2)基于Fama–MacBeth程序和Newey–West标准方差。最后,本篇论文还控制了公司的beta,规模和市净率等变量和,尽管这些控制变量对本篇论文的结果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图表7中的(1)和(2)列的回归分析使用本文的E替代变量。本文发现,碳排放指标可以预测图7A组的会计收益率(碳排放越低,会计收益率越高),但是对于图7B组的毛利率而言是不显著的预测变量。因此,结论是本文所用的E指标可能与基本面没有密切关系。对于本文的S替代变量,我们发现的结果也有些不同。7A和7B的(3)和(4)列回归分析得到的负值系数都表明,“罪恶”股票具有相对较强的未来基本面,这结果与Blitz和Fabozzi(2017)一致,但这些统计仅具有边际意义。(7)和(8)列的回归分析表明MSCI的总体ESG得分与未来的基本面呈正相关,但仅在7B中具有统计意义。
图7:E、S、G因子评分可否预测公司利润?

资料来源: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在(5)和(6)列的回归分析中,对于本文的G替代变量(Low Accruals, 应计项目|利润)的统计结果是最显著的。图7A中的这些具有高度统计意义的数据也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即,相对于每一个标准方差的增加应计利润(负数),会计收益率将相应地增加0.02,或者在0.1的平均水平上提高20%。这一发现为稍后在本篇论文将确认的,应计利润可能包含未来基本面的有关信息提供了可能性,而且这些基本面可能无法被市场完全定价(类似于Richardson等人在2006年的发现)。图7B中的对应回归值也展示了资产毛利率的结果。我们看到较高的G得分预示着未来的公司盈利能力会有所提高,但这个变量的影响相对较小:应计利润每移动一个标准方差,毛利润率变动0.006,约为该变量平均水平0.3的2%左右。
另外一个发现是,G替代变量的结果对于各种控制变量都具有统计稳定性。例如,虽然各个行业的应计利润可能会有差异,但是将行业虚拟变量添加到回归分析(5)中,则不会改变系数(系数从0.208略微增加到0.209,t统计量为22.6 vs. 23.3)。同样,在没有控制公司规模,市净率或Beta的情况下进行回归统计,或在没有日期固定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回归分析,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很小。最后,即使在测量应计利润后的24或36个月的时间段里,本文的统计结果也对会计收益和盈利能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存在着强有力的统计证据表明,应计利润与未来的盈利能力相关。
4.5 ESG可否预测投资者需求?
正如前文在理论与模型部分所解释的那样,与公司的未来基本面的相关性本身不足以确定ESG变量是会提高收益还是降低收益。因此,从整体上看,还需要分析投资者对ESG的需求。在本节中,我们将考虑机构所有权、交易活动和签署的订单量,以捕捉投资者对拥有或购买特定一类股票的兴趣。
图8A:E、S、G因子评分可否预测投资者需求?

资料来源: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图8 A使用了与图7类似的设置,即基于3个月前的ESG指标来预测机构投资者持有量(以13f数据为基础,以百分比为单位),当然这里采用“3个月”的时间段是为了确保观察到ESG变量的时间点早于机构持仓数据的财务披露时点。机构投资者(基于13f数据衡量其需求)似乎在构建其投资组合时已经纳入了ESG信息,尤其是本篇论文所选用的四个ESG替代变量都与机构持股正相关。而且这些ESG变量的经济学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E(添加负号的CO2强度)变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导致机构持有比例增加1.3%,即机构倾向于持有绿色企业,G变量对应的持有比例增加值为0.3%-1.3%,而ESG总体对应的数字为0.6%-0.8%。至于本文的二元S替代变量,从有罪股票向非有罪股票的转变意味着机构持有量增加了6%–7%。
图8B:E、S、G因子可否预测交易活跃度?

资料来源: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图8 B和C考虑了交易活动的度量(交易笔数的对数值)和已签定的订单数(买单的总金额占比)。为简洁起见,本文仅报告了具有日期固定效应的合并回归分析(Fama–MacBeth证据与此类似)。对于G变量(应计利润)来说,其统计结果也许是最直观的,因为数据显示应计利润得分(已乘以负号)改善时,交易数量和买单比例均明显增加。但是,对于其他三个指标来讲,统计证据并不那么直接。对于碳强度低或非罪恶股票,交易次数似乎有所减少。对于碳强度低的股票,本文还可看到买单比例的下降。
图8C:E、S、G因子可否预测买方订单数占比?

资料来源: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4.6 ESG可以预测估值和未来收益吗?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买卖股票除了基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另外一个重要参数就是证券估值水平,二者高度相关。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至少有一些ESG替代变量(例如G)与未来的基本面密切相关。同时,本篇论文也发现一些证据表明,投资者倾向于将其ESG组合投资于G评分更具吸引力的股票。正如在前文的理论部分所显示的那样,这两种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导致收益溢价或折价,具体取决于哪种效应更强。
相对于E、S和整体ESG的替代变量,该收益和需求预测可能更容易做出,因为本篇论文发现这三个变量(E、S和整体ESG)与未来基本面以及投资者需求的相关性较小。因此,我们的理论表明,具有良好E,S或ESG整体评分的股票应该比具有良好G的股票更昂贵,并且具有较低的未来收益。为评估这些预测,本篇论文在表3和表4中考虑了估值(Tobin’s Q)和风险调整后的收益。
图表9显示了ESG替代变量与市净率(PB)对数的关联性。因为本篇论文的兴趣在于找出市场愿意为ESG特征付出多少价格,所以本篇论文分析了同期估值(contemporaneous valuation)与ESG替代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篇论文控制了市场beta变量,但本篇论文已忽略先前使用的那些按市场结构估算(如公司规模、资产的市值净价等)相关的控制变量。
图9:E、S、G因子与估值(市净率)

资料来源: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图9中的第(1)列回归分析表明,E评分较高的股票(即低碳强度的股票,绿色股票)的价格相对高于棕色股票(高碳股票)的价格,而这与前文记录的投资者对E相对较高的需求是一致的。当在第(4)列的回归分析中使用总体ESG指标(来自MSCI)时,我们发现类似的统计模式。相反,在第(2)列的回归分析中使用S替代变量时,本文发现有罪和无罪股票之间的估值没有显著差异。
最有趣的是第(4)列的回归分析,这表明G变量(应计利润)可能未被市场定价。实证结果还表明,尽管G变量预测获利的能力较强,但G分数较高的股票的估值却较低,因此这意味这此类股票产生诱人回报的可能性将被打开,而且本篇论文在下面的实证研究将确认这一点。
图表10显示了ESG替代变量对证券收益率的预测能力。基于本文是四个ESG替代变量,我们每月将股票组合分为五个排列分位(对于有罪/无罪指标,则分为两个投资组合),并构建多空组合(买入ESG 得分最高的股票,卖出ESG得分最差的股票)。图表10列出了在控制各种资产定价因子的情况下,基于平均权重和市值加权所构建的ESG投资组合的最终表现。
基于G变量的投资组合具有较高的超额回报(alpha)。即使在控制了五个Fama-French因子之后,G变量的超额收益率依然显著,其在平均权重权组合的年收益率为7%,而在市值加权组合的年收益率为3%。这一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前文(4.2节)的实证结论,即G(治理)指标对于那些即使已经在其投资组合决策中使用多个其他投资因子来构建组合的投资者也有较大的意义。
与之相比,对于E和整体ESG评分的替代变量来说,本篇论文发现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现这两者可以产生超额收益。在本篇论文的样本期间内,基于统计学的点估计(point estimate),似乎碳排放强度得分较低的公司的相对表现较好,但超额收益也仅在10%的水平上才统计显著。本文注意到这与Bolton和Kacperczyk(2019)的研究发现一致,两位作者发现了碳排放的溢价,但这个溢价在更细致的统计分析设定中则消失了,例如在控制行业构成时。
图10:E、S、G因子可否预测收益率?

资料来源: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最后,本篇论文找到了Hong和Kacperczyk(2009)论文所记录的“有罪溢价(The sin premium)”的一些证据。因为本文考虑的是多空组合,即做多非罪恶股票(ESG较高的股票),同时做空罪恶股票(ESG较低的股票)。因此,有罪收益的溢价将被反映为负的超额收益(alpha)。本篇论文发现对于市值加权组合来说,每年的有罪溢价可达4%,但是对于平均权重组合以及五因子或六因子模型来讲,该溢价很小,甚至微不足道。本文这一发现与Blitz和Fabozzi(2017)的发现一致。另外,本篇论文的结果比Hong和Kacperczyk(2009)的结果显著性弱,这可能是由于统计方法和样本期间的差异所致。
五、 本文结论总结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ESG理念和投资观点纳入他们的投资组合中。简而言之,这些投资者只是想以道德的方式持有道德的公司,以促进良好的公司行为,同时希望以一种不会牺牲回报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因此,投资者必须切实评估ESG负责任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本篇论文的理论和模型框架可以用于有效地概念化和量化这些ESG因子带来的好处和代价。本文的研究表明,可以通过ES-SR有效前沿(投资机会集的图形化展示)来概念化ESG投资者的选择和决策后果。
总体来看,ESG偏好的好处是,可以量化为最大夏普(Sharpe)比率的增加(相对于那些仅仅基于非ESG信息的有效前沿)。ESG偏好的代价可以量化为:选择具有更好ESG特征的投资组合时,其可获得的夏普(Sharpe)比率相比于全市场股票下的最大夏普(Sharpe)比率有所下降。
除了在实证方面具有吸引力,ESG有效前沿还具有扎实的理论依据。本篇论文明确得出ESG-SR前沿和最优投资组合的对应集合。最优投资组合由四支“基金”组成,其中一只可捕捉股票的ESG得分。该框架可被视为所谓的“ESG集成”的理论基础,这意味着ESG特征可直接用于投资组合构建,而不是如目前很多投资者那样,仅仅被用作股票筛选的一个标准。
另外,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本篇论文发现当利用应计利润(G变量)的来度量ESG时,较高水平的ESG可以实现最大的夏普比率。而且,ESG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所导致夏普比率的降低很小,这意味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实现道德目标。再者,当对投资组合施加限制条件时,本文看到ESG-SR前沿的下降。这是符合预期的结果,因为强加限制条件会降低给定ESG得分下的最大可获得夏普(Sharpe)比率。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投资范围中剔除最低ESG资产的筛选,会使得最大化夏普(Sharpe)比率的投资者所选择构建的投资组合的ESG得分反而低于不受限制投资者选择的投资组合(不受限制投资者允许投资低ESG资产)。该结果反映了根据ESG构建最优投资组合时的相关性影响。
关于均衡资产价格,本篇论文得出了ESG调整后的CAPM,它有助于反映ESG对预期收益的影响。据本文作者所知,本篇论文的模型是第一个针对投资者如何使用ESG信息,以及明确地对异质性(model heterogeneity)建模的模型。换句话说,本篇论文的框架允许投资者优先考虑ESG,并允许投资者从ESG信息中找到投资信息。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操作的功能,因为有关ESG的产品规模越来越大(例如,《 2018年全球可持续投资评论》),而且在学术界也越来越多地将ESG视为潜在的“ alpha”信号(至少要追溯到Sloan,1996;Gompers等,2003)。这种异质性导致均衡状态取决于不同的投资者类型,从而导致ESG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为正相关、负相关或中性。
本篇论文使用一系列ESG替代变量来对该ESG-SR有效前沿和资产定价理论的进行实证检验,这些替代变量反映了本篇论文模型的不同方面,并且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投资者客户。本篇论文的G替代变量可以预测未来的基本面,同时吸引投资者需求,从而导致相对便宜的估值和正回报。相反,本篇论文对E、S和整体ESG的替代变量对未来利润的预测较弱,而对这些替代变量的投资者需求似乎更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在这些指标上得分较高的股票的较高估值,以及较低的收益。
总而言之,本篇论文的理论和模型为全社会开展ESG负责任投资提供了有用的框架,本篇论文希望这对研究ESG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以及ESG在投资实践中的应用有所帮助。
== THE END ===
1. Albuquerque, R., Koskinen, Y., Zhang, C., 2018.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risk. Management Science (November 16): https://pubsonline.informs.org/doi/10.1287/mnsc.2018.3043.
2. Baker, M., Bergstresser, D., Serafeim, G., Wurgler, J., 2018. Financing the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The pricing and ownership of U.S. green bonds.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3. Baron, D. P. 2009. A positive theory of moral management, social pressure, and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18 (1), 7–43.
4. Benabou, R., Tirole, J., 2010. 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conomica 77 (January), 1–19.
5. Bebchuk, L. A., Cohen, A., Wang, C. C.Y., 2013. Learning and the disappearing association between governance and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8 (2), 323–348.
6. Becker, G., 1957.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Blitz, D., Fabozzi, F. J., 2017. Sin stocks revisited: resolving the sin stock anomaly.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44 (1), 105-111.
8. Bolton, P., Kacperczyk, M., 2019. Do investors care about carbon risk.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Columbia University. Busch, T., Johnson, M., Pioch, T., 2018. Consistency of corporate carbon emission data.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Hamburg Report WWF Deutschland.
9. Chordia, T., Roll, R., Subrahmanyam, A., 2002. Order imbalance, liquidity and market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5, 111–130.
10. Chordia, T., Subrahmanyam, A., 2004. Order imbalance and individual stock return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2, 485–518.
11. Dunn, J., Fitzgibbons, S., Pomorski, L., 2018. Assessing risk through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xposures. Journal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16 (1), 4–17.
12. Edmans, A., 2011. Does the stock market fully value intangibles? Employee satisfaction and equity pric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1 (3), 621–640.
13. Fama, E. F., French, K. R., 1993. Common risk factors in the returns on stocks and bond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3 (1): 3-56.
14. Fama, E. F., French, K. R., 2007. Disagreement, tastes, and asset pric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3(3): 667-689. Fitzgibbons, S., Palazzolo, C., Pomorski, L., 2018. ESG 2.0: Hit’em where it hurts. IPE.
15. Flammer, C., 2015. Do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ad to superi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Management Science 61 (11), 2549–2568.
16. Friedman, H. L., Heinle, M. S., 2016. Taste, information, and asset prices: implications for the valuation of CSR.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1 (3), 740–767.
17. Gollier, C., Puget, S., 2014. The `washing machine’: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corporate behavior with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ors.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
18. Gompers, P., Ishii, J., Metrick, A., 2003.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quity pri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1), 107–156.
19. Grinold, R. C., Kahn, R. N., 1995. Active Portfolio Management. McGraw-Hill Education.
20. Hart, O., Zingales, L., 2017, Companies should maximize shareholder welfare not market value. Journal of Law,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 247-274.
21. Heinkel, R., Kraus, A., Zechner, J., 2001. The effect of green investment on corporate behavior.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36 (4), 431–449.
22. Hoepner, A. G. F., Oikonomou, I., Sautner, Z., Starks, L. T., Zhou, X., 2019. ESG shareholder engagement and downside risk.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23. Hong, H., Kacperczyk, M., 2009. The price of sin: the effects of social norms on marke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3 (1), 15–36.
24. Ilhan, E., Sautner, Z., Vilkov, G., 2018. “Carbon Tail Risk.”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forthcoming.
25. Kim, Y., Park, M.S., Wier, B., 2012. Is earnings qualit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Review, 87 (3), 761-796.
26. Kruger, P, 2015. Corporate goodness and shareholder weal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5, 304–329. Landier, A, Lovo, S., 2020. ESG investing: how to optimize impact?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HEC Paris.
27. Luo, A. R., Balvers, R. J., 2017. Social screens and systematic investor boycott risk.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52 (1), 365–399.
28. Merton, R., 1987. A simple model of capital market equilibrium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42 (3), 483–510.
29. Morningstar. 2019. ESG investing performance analyzed. Morningstar website, https://www.morningstar.com/blog/2019/03/12/esg-investing-perfor_0.html, accessed on October 8, 2019
30. Novy-Marx, R., 2013. The other side of value: the gross profitability premium.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8 (1), 1– 28.
31. Nagy, Z, Kassam, A., Lee, L., 2015. Can ESG add alpha? MSCI white paper.
32. Oehmke, M., Opp, M., 2020. A theory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LSE.
33. Pastor, L., Stambaugh, R. F., Taylor, L., 2019. Sustainable investing in equilibrium.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34. Phelps, E., 1972.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racism and sex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4), 533–539.
35. Richardson, S. A., Sloan, R. G., Soliman, M. T., Tuna, I., 2006. The implications of accounting distortions and growth for accruals and profitability. Accounting Review, 81 (3), 713-743.
36. Richardson, S. A., Tuna, I., Wu, M., 2002. Predi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case of earnings restatements.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37. Sloan, R. G, 1996. Do stock prices fully reflect information in accruals and cash flows about future earnings? Accounting Review, 71 (3), 289-315.
38. Zerbib, O. D., 2020. A Sustainabl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S-CAPM): Evidence from Green Investing and Sin Stock Exclusion.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Tilburg University.
风险提示:文献中的结果均由相应作者通过历史数据统计、建模和测算完成, 在政策、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模型存在失效的风险。
(本文作者介绍: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多伦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为歌斐资产公开市场(香港)高级股票组合投资董事。)
责任编辑:陈悠然 SF104
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财经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