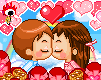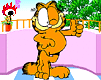| 史景迁:一个旁观者眼中的邓小平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1日 11:12 经济观察报 | |||||||||
|
本报主笔 许知远 高级记者 覃里雯 采访报道 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这是《Christianity Today》送给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称号。在整个西方世界,没人比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出版过更丰富的关于中国的研究作品了,而且它们在学术界与公众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除去题材的丰富性,也没人能比他写得更好看。据说史景迁教授是在咖啡馆中撰写那些历史著作的,那些在历史灰尘中的
现年68岁的史景迁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枯燥的数字与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从来都是尽量超越地域所限,而将之置放于更普遍的经验与情感中。他也更看中历史的连续性,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 访谈 问:您在一篇悼念邓小平的文章中将邓小平时代与晚清时代相比较,您为何这样做? 答:我认为在这两个时代都出现了中国的“洋务派”,他们在接触外界、在改革内部构架、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时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仍然认为,他(邓小平)的作用在于推动他周围的人,让他们更加灵活。 问:所以,这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延续?或者,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完成? 答:哦,从晚清到邓小平时代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的动乱,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再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现代化”这个词的意义,因此这个术语正处于争论之中。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完成了变化的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还有不同速度的发展需要完成,中国的构造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断裂。我在英国和美国居住多年,这两个国家也存在巨大的断裂,也还有很多发展没有完成。 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是惊人的,从它的整个外观面貌来看非常明显,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社会是如此难于组织……英国和美国仍然在寻求许多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问题的解答。 问:您在您的书中说过,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循环。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打破了这个循环? 答:我希望我的观点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确实说过中国有一个内部不断巩固(consolidation)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其他国家更常见的现象是分裂或者与邻国融合。今天,中国内部经济联系的加强当然是在不断加强,有很多很多的道路中国可以走。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恒定状态,而是处于一个重组构架的巩固阶段。它仍然在扩展、在实验、在探索阶段,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风险。它需要一个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领导层。 问: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相似阶段吗? 答:我得深思熟虑地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会显得头脑简单。1905年到1920年之间有过这样的时候,中国人开放心胸,准备改变组织规则、改变行为准则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语言,从外国引入词语、不停地探索世界。那时,中国处于困境之中,人们充满实验精神,显示出愿意在某些方面抛弃过去的意愿——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不愿意过于简单地做出比较。如果你看看其他时期的中国,比如康熙时代,人们也同样显示出灵活性;我现在研究的晚明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质疑精神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开始与西方学者对话,开始接受一些科学的新观念,西方也开始从中国接受一些新想法。 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某些时段相比不是那么独特,但是它的独特性在于变化的规模。我认为今天变化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按照过去的速度,这样的变化可能需要整个宋王朝的时间才能完成。 问:您曾经写过关于康熙、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您认为邓小平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占据什么地位? 答:我非常肯定,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地位。作为一个外国人,评价他是件困难的事。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忠诚的中共党员,但与此同时,他坚信中国必须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束缚中摆脱出来。在毛泽东去世后他对当时情况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精明灵活的,包括在党内团结哪些人、如何巩固自己几度不牢固的地位。他的信念就是通过结束束缚来解放中国人的力量,包括缓慢地关闭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 这些信念大概是他在后期逐渐形成的。在1978、1979这两年里,中国人需要更新思想,党的领导人也必须考虑如何迎接这一新的挑战。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吉米.卡特访华,后来邓小平访美——我当时很惊讶,怎么别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阻止他这么做。他在党内团结支持自己的力量方面一定是非常有技巧的。 问:您会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传记吗? 答: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有意思,但是可能很难得到邓小平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资料。我很难在他身上挖出更深的东西,只能通过他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而不是私人生活来了解他。关于他的个性我也只能凭猜测,除了他有很强的个性、很有政治技巧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曾经在华盛顿见过他一面,他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人,成百上千的人蜂拥而至,只为一睹尊颜。他毫无疑问是个强者。 问:那么,在过去300年中,邓小平处于怎样的地位? 答:在过去300年里,我所能想到的中国领袖包括康熙、雍正,然后就是一个大跳跃:曾国藩,他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邓小平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雍正和曾国藩还要长。其他有些失败了的有趣人物,比如袁世凯和蒋介石,他们试图将中国组织起来,但是没有获得其他最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因而失败。 邓小平的经历是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的,他比戈尔巴乔夫要有力得多。 问:您是何时开始注意邓小平的? 答:开始的时候是在1966年,我注意到他曾经与周恩来等人留学法国。但是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党内的组织人物。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才开始注意到他,那时他是作为一个强硬人物引起我的注意的。他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是当时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偶尔有一些外国企业进驻,但是不像今天这种速度。 问:在后来那些年里,您对邓小平的看法是否随着改革的进程而改变? 答: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知道,他的长寿起了一定作用——你活得越长,得到注意的机会就越多。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一个强硬人物,他对什么事情应该有什么限度是非常清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年份里,他已经不太出现在公众场合,也不太出来说话,但是他的政策依然继续。这体现出政策有自己的动力,即使领袖本人已经不再推行它们,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问:在人们对邓小平的评价中,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遗漏了吗? 答:这很难说。他的外交政策、政治和经济政策、提拔年轻人的习惯……他对前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对越南的政策……这些都不是我所熟知的。如果有人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还有他在法国、在四川和广西的经历,他和周恩来的背景的相似之处要多于和毛泽东的相似之处。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是一个适时出现的适当人物。 问:在过去100年里,中国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答:首先我不太敢肯定是否是结构性的变化。中国与历史的割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将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割断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又是如此发达。真正可能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人的开放心态,他们准备接受如此之多的外来事物:外来文化、外来制度、实用主义、计算机世界、经济理论……诸如此类。 更有意思的是观察在某些领域是否会发生结构性变化,比如家庭关系,尊老的传统等等。 问:那么,在权力结构中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答:对我来说,似乎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加强,不过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领域。中国的长年动乱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使得中央政府必须非常小心地解决问题,避免灾祸和痛苦。如果家庭组织弱化了,那么必须有新的组织替代它留下的空白。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由政府来解决,而必须由各类组织参与,共同寻找出路。 问:今天的改革是否在与邓小平时代非常不同的语境下进行的?假如邓小平依然在世,您认为他能否理解今日的变革? 答: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好问题。我认为他大概会把握住主要的概念,今天的技术发展、能源问题等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善于把握中国的强国之道和弱点所在。至于他能否就此做什么,那是很难猜测的。 我被锁在了自己50年前的价值观中,邓小平则是一个非常善于与时俱进的人。我无法理解新技术,在中国的小县城中我看到很多网吧,但是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太过复杂、难以理解的系统,领导人们也需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问:今天的中国与7年前邓小平去世之际所面临的挑战有何不同吗? 答:在我看来,人们在讨论问题方面更为坦率和开放了,束缚似乎更少了,行动更为自由了。外国人可以跳上飞机就来到中国,但是今天你却不能这样到美国去…… 问: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您是否同意? 答:他的改革也延伸到了教育和军事领域。但是我认为,在一个曾经如此中央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改革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它必然伸向不同方向包括政治。它一定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影响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新一代对世界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会变化的。 |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随笔砸谈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