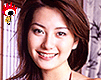中国能源部重建猜想 歧异来自权力分割中的争夺(4)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5月08日 16:15 《商务周刊》杂志 | ||||||||
|
行同虚设的安全监察制度 针对矿难频发,不能说政府无所作为。在中国,每年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几次声势浩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及对不合格的煤矿“坚决取缔”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的郑重宣告。尤其近几年来,这种领导权威的力量被使用到了极点,一系列的重拳出击和三令五申早令老百姓司空见惯。
在安全生产方面,政府管理似乎并不缺位。安全监察制度和机构也不是不健全。2001年2月,国家安全监察局挂牌成立,应该说这更是走向法治轨道的一次努力。 国务院《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对煤矿安全生产的监察制度规定得比较完备,其中已经包含了安全生产的预警机制,对煤炭业安全管理的“关口”实际上也是前置的,“事先建设,事先监督,事先介入”都有相应规定。而且各地煤矿安全监察部门也并非“由煤炭系统设立”,大中型矿区的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也是由国家和地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法设立的,与煤矿和地方政府分离,并不存在“左手”监督“右手”的问题。《条例》也赋予煤矿安全生产监察机构很大的执法权力,包括行政处罚权和紧急处置权。 其实,细水煤矿的问题早就引起过有关部门的注意。去年10月19日,山西省煤矿安监局朔州市安监站就向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细水煤矿下达过执法文书,要求其停产整改;11月5日,平鲁区人民政府又责令该矿整顿。但细水煤矿对两次执法令却置若罔闻,仍夜以继日不间断生产。 近两年,为了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山西省各市建立健全了监管模式,形成“人盯人,不漏网”的严管格局。记者在朔州市平鲁区煤炭工业局了解到,煤炭工业局和安监局两个部门全部在编人员117人,他们为全区67个煤矿共75个矿井派出了70个驻矿安监员。平鲁区安监局还做出了严格规定,驻矿安监员每月驻矿时间不低于22天,入坑次数不低于15次,不准弄虚作假、私通人情、包庇纵容。 平鲁区还制定了《驻矿安监员工作职责》、《驻矿安监员十二条权利》、《驻矿安监员十项工作纪律》等三项制度。驻矿安监员被赋予监察煤矿安全生产方方面面的权力,并可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和违规违章操作的行为依法采取检查、制止、责令停产和罚款等手段。 但驻细水煤矿的安全监察员在事发被拘后称,今年2月份仅仅下过2次井,3月份1次也没下。从平鲁区安监局提供的今年2月份安监员考评情况看,70多名驻矿安监员平均驻矿时间只有15天,最少的只有6天;而下井平均次数只有7次,最少的当月没有下过1次井。在这张表上记录的细水矿驻矿安监员朱义下井时间却是5次。 可以说,遏止矿难发生的有效措施早已规定在有关法律法规中,至少从制度上已经不存在太大的缺陷。面对中央的三令五申,甚至以撤职处分为警惩,各级政府官员也不能说不重视。但在一次次残酷的灾难面前,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下,无论是行政化权威,还是安全监察制度,都被消解得无影无踪。 机构重建日渐紧迫 1993年,在中国能源管理历史上,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能源部被撤销。直到今天,中国再没有设立部级以上的综合能源管理机构。 “能源部撤销后,煤炭部和电力部重新组建。国家能源管理走向了分散化,尤其是能源的宏观管理大大弱化。”今年已经66岁的王家诚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国家计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一直致力于国家能源战略研究。他认为,能源行业的相关职责分散在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水利部、电监会、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等相关部门。突出的问题是管理分散,职能划分不清,这种过于分散的能源管理模式,特别是缺少战略管理,难以适应能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能源自身发展的规律。 “从能源管理的内容和范围界定来看,目前各部委的能源管理职能是以管理对象界定。”他对《商务周刊》说,“决策者把能源工业等同于其他加工工业或制造业,能源的基础地位被削弱,综合全面性和长远性的能源战略管理很薄弱。” 王家诚一直强调,能源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门,特别是它涉及石油等国家短缺战略物资以及电网和天然气网的建设和运行等国家经济命脉,必须由国家监控和统一管理。因此,为了达到能源和经济的低耗、高效以及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能源监控和综合管理,他建议,必须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以能源战略管理为核心的能源监管体系。 2002年6月11日,路透社播发的一篇题为《中国需要集中的能源政策》的报道,也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在中国解散能源部将近10年之后,它如今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监督能源部门发展的中央化管理机构,“中国需要一项长期的、持续的和全面的能源政策,应该照顾到煤、油、气、电和再生性能源等各个方面,而不只是以项目为基础”。 近年来,类似重新构建中国综合能源管理机构的呼声此起彼伏。 “1993年国家撤销能源部,是国家对当时能源供求形势的一个错误判断。”王宏英认为,在1990年代初,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国内经济形势经过20年发展后,也出现了自然的周期性波动。在宏观形势判断上,决策者认为经济会继续走低,基于这种判断,当时认为中国的能源生产已经基本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国家没有必要再保留综合性的能源管理部门。“现在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进入工业初级阶段的国家,能源的供应远远达不到经济的增长需求。”他说。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发展速度加快,煤电油运全面紧张,这种判断得到了验证。能源短缺问题实际从2003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出现,到2004年则发展得更为明显和尖锐。总的表现是缺电、缺煤、缺油,媒体称之为“煤荒、电荒和油荒”。而由于能源短缺,煤和油的价格自然高企,这也对小媒窑屡禁不止、非安全生产顶风做案提供了利益刺激。 2004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了49%。但因为缺乏总体战略,没有石油储备体系,在国际油价浮动变化中,中国陷入了“买涨不买落”的怪圈。在缺乏立法和能源总体战略的情况下,中国历经10年才启动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但未来石油储备基地由谁管理、巨额资金由谁承担、储备油由谁支配却仍然存在疑问。 2004年,中国能源短缺问题越发严重,这也引起中央政府开始注意到能源管理这一个重要问题。自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听取能源工作汇报已经不下三次——这是前所未有的。 “成立能源管理部门,核心就是要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保障能源的安全生产和有效供给。能源短缺是客观的,但是可以通过综合协调发展来有效解决,比如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煤、气、水、电等的协调发展,必须有一个综合协调部门规划协调。”王宏英说。 他还注意到,目前国家宏观形势与10年前已经大不一样,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与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现在能源安全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能源问题,已经和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外交紧密联系在一起。”王宏英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层面上没有一个国家统一的、具有权威的能源管理机关恐怕很难再适应发展形势。 “国家对能源管理机构的重建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能源问题解决不好的话,恐怕不单单影响到能源工业自身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会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他斩钉截铁地说,“成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综合能源管理部门已经是形势所迫了。” 而基层的态度更直接一些。在山西采访中,一位国有煤矿的负责人也向记者建议恢复煤炭部或能源部。“屡受挫折的煤炭行业,多少年来变来变去,”他问道:“这样一个复杂而又高危险性的行业,现在连“司令部”都没有了,谁来制订行业规划,负责日常的安全管理?”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国内财经 > 行业专题--能源行业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怎样迅速挖掘网络财富 |
| 短线最大黑马股票预报 |
| 海顺咨询 安全获利 |
| 开风情布艺店生意火爆 |
| 首家名牌时装折扣店 |
| 如何加盟创业赚大钱? |
| 05年具有潜力好项目 |
| 开麦当劳式美式快餐店 |
| 开冰淇淋店赚得疯狂 |
| 美味--抵挡不住的诱惑 |
| 新行业 新技术 狂赚! |
| 投资3万年利高的惊人 |
| 1000个赚钱好项目联展 |
| 05年投资赚钱好项目!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