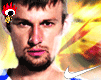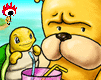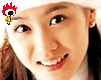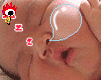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晏阳初学院:中国第二波乡村建设运动露端倪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6月17日 09:09 南方周末 徐楠 | |||||||||
|
这是一批有着共同气质和行动的人,很多农民把他们叫作“杂志社的人”。“杂志社”是一个特定的称呼,没多少农民在意它的全称——《中国改革》杂志社。提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意义是多重的:它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办者;是一些到过自己家乡的文化人;是做梦也想不到会专门让农民参加的大讨论会的主办方;是坚信自己的判断为此不惜代价的理想者。在70多年前晏阳初带领数十位大学教授、博士,进行“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的运动”之后,这批人开始走着一条相似的路。
□本报记者 徐 楠 一批有着共同气质和行动的人,在中国阡陌纵横的土地上行走。他们坚信自己的判断,为此不惜代价。 刘老石的正式职业是大学教师,可他有一半时间都来往于各地的农村,他顾不上考博晋升写论文评职称,不在乎文化人变成了“泥脚杆子”; 邱建生当年从一个福建山村“鲤鱼跳龙门”,在乡亲们艳羡的目光中考上大学,毕业后不到10年,他把家安到了河北农村。 他们自称“乡村建设”,并不引进技术改良品种,也不投资办厂,更不为官一方,而是“开发民智,培育民力”。 中国农村不乏施与式的扶贫扫盲,也不乏投桃报李造福桑梓的个人情怀,却少有知识分子以这样的角度、姿态和内容与农民直接对接。其中的精神遗产来源于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其中的政治经济学阐释来源于城市提取农村剩余这一古已有之的矛盾关系,这关系,在中国大步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今天,已亟需重理。 他们认定:假如农民依然无法联合起来应对市场,依然无法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依然无法实现自我管理,那么农村无以为继之日,也就是光鲜的城市颓然倒退之时。 近几年来,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走在了一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纽带,就是或多或少与一本叫作《中国改革》的杂志有着某种联系;他们在物质支持和精神指引上,都不同程度地受着一位叫作温铁军的人物的影响。 《中国改革》和它的负责人温铁军办会议、兴学校、做项目、搞调研,它联系起了高战、刘老石、邱建生,联系起了青年农民杨云标、马长华,联系起众多大学生和志愿者,联系起数不胜数的农民。 它更像一个实践中枢,在今日新乡村建设的图谱上,构成最显眼的节点之一。 2004年4月,华北平原的春播时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首期培训开班了。农民学员、志愿者和记者来了100多人。空气中漂浮着新麦的气息,还有热热闹闹的南腔北调。 对于当地农民,“杂志社”是一个特定的称呼。提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意义是多重的:它是眼下的乡建学院的创办者;是一些到过自己家乡的文化人;是做梦也想不到会专门让农民参加的大讨论会的主办方;最后,是那位了不起的“温总”。 现在,温铁军正是学院的院长。 对于那几位把大量时间花在农民家乡的“文化人”,最方便的概括就是“杂志社的人”。在乡建学院以及更早的新乡村建设谱系中,他们是不可忽视的主角。 事实上,他们才刚刚登场。 田埂上并不孤独 2002年春节,杂志社的邱建生带着支农调研的大学生来到河北定州翟城村。 翟城村是当年“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进行著名的“定县实验”的模范试点。上世纪20年代,晏阳初带领数十位大学教授、博士举家迁往贫困地区河北定县,推行教育、生计、卫生、自治四步方案,寻找中国人民古老落后生活方式的复兴途径。当时的一家报纸指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的运动。 2002年春节前夕,当邱建生和大学生们在村委会门上贴出对联:“平民教育诚可贵,乡村建设慨而慷”,村支书米金水吐出憋了好久的疑问:“还有人认得晏阳初吗?他不是去了美国吗?” 随后米金水终于明白:还有人“认得”晏阳初。 早年曾动过的念头在米金水心中再次涌起:“打晏阳初的旗号”,办学校,扩大影响,带动村庄。这和“杂志社”不谋而合。 2003年7月,学院正式成立。 53岁的温铁军站在学院的菜地边上说:“所谓乡村建设,就是小农村社经济前提下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他的设想里,面对分散的小农经济,要通过试点促进经济合作组织,让农民联合起来抗御市场风险;带动农村合作金融试点,使农村滚动积累发展资金;推广可持续的能源利用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希望农民健康的组织力量能够应对地方宗族势力、黑恶势力,改善乡村社会的治理。 想做这些,就没法闷在书斋里。 高校的涉农社团邀请温铁军演讲,他专程赶去;地方企业家投资有机农业,尝试创办“三农生产力促进中心”,他专程赶去。昨天在上海,今天在郑州,明天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他还在积极联络嘉道里基金会、香港乐施会等国际NGO组织,目前努力的目标,是为中国大陆十个左右的乡村试点争取小额贷款。 在2003年度CCTV十大经济人物评选的颁奖典礼上,温铁军说:“我是一个用脚做学问的人。” 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有人问温铁军是否在撒播火种。他说:“没有‘火’,就是‘种’。只是希望把这个贫富差别增大的社会稳住,让农村的问题缓解一些,让农村可持续一点。”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编印了2004年中央1号文件的全文;温铁军大声宣讲,1号文件已经明确:要“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积极推进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 温铁军告诉农民:“咱们成立合作社,联合起来买化肥、买饲料,被骗的可能性不就小一些吗?现在自己买药打虫,你家田里打出来,就全跑到他家田里去了。合作起来整体防治虫害既彻底又省钱。种出了果树咱们联合起来卖,各家都能分红。从信用社贷不出来钱,自己办小型的合作基金互帮互助。” “我是被赶着往前走的,没时间顾及别人说什么。”回避所有的理论争论,回避所有的派别定位,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有限的实践空间——在理论界,温铁军成了独行侠。 然而在村道和田埂上,他并不孤独。 “名誉村主任” 多年前,高战就听过温铁军的讲座,读过他的著作,“只要是他出现的场合,我就不断地提问题。” 2002年,高战还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已经拥有了一家注资100万元的公司。现在,他在苏北发起了三个农民发展协会,都是用乡党委的红头文件开路的。“我知道以个人力量推动农民组织化的风险,一定要争取到红头文件。” 他提醒乡村干部:成立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政绩考评里能加5分;组织农民开会议事,还能再加5分。 此后,他顺利地被乡党委的红头文件任命为“村委会名誉主任”。 2003年10月2日,苏北窑湾镇陆口村下着小雨,陆口小学的走廊上挤满了人。 这是高战曾经的母校。小时候老师说:2000年我们就要实现“四个现代化”。2000年早就过去了,再回家乡看病,“医生手里还是那个旧听诊器,几条大胶带和裂口还在老地方,一点没变。农村的现代化在哪里呢?” “这对我的折磨很大。”高战曾经相信自上而下的道路,想过要从乡镇干部做起。然而接触之后深感他们“人格分裂”,“在那个位子上即使你想做,也做不了什么,一切几乎都已经被规则决定了。” “做学者?我们的学者已经太多,做了多少实际的事情?从商?回来反哺家乡,能起些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可以奋斗的职业群体,而在这里,我的个人效能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 就在这所乡村小学的教室里,高战给小学生们演讲,组织农民谈天:“大家参加农民协会一起买化肥,各家都能省钱;管事的人真正由咱自己选!” 农协的第一件事是组织志愿整修道路。那天是大年初二,有人撂下家里刚做好的团圆饭,来了。 接着帮农户联系外出务工的渠道,组织20多人到工厂里实地了解。 然后是统计用量,联络各家在淡季统一购买化肥,“每户比旺季分散购买省了好几十块钱”。 会员家中有人亡故,会收到农协送来的花圈和悼词。悼词里说:死者向国家交纳公粮和农业税费,遵守法律、尊老爱幼、教育子女、团结邻里,这些都是农民作为一个公民爱国的最好表现。 收到花圈的人家感激不已:“破天荒能有一个组织到农民的家里送花圈啊!” 动员建立合作基金那天,当晚就收到了两万元股金。最多的一家给了5000元——一大塑料包的散碎票面,是攒着给儿子娶媳妇用的。 高战和基金会的会计、出纳三人是评议员,每笔贷款都须经他们一起审核。贷款只能用于看病、上学和发展。前两种情况不收利息。 基金会成立当晚有户人家就提出申请,后来提交了养蘑菇的明细计划,多少钱买多少种子,多少钱买多少肥料,计划如果亏了,章程规定评议员要受罚贴钱。 2004年,高战成为《中国改革(农村版)》的编辑、记者。 这本诞生还不到两年的杂志,经常刊发一些读者写来的信。一位四川青年农民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封信改变了。 他的名字是马长华。 一封信改变的人生 25瓦的白炽灯泡下面,到处塞满了书:《经济学(季刊)》、《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伊斯兰哲学史》、《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等等。 这是马长华的家,是他初中二年级辍学后的生活归依。他说:“我做体力活不在行,就想在别的方面帮帮乡亲们。” 在这个川西山村里,大部分人祖祖辈辈耕田为生,常有人家卖光了家当仍揭不开锅。 1999年,梅雨季节的一个下午,农闲的人们聚在村民马云德家的场子上“摆龙门阵”。阴云在坝子上越聚越多。 “听人说:乡政府上报的咱村人均年收入是2800元。” “啥?断粮还差不多!” “数字每年还得往上涨呢!” “靠种粮,谁家不亏钱?那400亩山地我早说该种些药材了,要不啥指望也没有。” “但钱从哪来?贷款?做梦吧。你拿啥抵押?穷得叮当响,信用社怎么会贷给你?” 在场的七个人决定写信向外界求助。他们想找到能出钱帮忙的人,引进经济作物。七个人之中,只有马长华知道“温铁军”。这个名字就被郑重地写在收信人的位置。 过了一段时间,温铁军的回信不期而至。从那天起,到处有人在村里问:“温铁军是谁?”马长华不厌其烦地说:“温老师不是北京的大官,是‘三农’专家。” 温铁军给出了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建议: “我出1000元,你们51户人家每家出100元,合计6100元。每100元为一股,51户占51股,你们组是大股东,这样成立兴富村1组‘互助会’。我不要利息和收益,只要把我这10股收益作为‘公共积累’,不断滚动增加,每年向我报告一次使用和收益的情况即可。” 按规定,会员每10户分为一组,每次只能贷款给10户中的1户,还清之后才可进入下一轮贷款,因此形成事实上的联保关系。每一笔借款,都须由理事会全体成员签字通过。 目前他们的互助会已有80户入股,分2批向10户农民贷了款。马泽伦家在互助会帮助下买来一头母牛,现在小牛犊已经到处吃草,再过几个月就可以牵到市场上去卖。 他们的信在《中国改革(农村版)》上发表了。马长华成了互助会会长、香港乐施会的乡村建设骨干培训项目讲师、首届乡村建设研讨会代表。 他开始明白了:“温老师是要让我们自我决策、自我发展,走上能力建设的可持续道路。” 互助会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但马长华肩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乡亲的猜测、怀疑、嘲讽甚至指责,与信任、支持和鼓励糅杂在一起。 “千把块钱,能做个啥事?”怀疑在村庄里蔓延。“水利局的人不是说了吗?修提灌站要十好几万。没有钱来,说啥也没用。” “风头出得这么大,还不是为他自己满世界游玩?不是说要修提灌站吗?两三年了,弄了个啥?” 互助会图书室几乎是马长华的命根子,大部分书是他自己拿来的。他就在这里给村民讲讲外面的事情。与温铁军的合影,被端端正正地摆在书架上。 他要求小学生们只要一踏进图书室,就必须讲普通话。 他执拗地打断村民的话:“沙友大哥,不是‘千里昭昭’,是‘千里迢迢’。” 他想要村民养成看书的习惯:“《读者》杂志上每期都有笑话,好笑哩!对别的不感兴趣,先看笑话也行啊。别的以后慢慢看。” 他在会上说:“一时半会咱们修不了提灌站,就先把玉米种起来,大家都种,将来组织合作社一块卖。一步一步来。” 快满32岁的马长华依然独身一人。曾经有人介绍了一位本地农专的大学生,可见了面,“觉得她还是那一套单向思维,一点逆向的、有个性的东西都没有。跟我在北京见过的那些大学生,完全不一样。” 温铁军的回信到达村中后,他们意外地收到另一封信,信中激励马长华他们实干起来。 几个人挤在一起读信,突然有人指着信末的草体署名喊起来:“是李昌平!” 他们不知道,李昌平于2001年10月来到《中国改革》杂志社,次年《中国改革(农村版)》启动,他开始担任副主编。 “钓鱼”与“发酵” 在“杂志社”的这段时间,李昌平完成了从乡党委书记到农民利益鼓吹者和思考者的转变。 2002年2月,是李昌平进入杂志社之后的第四个月,一位来自天津的年轻教师来到这里。他叫刘相波,在大学里讲授政治经济学。 刘相波站在走廊外面听完了温铁军在南开大学的讲座:“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它教人吃饭不种粮、穿衣不纺棉。它教大家都拼命挤向金字塔的塔尖,离中国最根本的现实越来越远。”那正是刘相波痛感大学教育缺乏“人文素质”,自己尝试带学生下乡的时候。 接下来,温铁军的“山沟设想”让他深受触动:“这事非做不可!” “然后就到‘杂志社’来了。太自然了,要不要我都会来。”他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刘老石”,一来上口,二来希望像石头那样坚实。 2002年夏,福特基金会以5万美金资助了“大学生支农调研”的两年期项目,刘老石成了“学生头儿”。 2003年春天,湖北房县窑怀乡三岔村小学一间教室的土墙上,旧白纸在疙疙瘩瘩的墙面上贴得有点歪斜,上面写着“乡村建设人才培训班”。 这是香港乐施会的一个项目,由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组来实施操作。 刘老石主持个人激励环节:每个人都要讲自己的梦想,还要大声喊出来。 沉默良久,一个羞赧的妇女小声说: “前夜俺没做梦”。 很多村民因紧张而皱紧的眉头在笑声里松开了。 “大伙先说说啥叫梦想吧。” 此后的每一天,都从“梦想”开始。 村民终于说出:“要办养鸡场”、“要送孩子上大学”、“要富裕安宁的村子”。 2002年,安徽阜阳青年农民杨云标组建的维权协会受到各方关注,大学生小队马上来到了杨云标所在的南塘村。他们放映农业科技碟片,放映电影,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画画、背古诗。他们跟村民一起唱《东方红》,唱《浏阳河》,有村民开始教她们扭秧歌、走“十字步”。守寡十余年的王殿敏拉住女学生赵玲的手:“十多年来我没像今天这么高兴过了!” 刘老石讲“钓鱼”,也讲“发酵”——大学生是鱼饵,是酵母,真正的主体必然是农民。而这个过程,更是对鱼饵和酵母自身的改造。 从湖北到安徽,从山西到四川,他不断体察到新的问题和动向。 杨云标曾把农村的现状概括为“组织资源的制度性缺失”,并提出“理性维权”。在生发于农村自身的组织力量中,杨云标走得最快,却走得“越来越困惑”:税费改革后干群矛盾有所缓解,村民不那么热心协会的事了。 “现在维权协会其他骨干有了危机感,他们说杨云标是大学生,上面又拢得这么紧,得搞民主化改革,离了他也能行,这才成。” “离了他也能行”——对“民主”的理解开始在切身组织利益中萌芽,刘老石把这句话牢牢记住。 迄今为止,参与过支农调研的大学生有近万名,直接带动成立了近百个涉农社团。大学生肖清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了2个月,现在辞职常驻湖北三岔村。 刘老石整天都忍不住乐呵呵的。 李昌平的基层经验,给了支农调研许多具体指导。刘老石说:“你会觉得温老师的大方向那么对,而李昌平在技术层面上的主意那么好。他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和各方面打交道。他给我们的太多了。” 李昌平在杂志社度过了两年时间。他的离开,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事件。 临别,杂志社的同事们收到了李昌平群发的短信:“因为太爱这里,所以才离开。” “晏阳初原教旨主义者” 邱建生言辞不多,总有几绺浓密的头发从头顶直竖起来。 向温铁军一再请战,邱建生终于把家安到了翟城村。到目前为止,他是惟一一个常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管理人员。 邱建生蹬着解放鞋,随便套件迷彩服,进城添置木床和二手市场的老板谈价钱,带着村里的个体司机在街边小摊上吃面,坐在记者的镜头前面却常常沉默,问一句,才答一句。为了给学院铺设宽带,花了几百元招待电信局的人,邱建生说:这是他最大的一笔公关开支。 沉默是他的常态。惟有走向田野的时候,能听到他小声哼唱的声音。 用院长温铁军的话来说,这个“晏阳初原教旨主义者”管账“马虎”,“不是一个帅才”;但《中国改革(农村版)》上介绍晏阳初思想和实践逻辑的文章,多由他来主笔,字里行间?他精确、内敛。 邱建生对晏阳初的兴趣,开始于一本《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1997年,他开始在家乡福建和北京等地奔走,发起成立“晏阳初研究会”。 听说河南有人想搞农民大学,他赶了过去。“我带书过去,我想参与,想让他们了解农村的综合改造、综合建设。可那是一家乡镇企业搞的,有商业意图,沟通有距离。” 中学教师陈炜自费到山西一个地方扶贫,他赶了过去。“那里很难——一点多余的粮食都没有,全都要自己种。走的时候我很低落——如果积蓄再多一点,我会多待些日子。” 离开山西,邱建生胃出血1000多毫升。“那时候就好像孤身一个人在荒野里。” 2001年邱建生结识温铁军,同年加盟杂志社。 来来往往的大学生志愿者总是让他感慨不已:“他们比我幸福,不用再经历寻找的痛苦。” 2004年4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首期培训开班,邱建生开始了建院以来最忙的一段日子。 一个年轻人背着大旅行包走进校门来报到。对着迎面走来的陌生人,他昂首挺胸地说:“我是马长华!” 在一起 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每天的讲座和讨论开始前,学员们要高喊口号:“改变自己,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 新的面孔闪现其中。 首期培训结束前3天,130余户村民加入了翟城村新成立的辣椒合作社。 几个月后的暑假,中国农业大学的二十几位学生,又将抵达马长华的家乡。 温铁军不承认自己在有意识地寻找、发现和吸引人,他只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1980年代,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温铁军的导师杜润生曾说:“动员起青年知识分子调查、下乡,你们就算成功了。”而现在,温铁军正“慢慢有点这样的感觉”。 “年轻人容易着急,我只是时不时在旁边给他们提个醒:慢慢来,稳当一点,扎实一点。” 高战、马长华、刘老石、邱建生这批人天南地北,各处一方,偶尔在杂志社碰到了,竟是难得的不期之遇。 在一定程度上,加入“杂志社”意味着以乡村建设为正式职业。 高战正在计划到翟城村去常驻,公司已“撂荒”多时;刘老石放弃了一度有过的考博计划,每周两次奔波在京津之间;马长华从寂寂无名一下子成为州上镇上瞩目的人物,今天所有的压力都是三年前始料未及的,他的孤独远甚于压力;作为村主任,杨云标在自己植根的土壤里身陷权力与矛盾的漩涡。 前路上遍布着尚不可确知的种种可能,这反而向他们印证了另辟蹊径的意义。 脱离官场、商场、学术界的正统评价标准,他们试图用自身命运辟出一个价值与机遇的岔路口。他们精力充沛,志在必得,他们竭力付出以期收获。他们初尝胜果,倍感欢欣。 先前种种分散的努力正在织就一张网,虽显疏淡却已见端倪。乡建学院如同网扣,在织网人的手中一天天收紧…… |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国内财经 > 关注“三农”问题 > 正文 |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