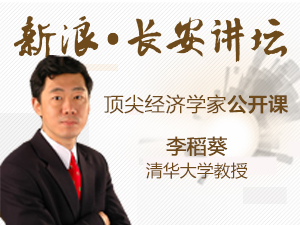来源:中伦律师事务所”微信
2014年7月,香港终审法院作了裁决(FINALAPPEAL NO. 21 OF 2013 (CIVIL)),直接“击穿”了以信托结构为形式的夫妻资产隔离,引起了全球私人财富管理行业的高度关注。该案意味着,海外信托,并非绝对“安全港”与“隔离岛”。该案也给国内拟在离岸设立信托以保障家族财富安全的高净值人士以警示:一切以“非法侵害”为手段的财产隔离手段都最终敌不过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不论是婚姻、家族、还是家族财富的配置管理,首先要公平、合法地建立私人财富保障的法律体制,促进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进步。
案例 7-4-5 PLTO(PLTO,私人信息已经过化名处理)案[1]
PLTO(P先生,判决中简称“H”)与妻子KLK(J女士)于1968年1月6日在英国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三名子女分别为K、R和H(其中R及H分别于1995年、2000年过世)。P先生自1977年便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虽然在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免有各种高低起伏,但自1994年起,P先生的生意开始风生水起,在香港成立了一系列的运营公司。之后,P先生成立了AL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L集团”),P先生担任AL集团的主席,而AL集团则成为P先生所有生意的控股公司。
1995年7月,P先生以AL集团84.63%的股权及另外一家公司REY Limited的股权(该公司持有P先生与妻子儿女共同居住的房屋)设立了名为“TOPF Trust”(以下简称“信托”)的酌情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该信托在泽西岛(Jersey)成立,财产委托人、保护人及受益人之一为P先生,受托人为H国际信托有限公司(H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2009年2月P先生提出离婚申请,J女士并未作出任何抗辩。法院于2009年5月颁发“暂准离婚令”,2010年9月颁发“永久离婚令”。
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后,J女士立刻向香港法院申请了“附属救助”,要求基于平等分配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al sharing[2])对半分割该信托的所有价值,并主张该信托的总价值为$1,560,686,000;同时,J女士认为双方分居时间为2008年,而AL集团系2001年起开始产生巨额盈利,故该巨额盈利的产生于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由双方对半分割。
P先生方则认为,该家族信托中包含双方子女K的权益,夫妻双方仅拥有2/3的信托价值;另外,P先生主张双方自2001年起已分居,AL集团自2001年所产生的巨额盈利与J女士无关。
经过一系列的诉讼程序,香港终审法院(Courtof Final Appeal,Hong KOng)最终于2014年7月17日对P先生一案作出了终审判决[案件编号:FINAL APPEAL NO.21 OF 2013 (CIVIL)],该判决推翻了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关于“该信托的价值中只有2/3权益是双方的婚姻资产”的观点,而认为整个信托完全系P先生可用的财务资源。随着该终审判决的尘埃落定,不但使得P先生本人需要向前妻J女士支付约$7.6亿的赡养费,同时更引起了社会大众对于信托的资产保护能力的普遍质疑。
笔者通过对香港终审法院出具的终审判决书的研究,终审法院关于P先生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之一即该信托是否属于P先生的财务资源(Is thediscretionary trust is afinancial resource available to H),并设置了一个测试的标准问题:如果P先生要求该信托提前预付该信托的全部或部分资本或收入给他本人,受托人是否极有可能按照P先生的意愿执行?而香港终审法院主要通过研究该信托的设立及条款、P先生的信托意愿书、该信托资产的性质及受托人以往所做的分配等内容从而作出判断。
首先,香港终审法院通过该信托的设立及条款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P先生让自己成为该信托的保护人,这使他拥有了非常重要的权利,这种权利甚至包括更换受托人,因此他的意见对于信托的管理者即受托人有很重要的影响;
2、P先生让自己成为该信托的潜在受益人之一,表明了他也打算从该信托的资本和收入中获得相应的利益;
3、P先生只打算让受托人成为AL集团84.63%股权的持有人,而AL集团的实际经营权则仍由P先生本人掌握;
4、P先生声称其子女K应当拥有1/3的信托权益,但是K在该信托中也是一个可以被P先生任意决定的对象,且她能否从该信托中获得收益完全是未知的;
5、最为重要的是,如果该信托决定把整个或部分的信托资产或收益仅分配给其中一个受益人,是完全没有任何阻碍的。
其次,香港终审法院通过审查P先生的信托意愿书发现:
P先生作为保护人所获得的权利已经完全取代了受托人,且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而P先生的意愿对于受托人的行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如:根据P先生1996年1月22日签署的信托意愿书显示,P先生希望香港理工大学(Hong KongPolytechnic University)成为该信托的潜在受益人之一,而受托人则在四天后立刻决定该大学成为符合条件的受益人。
又如:当P先生与J女士开始离婚申请,且P先生从双方共同居住的家中搬出之后,受托人根据P先生的指示,便立刻将信托所持有的REYLimited公司的所有股权(该公司持有P先生与J女士及子女们共同居住的房屋产权)转移给了J女士,自此该信托中资产仅剩下AL集团的84.63%股权。
香港终审法院认为根据P先生的信托意愿书可以证实整个信托实际上可以被视为P先生对于AL集团股权处理的遗嘱。就像立遗嘱人可以随时改变遗嘱一样,香港终审法院也有理由相信无论P先生希望怎样修改信托意愿书,受托人都一定会尊重并执行他的所有意见。
此外,香港终审法院还通过研究该信托唯一的资产即AL集团84.63%股权(原本信托内的另一家公司REY Limited公司的股权已经根据P先生的指示转移给了J女士)的财产性质及受托人以往所做的财产分配后发现:
虽然AL集团是一家年营业额超过25亿、旗下拥有13家公司、雇佣人员超过1500人的大集团公司,但根据该信托的信托契约(Trust deed)第26(b)(i)显示,受托人仅作为AL集团的股权持有人,并未参与到整个集团经营任何一部分,甚至没有任何基于股权持有人而享有的投票权或其他相关权利。结合P先生的信托意愿书,P先生不仅是AL集团的实际经营者,实质上已经成为了AL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甚至P先生还能指定他身故后由谁来担任AL集团的董事长(managing director)。
因此,该信托并不是通过受托人去经营管理信托资产从而获得收益,整个信托的收入完全来源于AL集团所派发的股息(dividends),且信托除了该股息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另一方面,由P先生所控制的公司董事会则决定了AL集团是否派发股息及何时派发多少股息等内容。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一旦股息被派发到信托中,受托人总是会按照P先生的意愿去分配这些收入,包括分配给P先生自己。在本次附属救济程序开始前,该信托已经分别在2001年3月29日、2002年3月14日、2008年7月16日、2009年7月30日及2011年2月21日将AL集团派发给信托的股息直接分配给P先生,财产价值共计$68,552,999。具体的分配方式为:以2001年3月29日的股息分配过程为例,2001年3月26日P先生作为AL集团的董事长通知受托人可以获得的股息价值为$8,463,333并开具支票给受托人,受托人在收到AL集团派发股息消息的当日,并决定以P先生为信托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we intend to exercise ourtrustee power to make a distributionfromthe trust fund to you as beneficiary thereof”,2001年3月29日该信托将价值$8,463,333的信托收益全部转入到P先生的银行账户中,2001年4月9日P先生向受托人支付了分配信托收益的手续费$5,000。之后,为了更加简化手续,AL集团甚至将应当分配给受托人的股息直接转入到P先生的银行账户中。以2008年7月16日的股息分配过程为例,2008年7月10日AL集团向受托人写信表示根据P先生的意愿,希望受托人同意AL集团直接将股息收入支付到P先生的银行账户中:“As Mr O P wishes to have the said dividend to be received byHSBCInternational Trustee Ltd distributed to him, we would therefore appreciateifyou could kindly send us your letter of instructions to pay the saiDDividenddirectly into Mr P’s BAnk account.”而受托人于2008年7月16日指示AL集团将股息直接支付到P先生的银行账户中。由此可见,该信托中唯一的收入即AL集团的股息可以由P先生任意决定并分配给自己,甚至根本不需要受托人经手处理。
综上,香港终审法院通过对上述事实的论证及调查,可以得出结论即受托人极有可能在P先生要求下,将信托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或收入都预付给P先生本人,因此该信托的资产应当被视为P先生直接可用的财务资源。
信托作为一种实现财产隔离功能的财富管理手段,已被境内、外的高净值人群广泛使用。鉴于信托关系成立后,所交付的财产就成为信托财产,系一种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的财产,这使得信托财产具有了财产隔离的功能。而信托实现财产隔离功能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需要保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财产必须独立于委托人、受益人而独立存在。但通过P先生的案件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案例中的信托财产并不具有独立性,反而整个信托财产及受托人都完全受到委托人P先生个人意志的控制,该信托中的受托人除了担任信托财产即AL集团相应股权的名义登记人之外,其他包括AL集团的投票权及经营权、AL集团的股息分配权、信托收益的分配权等所有的权利均由P先生所操控,这最终导致了香港认定该信托财产实际为P先生所拥有的财产,判决P先生需要向前妻支付数亿元的赡养费用。
另外,在P先生的案件中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即P先生所设立的信托为一个酌情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3]),该信托的特点为,信托的受益人及受益人的权利都是不特定的,主要由委托人在信托文书中设置的标准条件而决定。而委托人通常会向受托人出具信托意愿书,由于信托意愿书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受托人可以自由裁量是否依据委托人的信托意愿书履行相应的行为。但P先生案件中,受托人完全依据了P先生的信托意愿书指示,包括新增香港理工大学为信托受益人、直接转移该信托持有的公司股权给P先生的前妻等,同时在P先生的指示下将信托中的唯一收入即AL集团的股息直接分配到P先生的个人银行账户中,这所有的行为都使得香港终审法院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P先生利用信托意愿书向该信托提出要求提前预付信托的全部或部分资本或收入给他本人,受托人是极有可能按照P先生的意愿来执行的。因此,香港终审法院进一步确认了该信托的资产实际就是P先生个人可支配的财产,应当作为夫妻的共有财产进行依法分配。
此案,是2013年6月英国最高法院判决涉一起婚姻(X案)附属救济案件的有益呼应。在X案中,最高法院的长达四十几页的判决书中,大法官NeuberGEr,大法官Walker,法官Lady Hale,大法官Mance,大法官Clarke,大法官Wilson,大法官Sumption这7位大法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论述了在婚姻案件中提起附属救济的情况下,把在一方当事人所控制的公司名下的财产转移给另一方当事人的三种适用情形:
1、刺穿公司面纱原则的适用情形;
2、1973年婚姻诉讼法相关条款的适用;
3、实际权益人的适用。
因此,不论财产是否在中国,只要树立“公平正义”的信念,权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就有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进入【新浪财经股吧】讨论
责任编辑:戴明 SF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