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罢免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06日 17:06 新浪财经 | |||||||||
|
艰难的罢免 六年过去了,寮东村罢免案,已经成为见证中国村社民主的里程碑式事件,被各式各样的书报宣扬得伟大,光荣,激动人心。然而,撩开覆盖在罢免案上的并不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乡村民主创新的艰难和不易。
今天的寮东村,早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乡村村落。温州火车站,温州汽车新南站,都盘踞在寮东的土地上,八方商贾,不在空中飘落,就从这里聚散。地利上的近便,引得豪华的商务公寓酒店一个个拔地而起。一个原温州大学的讲师告诉我,1990年代初,他宁愿选择学校70平方米的旧房,也不愿意分到建在寮东的120平方米的新房。然而,仅仅十年,寮东每平方米的房价,变戏法似的成了前者的一倍。 吴锡铭说,寮东的房价贵了,是因为土地越来越稀少了。经过十年的开发,寮东原先700亩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土地在转让过程中的矛盾,是引爆罢免的导火线。 1994年,金温铁路行将竣工,温州火车站站场开工在即。黄祝华所在的第六村民小组,被征地55.23亩。政府同意的补偿是每亩1万8千元,拗不过农民的争吵,每亩地的补偿又增补了4千元。考虑到村民失去土地后的再就业,地方政策规定,被征用土地依据百分之八的比例,返还给第六村民小组57户村民作宅基地。遗憾的是,政府没有及时兑现承诺。直到1997年,反复上访的村民们才在瓯海区土地局的文件上看到了4.5亩的安置房用地。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据吴锡铭说,村委会一共盖了7300平方米的房子,但没有依据区土地局1997年63号文件所说的那样,由57户农民分享。而是给每户分了60平方米,剩余的3300平方米由村集体占有。村民和村委会的矛盾由此而起。 随着地价的不断飙升,农民的心理越发失衡。当他们得知政府以每亩250万元的价格,把他们的土地卖给东瓯大厦的开发商,他们抱怨自己得到的补偿太不合理。 争吵,上访——反复的较量,促使牵涉其中的温州市个体协会让步。1997年,个体协会决定补给村委会180万元,另有2200平方米的房子按照基本造价每平方米1700元的价格,卖给村委会。当时的市场价格是每平方米2000元。所有的利益大略有200多万元。第六村民组认为,利益应该由他们所有,而不是整个村集体。 黄祝华兄弟较多,家族利益也相对较大。初中毕业的黄,算得上第六村民小组的知识分子,做过企业当过优秀厂长的他,很自然地成了矛盾一方的领军人物。吵闹,无休止的吵闹。1997年秋天,黄祝华还因为在施工现场领导村民吵闹,被关进了收容所。公愤于是扩散。 “寮东名士”吴锡铭“及时雨”一样出场了。他以黄的名义,去瓯海区法院打起了行政官司,认为对黄的收容,是不当行政。他说,黄既非流民,也非身份不明者,怎么能够对他进行收容?仰赖区政法委的干预,黄于第37天走出了收容所。 冲突中,第六村民小组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变成所有村民和村委会的矛盾。矛盾的焦点,也由征地延伸到村官们的不廉洁,不亲民。 1998年春天,村民们把村委会告到温州市中级法院,主张村委会返还温州个体协会的业主们给予的180万元的补偿费,以及2200平方米的房子。1998年10月下旬,温州市中级法院驳回了村民的诉讼请求。执著的村民们上诉到浙江省高级法院,得到的结果是:维持原裁定。 村民们虽然不懂法,但他们凭借“情理”,认定法院驳回他们的诉求是不公正的。他们开始上访。先是温州市府,再是浙江省府,既而是国务院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最终,他们在没有结果的上访中感到疲惫和懈怠。 此间,有气无处撒的村民们突然看到瓯海区农村合作经济审计总站的审计报告。1998年8月6日出笼的寮东村1993年至1996年的财务审计报告,让平日就对村官花钱存有疑虑的村民,瞪大了双眼。 审计报告开列的三个“主要问题”,就是村民眼中的三大“罪状”: 第一,制度观念淡薄,财务管理混乱,白条漫天飞。 会计凭证不规范,五分之四以上的现金支出都没有正式发票入账,且大多为自行填制的白条子,真实性很难查核,财务审批流于形式; 出纳管钱乱付钱,据1996年12月9日对出纳库存现金的盘点,应存现金余额高达76万余元,经清点账后未报结单据35万余元,白条抵库的暂支以及应收款多达40余万元; 第二,乱花钱,铺张浪费。 公款吃喝,请客送礼乱消费。从1993年到1996年,以会议费、招待费、请客送礼、公款吃喝等名义报销的支出,多达44万余元。换言之,这四年内,村里正常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被村官们的“大嘴”啃掉了。一个看上去很滑稽的吃喝报销项目是联防队点心支出,1995年村里招待联防队的点心费是12587元; 村官补贴名目多,工资奖金增长快,专控商业违章购置多,“耳朵边的腐败”和“屁股底下的腐败”都很严重。1993年村官们的总酬金是51211元,1996年则是104924元,翻了一番。1994年春天,5个村官和一个退休的支书一人公款配置了一个寻呼机。次年夏天,村长和书记各自公款配置了一部手机,在那个手机还是身份象征的年份,两人的手机花去村集体资金49000余元。1994年后连续三年,村官们花了10万元,买了三辆摩托车为胯下坐骑。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无论是买手机,还是买摩托车,既无审批手续,又没有正式单据,入账的全是白条子; 村官和党员公费旅游、公款保险。村官去深圳考察,全体党员去雁荡山开展党员活动,无不耗资颇丰。村官们不仅像正式编制的国家干部一样,为自己开列三项保险,还在1994年用村集体资金为自己的家属作定额人寿保险。 审计报告特别指出,旅游保险,村官报酬,以及“嘴边的腐败”“耳边的腐败”“屁股底下的腐败”,各项支出高达92万5千余元。看看寮东村这几年的收入,半壁江山就这样被糟蹋了。 审计还指出,铺张浪费远不止于此。在工程费用、土地征收、道路修理、集资联建等事务中,同样存在铺张浪费。 第三,部分村官存在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经济问题。村里安装电话,会计和出纳每人减免2000元。村长潘义汉一年的手机费就报销了11000余元。此外,公款私借现象也多次发生。 被激怒的村民们,愤慨于村官们的“腐败”,并将村官们假想为掠夺他们土地和利益的团体。1998年9月8日,800余村民在中国第一份由农民起草的罢免书上签了名。很快,梧田镇政府、瓯海区人大常委会和民政局都接到了罢免书。 一段日子后,村民们没有听到任何官方回复。起草者吴锡铭去征询区民政局的态度,并声称罢免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民政局一官员答复说:“我说了不算,只有区委组织部和镇党委才能做主。” 无奈之下,吴锡铭跑到浙江省民政厅。敲开基层政权处的门,他终于听到了肯定的回答:“你们有权利罢免村委会主任,区民政局不同意,你们可以起诉他们不作为。” 1998年11月4日,《村委会组织法》开始施行,而非先前的试行,原先的24个条文也变成了30个条文,对照第19条、第20条,吴底气更足。 可是,法律条文似乎并不足以打动瓯海官方人士的心。四处碰壁的吴决定乘去北京大学看望女儿的机会,去趟民政部。 1998年底,颐和园的水已经结冰了。看过女儿,离开北京大学的吴,受到时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刘喜堂的接待。吴担心国家部委的官员们对上访者不信任,特地将《温州日报》关于村民欲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报道,呈递给刘。 刘看到的村民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材料上,潘义汉的行为和一个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已经严重不相符:潘不顾村民重托,对村务财务未经村民同意,擅自超越职权自作主张,导致集体资产大量流失。譬如,对集体公益事业建设,暗箱操作,1996年村里建造三个厕所,未通过村民代表会议,造价未经公开投标,结算也不公开。 刘对他们的民主热情表示钦佩,并态度鲜明地支持他们的罢免案。 虽然有了国家部委官员的“口谕”,罢免案的启动依旧不那么顺畅。性格倔强的吴,不断给北京方面打电话。 不久,民政部要为《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开个全国性的会议,各个省民政厅和地级市民政局的官员被要求与会。会议组织者还特别留给梧田镇镇长一个特别的列席名额。 回忆刘喜堂对他描述过的会议的场景,吴黑黝黝的宽阔脸膛上,红彤彤的,光彩照人:“开完会后,刘处长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会议间隙发言,‘寮东的村民要罢免村委会主任,可是镇里却不同意,今天,我们把镇长邀请到现场,请他开完会回去启动罢免,尊重民意,贯彻《村委会组织法》。’” 吴说,会议结束后,刘还专程去宾馆和镇长谈话:“尊重老百姓的意愿,别让他们老是上访啊。” 镇长回到温州,见到吴,打趣道:“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吴笑答:“你要请客,我不上访,北京怎么知道还有你这么一个镇长?” 1999年春节后,机关开始上班。吴一脸严肃地找镇长:“怎么老是搪塞,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罢免?”不愿意在推诿拖拉中慢慢等待,吴再度致电刘喜堂,恳望借助他的力量和途径,推动寮东村的罢免。 此时,另一份审计时限自1997年至1998年8月的审计报告出台。结论依旧是财务混乱,报酬不透明,铺张浪费等等。两份审计报告预示着罢免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吴的“上层路线”发生了效果。民政部将他们的罢免要求,向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作了汇报。据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在摁满手印的罢免书上作了批示。后面的事情一路顺风。浙江省民政厅决定派员前往寮东,督察村民提前改选村委会主任。 3月的一天,镇政府派出一个21人的工作组,前往“核实”村民的联名要求。来自温州人大常委会的消息说,一工作组成员把一个妇女“同意罢免”的意愿,写在“不同意罢免”一栏。看上去,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插曲,但在一个反感情绪压抑已久的村庄,它差不多成了政府有意抵制罢免的“证据”。 实际上,面对黄祝华等村民强大的罢免决心,任何抵制都没有了力量。1999年5月24日,启动罢免的前一天,有记者来到黄祝华的住处。黄指着一间凌乱的房屋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所有的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该记者在工作室看到两张并排的办公桌依窗而置,上面是一堆指导罢免的图书和审计报告。 第二天,期待已久的罢免正式启动。法兰西电视台等境外媒体都做了正面的报道,均以此为风向标,称许中国民主的进步。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国内财经 > 浙江发生了什么 > 正文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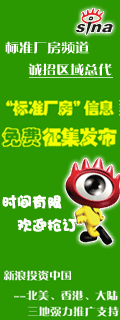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市黑马:今日牛股! |
| 1.28万办厂年利100万 |
| 名人代言亲子装赚钱快 |
| 小女子开店50天赚30万 |
| 女人钱,怎么赚 (图) |
| 06年赚钱项目排行榜! |
| 介入教育事业年赚百万 |
| 100万年薪招医药代理 |
| 品牌折扣店!月赚30万 |
| 泌尿顽疾——大解放! |
| 拒绝结肠炎!! 图 |
| 从此改变哮喘气管炎!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糖尿病——重大发现! |
| 高血压!有了新发现!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