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厂,回不了乡

欢迎关注“新浪科技”的微信订阅号:techsina
文/张进
来源:光子星球(ID:TMTweb)
春节前几天,曾在百度、网易等互联网大厂工作过的Jenny收拾好行李,退掉了自己在回龙观租了几年的房子,准备回到重庆老家过春节,节后不再回来。
回到重庆,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叫她小花,只因她的名字里有一个“花”字。“在北京工作这些年,大家要是叫小花我会不喜欢,觉得Jenny才是我,后来慢慢发现,Jenny只是我的保护色,小花才是我的底色。北京的房价是重庆的好几倍,要留下来不太可能,但是回重庆工作买房就比较轻松。”
春节之后,小花将前往一家重庆的车企工作,虽然待遇比以前低了不少,但是相比同龄人待遇仍然不错,她比较满意。
去年大学毕业后,经过不断面试和淘汰,薛娇最终如愿以偿进入了一家互联网大厂——美团。每年,都有很多像薛娇这样的年轻人挤破脑袋也想要进入这些公司。
过去这些年,大厂不仅吸引了一批批从985、211等国内优秀大学毕业生、海归蜂拥而入,也让许多普通学校的学生以能进入其中工作而被同龄人羡慕。同时,传统行业许多公司也以这些互联网大厂作为风向标和学习的榜样。
一时间,这些大厂装着一群群年轻的精英,瞬间又成为一个区分人与人差距的分界线。
最近几年,互联网行业的坏消息变多,同时,离开大厂的年轻人也随之增加。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散发着对互联网行业的痛苦、焦虑,其中多来自这些大厂人。
一年大厂经历,并不如在学校时想象的那般满意,薛娇渐渐动了离开的念想。她告诉光子星球,自己和男友已经决定好了,再坚持到今年六月,就从美团辞职去国外念书,以后不打算回来了。
“早点在大厂赚到买房的钱,然后Fire、跳槽去不加班的外企。”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
大厂渐渐祛魅, 内卷、裁员、躺平、咸鱼、佛系成为离开大厂种种原因的关键词,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迫不得已。
拒绝当工具人
对于互联网大厂,王淼早已祛魅。在他眼中,这些高大上的互联网大厂某些方面跟传统的流水线工厂并无甚区别。
十年前,王淼到某电商大厂实习。回想起第一天中午,当他坐在公司餐厅吃饭时,静静地感受周边环境,从里面看外面街道的行人车辆像蚂蚁一样小,有种俯瞰众生的感觉。到了饭点,人们鱼贯而出,在这座大厦四散开来,好不热闹。
十年后,再次路过,看着对街那座熟悉的大厦,透过玻璃看到人们忙碌的身影依旧,甚至更多,王淼早已没有了什么感觉。
从这里离职已满一年,他谈起曾经工作十年的公司,感情复杂。
“虽然不是这个时代里最幸运的1%,至少也是前20%,命运把我放在这前20%的位置上,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在这里他付出了十年青春,挥洒自己的热情,也赚到了足够多的钱。现在回到自己的家乡扬州,电商已经成为他的副业,生活还算惬意。
互联网行业光速进步,大厂的发展,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很多切实的改变,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对于王淼而言,一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能用十年时间,攒下一笔钱,尝试另外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已经足够幸运。
互联网大厂带给普通人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但相比国外同类型公司,对个人的损耗太大。他用“社畜”来形容自己十年大厂生活,每天像工具一样,忍着,熬着。
在他看来,西方式的后工业时代,人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工作的意义感逐渐缺失,职场倦怠难以解决,而资本的过度扩张,让原本过细的现代化分工带来更重的职场病,而这在互联网大厂中尤为严重。
夜以继日的熬夜加班,上级的pua,职场的冷暴力,十年里他几乎什么都经历过了。
与王淼同期进来的同事,大多早已升职,剩下的三两个也在前几年纷纷晋升,唯独他还停留在原地。关键是自己的绩效也挺好,十年里他已经想通了,归根结底在于自己与庞杂的官僚体系不匹配。
“虽然自称为自由创新,互联网大厂们并没能摆脱传统的唯上与官僚。”
在他看来,与硅谷相比,国内所谓的互联网科技企业,科技含量不高,加之整个环境创新氛围不浓,很多人进去都是“拧螺丝去了”。
一位手机大厂员工也有如此感受。他用“面试造火箭,入职拧螺丝”来概括自己的大厂职业落差。搬砖、螺丝钉、工具人也成为很多大厂人的自我调侃。
入职拧螺丝这一特质从“互联网搞35岁优化”便可以体现。
“互联网在风口上,开得起薪水,公司自然要招最优秀的人,但是大部分活儿专科生也能干,并不需要招那么多优秀的人。”王淼认为,一个单一经济体需要的互联网行业从业者是有限的,因为有所谓的人口红利,所以就搞35岁辞退。
资本运作下,大厂为高速运转,永远需要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进来,团队极速膨胀。阿里巴巴已有超过10万员工,腾讯约有10万人,互联网新贵字节跳动的员工总数在2020年里从 6 万蹿到近 10 万,而京东集团的员工数更是已经超过了30万。
在人员膨胀之下,就出现把人当工具的现象。对于大厂最常见的996,许多人习以为常,但王淼认为60%的加班是无意义内耗。
对于前段时间企业微信高强度加班领导层被怼的新闻,王淼认为这些微小的力量并不能改变什么,犹如朝向大海里扔出的一颗石子,泛不起一点涟漪。
“为了表演加班而加班,时间全被浪费掉了,没有任何正向产出,更多是为了讨好各级领导,或者附和所谓的集体主义。”
在他看来,大厂人员严重膨胀,浪费了不少高端人力,这些人原本可以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逃离之路
虽然并没有王淼这样深刻的经历和透彻的理解,一部分年轻人感受到不适,早早离开。
站在大厂门外,那一栋栋大楼里的人们是光鲜亮丽的。接到offer时,薛娇激动了好几天,直到真正体验了里面的生活,才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每天最焦虑的是日会,你要在日会上说明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如果今天没什么进度的话,到了第二天的日会,就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对于刚工作的薛娇来说,焦虑来自这些小细节,日会、周报,让她时刻感受到被push,领导催进度很凶,而周围的同事都非常努力,自己必须同样如此才能像一个团队。
公司有绩效考核与末位淘汰,部门里每个人都非常紧张,没人敢放松。领导都很有忧患意识,希望主管的部门在较短时间内可以有更多的产出,这样绩效看起来就会更好。
“大家都希望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可以达到一个看得见的效果。”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一定要做快一点不能落下,同时,大家还都希望无论是合作还是对接的人也能同样高效,从而不影响自己的进度。
薛娇是做算法研发的,除了领导,还有产品经理催进度。
北京太大,生活成本非常高,为节省,她很多同事都租住在离公司很远的地方。一位同事告诉她,自己每天早上要坐两个小时的地铁来上班,下班回到家已经十点了,笑称连取快递的时间都没有。
对于薛娇来说,在大厂的这段时间是失重的。每天除了高效工作,回到家醒着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没有个人自由、没时间好好生活、没精力处理感情问题。即便到了周末,工作日被榨干的身体,也只想躺在家里哪儿也不去,无暇欣赏北京的风景或关心家里人。
在资本的运作下,大厂必须保持高效运转,而维持这些大厂机器得以快速转动的是工作在其中的人们,当工作时长严重挤压生活,压力便随之产生。
即便是从内部压力最大的核心部门转岗到现在的部门,薛娇依然感受到不适应,她想出去。
“现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压力都挺大的,待在这里人的损耗很严重,我准备出国读书,最后就留在国外的互联网公司,那边的环境可能稍微好一些。”
当初,她对进大厂抱着无限憧憬。觉得互联网大厂是开放包容和自由创新的,人在这里是鲜活且有个性的,而进去后才发现,一切都是幻想,依然摆脱不了传统的主流和庸俗。在这里,冷漠教条、市侩虚伪依然普遍存在,人被工具化的情况也随处可见。
感受到不适,如薛娇这样的年轻人选择逃离,而还有更多心存矛盾、没有勇气离开的年轻人,选择继续困在这些大厂里挣扎。
异端生活
当拿到字节的offer时,张天给家人分享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自己能赚多少钱,家里每个人的工资都比不上。
但随着在字节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心里的痛苦便会加倍,对工作也心生排斥。也更想念老家的院墙和家人,想念广阔的天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生活。
从小生活在内蒙古草原,每天面对着“拉通对其”“闭环卡点”这些词语,让他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曾在某头部视频平台工作的李琳的感受是:“每天的工作内容都是为了绞尽脑汁,把上亿刷手机的人困在我们的App里(黑话叫“闭环”),卖广告,攫取流量、金钱、精力。”
越来越找不到工作的意义。像张天、李琳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除了能赚钱,他们还想寻求工作的意义。
“当初大厂校招的时候,正是因为死活想不出我在这些岗位的意义,所以最后都没投。”一位网友称。
同张天一样不适应,梁成觉得自己在大厂是个异端,同组同事都在为升职加薪而努力,生活里只有工作,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和无意义感,我不知道追求这些KPI和OKR到底能带来什么?”
在外面对大厂充满幻想,进去才发现大多是“海市蜃楼”,想要逃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些,开始离开大厂。
一座围城
大厂就像一座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
在这些大厂,很大一部分自称是小镇做题家,他们出生在四五线小城镇,凭借着考试天赋进入985、211名校。

大厂充满机遇,但996的工作环境以及北上广大城市的经济压力,让他们内心充满对留在大厂还是回去家乡的矛盾与挣扎。
留给年轻人的选择并不多,互联网迎来寒冬,大厂待着痛苦,三四线也并不能躺平。
宫羽从2015年来到北京,进入一家大厂投资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工作,之后2018年转辗到了上海某数据服务独角兽公司,现在回到成都已经一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了。
她在互联网行业爆发期时进入,那时在北京上海选择很多,一家不行换另一家,永远有选择。而成都与北京在就业环境、商业氛围差距很大,看上去成都好像有很多大厂、中小互联网公司,但其实好工作少得可怜,公司的数量、体量、质量都有不小的差距。
她认为,自己回成都时间有点晚了,这几年从北上广逃离到成都的人越来越多,加上行业收缩,大厂岗位有限,很难找工作。
“虽然现在一线城市也有这个趋势,逐渐全行业呈现供大于求局面,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一线城市仍然更好找工作,更多选择,更多发展空间。”
成都的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不管是房租还是物价,但是高生活成本却让北上广回去的人们感觉没那么值,并且成都也很卷,想要在这里躺平不要抱太大希望。
以前,考公考编考研似乎是大厂人的退路,如今,这条路也越来越难走了。
“没进互联网的也因低薪而焦虑。”马丽在某四线城市当公务员,年包是她在阿里的应届生堂妹的四分之一,同龄人的收入差距,让她曾经一度想离开体制内,北上打拼。
“除公务员外,四线城市提供不了任何体面的岗位。”但是体制内几乎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一位在百度工作的员工告诉光子星球,虽然互联网压力很大,但是考编考公又考不上,只能浑浑噩噩继续苟且着。
离开腾讯两年后,吴涛进入一个小厂,目前又在考虑重回大厂。一番对比,他发现大厂资源、机会更多,钱也更多,但是考虑到又要拿命来换钱就犹豫,害怕自己身体承受不了。
之前在腾讯,由于部门工作能力不太行,整个部门每天加班到9点甚至12点。长期高强度工作,身体亮红灯,严重耳鸣,脑子基本没清醒过。
跳槽去了一家小公司后,发现其部门的工作效率远超原来在腾讯的岗位。
最近,吴涛和一朋友聊天,说想去大厂,问他为什么,朋友说没有去过,想去长见识,想学到更多东西。
“可能我比较悲观,感觉大厂和他期望的并不一定一样。”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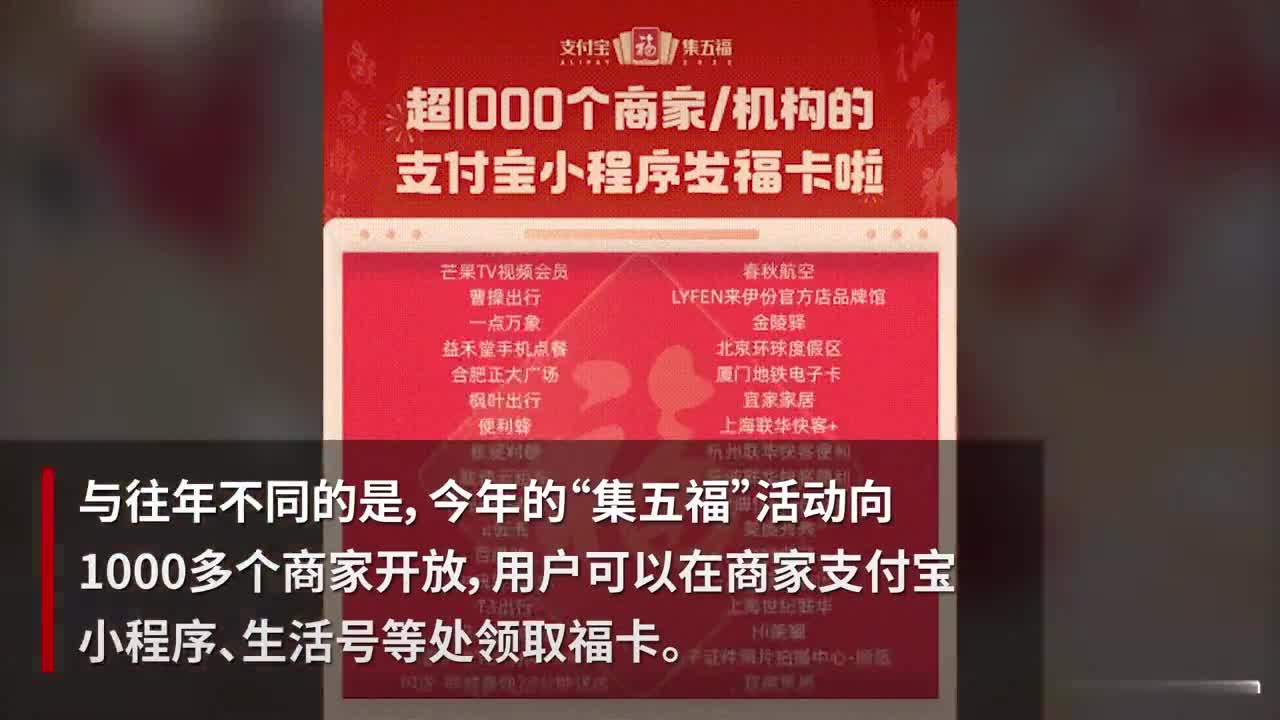 play
p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