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2021年了,居然还有人跟杨永信一样将游戏产品比作“鸦片”

欢迎关注“新浪科技”的微信订阅号:techsina
文/毛文琦
来源: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
8月3日,由新华社主管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精神鸦片”已长成数千亿产业》,很快这篇文章便引起沸腾,游戏从业者们被官媒比作毒贩,一时间愤怒和绝望的情绪弥漫在整个游戏行业。
很难相信在2021年,居然还有人跟当年的杨永信一样将游戏产业“妖魔化”。虽然发布4小时后原文被删除,但这篇充满了陈词滥调的文章,让人一夜梦回2000年《光明日报》那篇改变中国游戏产业命运的《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
实际上,无论是“鸦片”还是“海洛因”,其出发点都指向游戏产品的上瘾性。那么今天,《中欧商业评论》就来专心的、认真的、深度的讨论一下关于“成瘾性”的话题。
瘾,当舌尖碰到上颚,口中吐出这个发音,有种隐秘的快感。这个字刚造之时从“隐”借出,天然带有隐蔽感,是一种羞与他人说的“偷着乐”。
而今,最初带来的一丝禁忌感日渐消散,人们乐此不疲地把自己归到“成瘾”症候群中。“瘾君子”三字虽然还没有正名,但很多人一日不在朋友圈晒晒自己是咖啡重度爱好者、有点书瘾、或者有点运动癖,似乎就觉得手痒心痒。一不小心,又成了“不刷朋友圈会死星”人。
上“瘾”才是合理的?
上瘾与习惯,瘾与爱好,最初的界限俨然楚河汉界,如今却日渐模糊,很容易可以读出人们对“上瘾”的隐隐炫耀,而这背后其实指向的是我们的时代病。就像麻辣在这个时代横行天下,口味不重不足以彰显身份。
有点小瘾头,无伤大雅,何况清代文青先锋张潮树起的那面“人无癖不可与交”大旗还在猎猎作响。
“瘾”字从幕后走向台前,这暗含了一种现代性。假如我们更多地去体会“瘾”字底下独有的一种沉溺感与快感,体味游走在爱与痛的边缘的那股张力,我们对现代人会有更多的同情之理解。就好像盖茨比说自己既置身其中又游离其外,对人生的光怪陆离既感到沉醉又觉得深深地厌恶,充满人性挣扎与矛盾。
而这股力,证明了你在努力活着,而不仅仅是生存。活着就有情绪,无聊或者焦虑、悲伤或者内疚、愤怒或者恐惧……情绪的极端化往往会让人渴求解脱,而冰冷的现代文明高速前进则加重了这些情绪,让“瘾”变得无处不在。

如果说“瘾”的现代性让人们竞相贴上相关标签,那么“瘾”的全球性更是让人觉得这种姿态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存在即合理”。
把目光略微投射向历史的不远处,正如戴维·考特莱特所说,最初的瘾品泛滥,乘着商业大潮,沿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路径一路征服人类。
只要是人类,就无一幸免。毒品当然是瘾品,但不同的是它威力巨大无远弗届,没有人可以从它的魔爪下逃脱,所以它必须戴上“人类勿近”的标签。
拿比较常见的瘾品如烟草(尼古丁)、烈酒(酒精)、巧克力(咖啡因)来说,它们各自的历史都像是石头扔进池塘,激起阵阵涟漪。比如美洲的烟草最早在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的航海日志中出现,之后传到了英国、法国、荷兰、俄国乃至整个欧洲。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种植烟草,很快亚洲各国也都流行起“吸烟”。到17世纪20年代左右,烟草成为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

至于烈酒,《加勒比海盗》中杰克船长把自己看得金贵无比的朗姆酒作为报酬和他的船员谈条件时,我们仿佛隔着银幕都能闻到那浓烈的酒味。在历史学家戴维·克里斯蒂安看来,传统发酵饮料如果是弓箭的话,蒸馏烈酒则有如枪炮。
即便不是烈酒,也足够老杜写上一首《饮中八仙歌》,而李白则常常在诗中嚷嚷着要“呼儿将出换美酒”,“会须一饮三百杯”。蒸馏酒的流行与烟的时间线性传播不同,它几乎是在12世纪之后在地球上四处开花,后来形成了中国白酒、法国白兰地、英国威士忌、俄国伏特加、古巴朗姆酒、荷兰金酒六颗明珠。蒸馏酒出现的时间,则与西方打破中世纪的黑暗,元末明初的中国处于疆域空前广大的时刻相呼应。

咖啡因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瘾品,咖啡、茶、可可、可乐这四种食物让人提神上瘾正是它在起作用。关于巧克力,有个有意思的片段。
18世纪,胖胖的萨德侯爵与奥匈帝国的作家马索赫齐名,但这二人在文学史上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说起“SM”(性虐待)即是由萨德主义(Sadism)与马索赫主义(Masochism)的首字母组合而成,大多数人估计会默默一呼:“原来是他!”据说萨德被关在巴士底狱期间,他写信让妻子送蛋糕:“希望是巧克力口味的,里面的巧克力要黑得像被熏过的魔鬼屁股。”倘若我们不知道18世纪的法国,巧克力还略等于春药,我们大约就错过了这个细节。
最早中美洲的古印第安人和玛雅人对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顶礼膜拜,认为它可以助兴,前两年对“玛卡”的热捧庶几近之。西班牙人将加糖的巧克力带到了欧洲,后来风靡法国,成为贵族的专供,此后又在平民间流传开来。
与瘾品作为介质不同,另一种上瘾是行为成瘾。而成瘾行为的“全球性”是与生俱来的,有人的地方就有“行为成瘾”的可能。瘾是一种对大脑天然奖赏的强化,令人诟病的是度的把握。
某种瘾品或成瘾行为要成为全球流行,离开便捷性,那很难谈起。说到便捷,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无压力,比如价格的日渐低廉。无论是咖啡、酒还是烟,人们大都能够承担得起。而另一方面,则是时间上的无压力,这同样推广了“瘾”。
都说现代社会已经被免费的信息碎片化了,而碎片化的时间常给人一种错觉,这是“可以浪费的时间”。人们随手拿起手机就可以埋头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看网络小说,打手游,刷微信。特别是电子游戏,它与做梦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那就是感知维度的弱化。
有人说,现实世界中听觉、嗅觉、味觉、融觉、视觉五感统一,构成了人们对时间的印记。梦境中时间感很弱,玩电子游戏亦如是。正如麦克卢汉笔下“人体的延伸”,互联网把人类的需求带入虚拟世界,极大地降低了沟通成本。
而移动互联网,则把时间成本也降低了,难怪周鸿祎判断“手机是人类长出的新器官”。而这些,无疑都在助推我们的“瘾”,让它在这个时代里显得更合理,更理直气壮。

王者如何荣耀?
2017年谁没有听说过《王者荣耀》?那他一定是奥特曼(out man)。
手机游戏《王者荣耀》被戏称为“农药”,目前用户规模已超过2亿元,它的吸金能力非同小可,仅一个季度就能创造120亿元的收入,一款赵云的“皮肤”单日卖1.5亿元。仿佛宿命一般,“农药”自然让人联想“有毒”,所以当人民日报7月3日发文追问它的社会责任缺失时,腾讯控股的股价一度跌近5%,市值蒸发千亿港元。

那么为何这款游戏让这么多人去玩并且玩“上瘾”呢?
可爱的电童声“timi”仿佛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的暗号。这是一款即时战略型游戏,很多玩家表示与端游《英雄联盟》很像,画面伊始它会推荐5v5的团队多人对战。界面设定了游客登录、与微信或者QQ好友玩三种模式,结合了熟人社交和陌生人社交,这也是用户量得以激增并维持的“双保险”。每一个玩家都被称为“召唤师”,可以召唤出“英雄”。
作为一款游戏,它自然带有那些成功流行的游戏特征:目标明确、规则清晰、反馈及时、强烈的使命感与荣誉感、有效的奖励。但更愿意让人一探究竟的是它天生的超强社交互动特征,这或许才是它之所以成为手机游戏中的“王者”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一个共同体,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都需要一个互动的基础。一起“扛过枪”的人自然会有一种亲密感,因为共事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自然而非强加的,这样的友谊自然会有认同感。初识的人一起团队作战,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互动,不会有尬聊的场面。
不可否认,很多人都是冲着异性去玩的,《王者荣耀》目前24岁以下年轻用户占比超过一半,男性用户占比58%,男女比例相对比较平衡。
《王者荣耀》的成功,在于腾讯把社交网络优势与游戏优势双剑合璧。要想有默契地线上打配合,自然是线下真实的朋友(或熟人)更好。而一起玩游戏,则又可以拉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距离,甚至还能产生情侣。
2017年移动社交行业用户总规模持续超过10亿且较为稳定,这意味着全民社交已成常态。社交在这里是高频词,马斯洛关于人类需求五阶梯的理论可谓耳熟能详,其中社交需求正正好排在第三位,仅次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王者荣耀》暗合了这个需求,何况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更进一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得人际关系成为生存的核心需要。”社交的过程,是人驱逐自身孤独感的过程。身体的孤独不过是找一些同伴,而心的孤独则必须达成自我和解。
加缪在《局外人》中写道:“我常常想,如果让我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看天上的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久而久之,我也会习惯的……她常常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这里的“习惯”指向比较消极,而“瘾”往往带有一种强烈的魔性,让人绝不能置身事外。
现代人面临的一大课题就是找回自我,加强人际情感的链条,否则就成了诗人拜伦所说的“没有人祝福我们,也没有谁可以祝福”,“这才是举目无亲……这才是孤独!”陷入这种境地时,人们往往会去寻求一些安慰或者刺激,有时就得了小小的“瘾”,比如游戏。
当周边的朋友都在玩同一款游戏时,加入就成了一种微妙的“胁迫”,否则就很容易落单。游戏的吸引力毕竟还是有限的,只有在社交的加持下,“王者”才能持续荣耀,同样道理,下一个“王者”才能荣耀。

“上瘾”是常态
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人们已经很少将上瘾污名化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指责上瘾者意志力缺失或是道德有缺陷。
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库赫在新书中提到,多巴胺不仅与快乐有关,也与警觉和动机有关。“从这个角度看,成瘾是一种动机失调或疾病。”人的漫长一生中,生病当然是一种常态,“上瘾”也是人需要面对的一个常见病。你治或不治,“瘾”都在那里,不同的是每个人上的是不一样的瘾。
黄赌毒的瘾让人避之不及,但倘若是锻炼、工作、学习等原本充满正能量的生活方式呢?大多数人给自己贴上“上瘾”的标签,不过是一种言语的快感和强调罢了。
假使我们不那么纠结于真正上瘾带来的失控后果,而是借用“上瘾”一词侧重的痴迷度与快感,上瘾大概与“不疯魔不成活”有一种奇妙的对应。波德莱尔说“痛苦是唯一的高贵”。活着,人难免渴求强烈的快感,而痛苦,或许就是戒断反应。
谈论意志力或好习惯,天然有一种政治正确。那么大张旗鼓地教人如何“上瘾”,是否背负了道德的原罪?当商业世界的人用理性去解析它时,它似乎成为了可操纵的对象。
上瘾的是用户,而稳坐钓鱼台的是悠游的商家。
因为暗合了人们的内心渴求,当人们对这样的“设计”甘之如饴,手执“上瘾”利剑的商家是不是有种所向披靡的快感?对这样的“病”,商家必须要有道德的考量。但换个视角,如果商家能用一种研究客户上瘾的“瘾头”来对待客户,那这些“病态”偏执的词背后,便是一颗要成角儿的心。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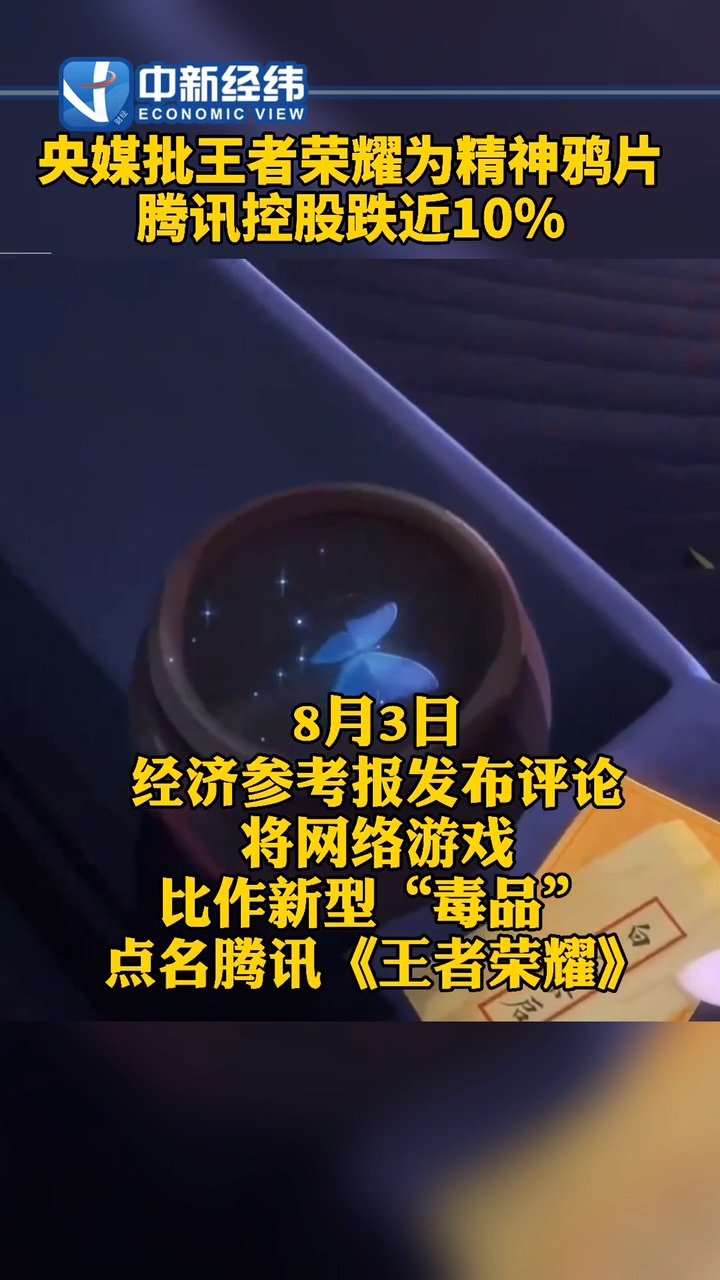 play
p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