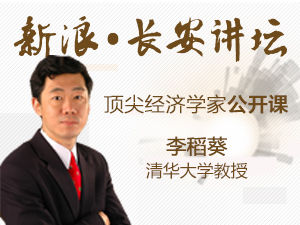营改增孤军深入遇险 重要领域改革须整体推进
■冯俏彬
最近关于改革的话题遽然升温,反映了知识界对于当前情势的某种隐忧。我也认为,当前重要领域的改革要更加重视整体推进,对于当下各方关注的营改增问题尤其如此。
营改增后的“异向”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个基础和重要支柱是由税收体制、中央地方财政体制、预算体制这3只“脚”共同组成的,分别涉及“收钱”、“分钱”、“用钱”三个环节,内在相连,环环相扣。在进行营改增这样对地方财政收入有重大影响的改革时,应当同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否则“三足鼎立”之下,只有一只脚往前走,其它的脚不动,就会形成后拉作用,引出适得其反、意想不到的效果。
作为财政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营改增已于5月1日全面实施。鉴于其高达1.1万亿的减税规模,在当前财政收入总体下行的格局下,推出确属不易,体现了政府与社会一起共渡经济下行难关的决心。但由于没有得到财政体制改革等其它方面的同步配合与策应,反而出现了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试举两个方面的数据为证。一是1-5月,我国财政收入增速总体高于GDP增速,特别是4月份,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速度曾高达14.4%。二是4-5月营业税收入大幅度增长,4月份74.8%,5月份76%,甚至进入6月份以后,理论上已经消失了的营业税仍有少量增长。营改增的本意是取消营业税,现在却出现了营业税爆发式增长的咄咄怪事。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还可以看到在2015年,全国非税收入达27325亿元,增长28.9%。这说明什么呢?一方面,上上下下都在喊减税,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在不断增加。这令人不由得想起2002年前后曾在财政界流行一时的所谓“黄宗羲定律”。现在这种情况,隐隐约约有点“黄宗羲定律”重现的意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近几年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上,似乎可以发现问题的答案。一般情况下,营业税对于各级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均在30%以上,绝对是地方财政的主力税种。早在2013年,“营改增”就开始在全国推行,但似乎一直没有正面回答这样一个关键问题:营业税取消后,地方财政收入怎么办?3年多来,各路专家学者的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但在相关改革设计上,始终没有给出过明确答案,只有各时期一些临时性、过渡性的调整方案。因此,可以说自营改增试行以来,地方财政就始终处于紧张与不确定状态。由于支出是刚性难减的,因此地方政府自然会加大对其它税收、非税等的征收力度,并发起对营业税的“运动式”清缴。上述在财政收入上出现的种种异象,就是营改增之后地方财政收入体系风雨飘摇心态下的“主动”应对所致。但这种在个体角度合理合法的行为抉择,却导致了总体层面上的加税效应,与国家的减税初衷背道而驰。
需构建新的地方收入体系
因此,在推行营改增的同时,应当同步构建新的地方收入体系。或者反过来讲,应当将营改增与中央地方财政体制这一更加核心的改革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合力推动。但现在的情况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与重要支柱的财政,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预算体制改革方面收效明显,税收体制方面却进展迟缓,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在这方面基本未有大的动作,整体改革不同步、不配套,而且越重要的改革进展越慢。这就是营改增孤军深入后,马上面临险境的主要原因所在。
中央转移支付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大国体制下,无论是从维护国家统一、保证中央政令畅通还是平衡区域差距等任一方面看,地方财政收入中的相当大部分必须来自中央给付。中央给付有两种形式,一是税收返还与分享,二是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长期以来,第一种形式在我国中央对地方的给付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至于已形成体制惯性。这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后,为了保证地方既有财力,出台的过渡方案就是将增值税的分享比例从75∶25调整为50∶50。必须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一过渡方案是存在内生性缺陷的。因为这与国家更大的目标——构建全国统一市场、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型、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等相悖而行。原因主要在于,增值税属于流转税,其背后是企业对于生产经营地点的自由选择,是资本的自由流动,税基的流动性较大,本质上并不适宜共享。地方政府分享该税的比例越高,就越会把地方政府牢牢地绑在各种产值大的制造业上、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上。而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今后要重点发展的是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地方政府的职能应主要转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方面,而不是一味发展经济。要达到这一目标,机制设计上就应当逐步降低而不是提高地方参与增值税分享的比例,从而对地方政府给出明确的预期与未来的方向性指示。当然,在操作上,逐步降低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速度可以慢一些,可以分几年,但方向不能反,信号不能错。这就是改革的整体感。
地方政府收入靠什么
当然与之相连的问题是,如果增值税不共享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怎么保证?我认为,应该主要来自中央对地方的一般转移支付。对此,地方政府最大却又说不出口的担忧,主要是中央一般转移支付太少而专项转移支付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事事求人,“跑部”才能“钱进”,大大影响地方财政的稳定性。对此,解决之道其实十分清楚,那就是加强法治,强化一般转移支付的规范程度,提高对中央财政的约束力。这方面,财政部一直在推动出台《转移支付法》,可谓是用心良苦,眼界长远。可惜一直没有正式消息传出。
在中央转移支付之外,地方还要有自己的收入体系。第一是各类地方税,如房地产税、资源税、环保税、消费税等,从性质上看都适合成为地方税。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改革的推出举步维艰。特别是房地产税,理论上应当成为继营业税之后的另一新型地方主力税种,但闹腾了十来年,现在仍遥遥无期。当然也有好消息,比如7月1日开始实施的资源税改革方案,无论是改革思路、方式,还是收入归属,甚至包括地方政府的税权等,都十分符合整体改革的方向。第二是费和基金,可以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有益补充,但绝对不能成为主体。这方面总体来讲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费”要非常规范,原则上税收重叠的一般行政性收费应当一律取消,对于大量使用者付费项目则要加强价格管理,积极推进信息公开;二是要实质性地打破费与基金“收、支、用、管”一体化机制,消除其部门化特色,增强财政部门的综合统筹能力。第三是适度发行地方债,大力推进PPP。考虑到我国尚处于城镇化的中期,通过发行债务获得建设资金,其必要性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目前地方债管理方面的行政规制色彩较重,过多约束住了地方政府的手脚,今后宜稍加放开,更多导入市场约束成分。PPP方面,虽然很多方面还需要学习和改进,但毫无疑问,这将成为未来地方政府搞公共建设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社会合作的生动体现,对缓解财政资金压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型等有着重大意义。
总之,改革不仅要有决心有行动,还要有空间上的配合和时间上的协同。营改增不只是税制改革,更是地方财政收入体系的重构,高度受制于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进程。进一步看,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也绝非仅是各自分多少钱的问题,更是事权、支出责任在双方之间的合理配置这一我国行政体制的核心所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这一体制更是中央借以引导、约束地方的“利益指挥棒”,是整体改革的关键枢纽所在。及时启动这一枢纽,方能巩固营改增、化解产能过剩等改革成果,并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贡献。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新浪财经股吧】讨论
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