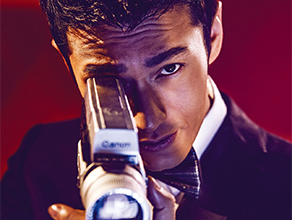辩证理解去杠杆
徐诺金
关心杠杆率的实质是关注风险
金融的本质就是运用杠杆。这是因为金融的核心功能就在于连接资金短缺部门和资金盈余部门,为资金短缺部门加杠杆,使之实现以有限的自有资本控制数倍于己的资产、扩大生产活动以营利的目的,同时也为资金盈余部门资金保值增值、分享生产活动盈利提供机制。没有运用杠杆的过程,金融的核心功能就无从发挥,各部门生产只能靠自我积累、自给自足,这样会大大限制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的扩大。
然而,如同金融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配置风险一样,加杠杆的过程同时也是加风险的过程。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戈夫(Kenneth Rogoff)作为国外两位长期从事高杠杆风险研究的经济学家,于2010年对44个国家跨越二百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存在类似的“公共债务阈值”现象,即在公共债务与GDP的比值低于90%时,政府债务与GDP的实际增长率之间存在弱相关关系;当公共债务与GDP的比重超过90%时,经济增长率的中位数大致下降1个百分点,平均增长率则下降更多。而外债的警戒值比公共债务的警戒值更低。据他们研究,外债规模超过GDP60%的国家,经济增长会出现明显恶化;这一比重超过90%的国家,经济大多出现衰退。人们对于中国高杠杆状态以及去杠杆进程的关心,主要就是源于对中国经济所蕴含风险的担心。
对风险的判断不能简单看杠杆率高低
研究者们常用负债与国民收入或者GDP的比值来衡量宏观经济的杠杆率,判断杠杆率高低的标准以“60~90标准”和“5~30标准”最为常用。“60~90标准”来自于上述莱因哈特和罗戈夫的研究,即认为公共部门债务与GDP比值的警戒值为90%,而外债与GDP比值的警戒值为60%。“5~30标准”则是一个动态标准,按照此标准,一个经济体若在5年的时间内,以国内信贷规模与GDP之比为代表的杠杆水平增长幅度超过30个百分点,之后该国将有较大可能迎来一轮金融危机。
要想从理论上和实际应用中提出一个判断杠杆率高低适度性的指标,需要有正确的认识。一是杠杆率高低的判断标准,要把静态和动态结合起来看。二是要认识到杠杆率本身作为一个经济指标,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分析使用中如果不区分经济部门、金融结构,不考虑宏观经济的平衡状况,只通过一个数值简单比较杠杆率的高低,很容易产生误导。三是杠杆率的快速升高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要加以辨析。有些高杠杆是经济危机之因,也有些高杠杆是经济危机之果,即使两种不同的杠杆率都出现快速上升,在治理中也应该区别对待。四是各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差异巨大,各个国家杠杆率升高的主导经济部门不同,甚至在不同时期同一国家杠杆率升高的主导经济部门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对其他国家的经验应灵活借鉴而不能生搬硬套,治理高杠杆率不能幻想“一药治百病”。
因此,对一国杠杆率适度性的分析,要结合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差异及增长潜力,静态和动态相结合,还要重点关注其债务资金的使用结构和使用效率。
从静态来看,要考虑该国的经济结构,包括国民收入、金融结构、对外净负债、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情况等。例如,内债的安全性高于外债,典型的对照是日本和欧债危机中的重债国。日本中央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远超希腊、西班牙等国,但由于日本政府债券主要由国内部门持有,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日本国债安全性远高于希腊、西班牙等国。之所以出现这种区别,还在于各国宏观经济的平衡状况存在差异。我们知道,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即I=S。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的储蓄率长期高于投资率,即I
从动态来看,要考虑该国杠杆率水平的发展趋势及利用效率。判断一国杠杆率是否合理、是否安全,不仅要看该国当前的杠杆率水平,还要分析杠杆率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同步,经济增长能否覆盖债务成本的增长。通过借债即提高杠杆率去发展经济,最基本的条件是借债成本要小于资金投入产出的效益。从微观来看,即边际成本要小于边际收益;从宏观来看,即债务成本要小于经济增速。因此,杠杆率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性。较高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带来收入、资本、净资产的持续快速增长,能有效稀释杠杆率,化解债务风险。而经济增速下滑将降低各类经济主体的收入,影响其还款来源,还可能引发债务危机。2003~2007年,我国就通过经济增长成功实现了去杠杆。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欧央行利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即降低利率和量化宽松)应对低迷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简单地去杠杆,也是利用了这一原理。
从动态、静态结合来看,我们提出杠杆率安全性判断的两条标准:首先一国的投资率是否小于储蓄率,即IS状态时,则需要继续考察其杠杆成本是否小于或等于经济增速,如果杠杆成本超过经济增速,则任何水平的杠杆增加都会加剧经济体内的风险,从而引发系统性危机。
我国杠杆率总体可控但结构存忧
据测算,2015年末中国非金融部门负债与GDP之比约为240%。不过,同我国历史数据对比可以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出现了快速上升,2008~2015年猛增了82.8%。按照“5~30”标准,中国经济杠杆率增长过快,这也是国内外众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蕴含了较大的风险的理由。但是,如果深入考察我国的宏观经济平衡状况、金融结构和杠杆的利用效率,我们就会发现,近几年来,我国投资率显著低于储蓄率,多年来在国际收支中我国都是净债权国,现有存量债务也以内债为主,安全性较高。同时,长时间灵活的货币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金融货币环境,尽管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了明显的下滑,但增速仍高于债务融资成本。再者,我国的杠杆率水平也反映了我国社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不发达、直接融资占比低的事实,具有其合理性。整体来看,我国杠杆率处在合理区间,仍安全、可控。
不过在相对安全的整体杠杆率之下,我国的杠杆利用中确实蕴含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从部门来看,2015年末,我国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6.5%、143.5%和39.9%,三者加总得到的实体经济杠杆率为239.8%。对政府部门杠杆率进一步分解表明,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为17.5%,地方政府杠杆率39.0%。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较低,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处在中游水平,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这反映了我国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我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风险也主要存在于不合理的期限结构中。地方政府负债期限大多在3~4年,而项目投资回收期往往长达十多年,在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这种借短还长、债务期限错配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值得警惕。
从行业看,根据对我国上市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披露的账务报表的分析,我国周期性行业和传统产能过剩行业(建筑、房地产、钢铁、电力及公共事业等)以及金融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处于高位,而新兴产业(医药、电子元器件、计算机、传媒等)和消费服务业(餐饮旅游、农林渔牧、食品饮料等)的资产负债率较低。这反映了在2008年的4万亿元刺激以及之后宽松的宏观调控政策下,一方面,传统周期性行业得到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而普遍出现产能过剩,杠杆率高企,而金融业对周期性行业过度地提供信贷支持,也导致自身杠杆率维持高位。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和消费服务业符合经济发展方向,市场需求大,行业充满活力,而且股权融资占比较大,杠杆率较低。
对于所有制结构的影响,有学者分析了我国2500余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07年,国企和民企的资本负债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动。但从2008年开始,两者的资本负债率发生了分化,看90分位数,国有企业的资本负债率从2007年的304%上升到2013年的350%,而同期民营企业的资本负债率则从292%下降到206%。关于投资效率的众多研究都表明,平均来看,其实信贷资源在民营企业里比在国有企业里有更好的投资回报率。当前我国的杠杆率不仅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分布不同,而且2008年以来信贷资源同投资回报率分布反向流动的事实,更向我们暗示了,投融资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是比去杠杆更为根本和迫切的改革。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使我国的杠杆率还存在地区差异。总体上看,西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最高,沿海地区企业次之,中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最低。
总的来说,我国内陆的传统产能过剩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杠杆率最高、风险也最集中,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长年亏损的僵尸企业。对于它们,应坚决地去杠杆,释放被冻结的生产资源,化解潜在风险。而沿海的新兴产业尤其是其中的民营企业,以及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现在的杠杆率还不太高,可以适当加杠杆以承接被解放的生产资源,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稳定经济增长。
我国去杠杆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要警惕高杠杆带来的风险,但也不可盲目采取全面去杠杆的措施。当前我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不在于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可能会引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薄弱环节的风险,“一刀切”地要求经济全面去杠杆不但没有必要,还极易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关于这一点,我们在2015年股市去杠杆中已经有过教训了。因为去杠杆最重要的判定因素在于名义经济增速是否高于名义利率,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稳增长、守底线”的策略,多注意优化杠杆结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在结构性去杠杆中,对杠杆率较高的部门,应当主要采取健康、积极、渐进的手段,适当引导杠杆增速放缓,更多地通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逐步化解高杠杆,而不是生压硬降。对杠杆率还有增加空间的部门,在增加债务融资时也要注意防范风险隐患。
第二,在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非金融企业去杠杆的过程中,要强化市场化约束,多采用企业退出、市场出清等市场化方式实现去杠杆。哪些企业需要去杠杆,哪些企业可以加杠杆,本质上还是要由市场说了算,要由企业、银行和消费者自己决定;支持企业通过并购和重组等市场化方式化解部分债务风险,实现市场出清和结构优化。同时要规范企业的发债、举债行为,加强对发债企业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披露的要求。政府千万不要过分干预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僵尸企业的不当保护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更应该彻底消除。去杠杆过程中,政府的积极作为,一方面在于深化改革消除制约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在于充分运用近几年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为企业退出提供的有利条件,鼓励运用市场机制去出清市场,不要再硬性地或者隐含地规定企业自行承担失业人群再就业任务而阻碍市场顺利出清的过程。
第三,地方政府去杠杆主要依靠政府自我改革实现。要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制度,强化预算管理,规范融资平台行为。要深化全国财税制度改革,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对称。要进一步开展地方债置换,优化地方政府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和流动性压力。同时,要多尝试推广现代化公共项目融资制度,如PPP、BT、BOT等,加强社会资本对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支持,缓解地方政府支出压力,腾出更多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和在建项目的建设。
第四,去杠杆要和去产能、降成本相互配合,稳步推进,互相支持。去产能、降成本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由于我国产能相对过剩的行业大多同时也是杠杆率较高的行业,这反映出我国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来源于信贷投放结构不合理和金融对部分企业不计成本的支持影响了市场的正常出清,甚至造就了僵尸企业。因此,去杠杆和去产能两项工作应该协调推进、相互配合,提高效果。信贷资源要减少对过剩产能行业的投放,注意对僵尸企业未清偿债务的回收,促进相关行业中企业产能的出清。同时,高杠杆率带来的利息负担加大也是企业运营成本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前几年信贷扩张阶段,低利率吸引了部分企业过度借贷,现在经济增长下行、融资成本上升,对前期债务的利息支出成为这些企业的重大成本负担。对这些杠杆率过高的企业适当降杠杆有利于其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此这两项任务也可协同推进。
第五,去杠杆、去库存要和补短板相配合。从长期来看,去杠杆有利于经济健康持续增长,但在短期内,信贷约束增强、融资成本上升以及部分企业的破产与兼并重组,又确实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冲击。因此,去杠杆、去库存要和补短板结合进行。在部分领域去杠杆,须同时制定政策对居民和有能力的企业加杠杆,在扶贫、社保、教育、科研以及中西部落后农村地区公共品供给等领域加杠杆,补足社会短板。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一个需要充分利用杠杆加快发展的阶段,去杠杆的顺利推行离不开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利用杠杆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主体、提高投资效率同样重要,用好用活金融以推动经济增长仍非常必要。去杠杆和加杠杆的节奏要相协调,同经济发展环境要相适应。要用加杠杆减缓去杠杆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和社会在平衡发展中实现优化升级。■
(责任编辑 许小萍)
进入【新浪财经股吧】讨论
责任编辑:邹枫 SF168
金融业创新层出不穷,行业发展面临挑战与机遇。银行频道官方公众号“金融e观察”(微信号:sinaeguancha),将为您提供客观及时的新闻精粹,分享独家、深度、专业的评论点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