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8年前的远大预言(3)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16日 15:47 《中国商业评论》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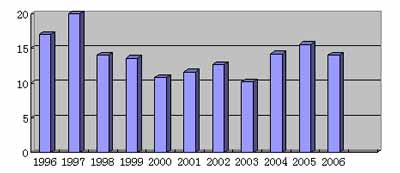 制度主义滋生的企业奴性 张跃对制度的推崇确实到了固执,甚至偏执的地步。在远大,从生产到非生产,从大事到小事,每一项工作都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比如:接待外来参观人员,事先要根据对象制定专门的、唯一的接待程序。 远大制定的正式制度文本多达300份,1900多条,7000余款,大约70万字。从员工的衣食住行到企业经营,几乎无所不包。为灌输臆想的文明,保持远大道德的纯洁性,远大实行封闭式管理,不鼓励接受新思想,提倡绝对服从。 一个显得有些极端的例子是:国家政策法规、企业动态、投资趋势、经贸信息、汇率变化、股市分析等,都是很多公司干部员工的普通读物。而在远大,公司领导畏之如虎,生怕干部们阅读后受什么影响,其封闭程度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远大总想在组织形式上标新立异,毫不考虑商业惯例、社会交际身份对等这一最重要的规则。远大最高领导、行政长官的职务名称为“助理”(后改为总裁);各部门称为“课”,相关负责人称“主谈”、“管理者代表”、“部门召集人”等。 从远大的组织机构设置及机构名称可以看出,远大崇尚的是日本管理模式。日本管理以等级森严著称。远大决策者将这一模式嫁接到了远大这一家族企业上,而中国家族企业本身就是最容易产生等级和专制管理的地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怪胎:当远大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扩大决策圈集思广益规避风险时,它却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集思广益了。 对外界而言,远大这种制度主义的管理模式似乎并无多大危害,但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第一,远大管理模型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封闭,员工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圈里,缺乏活力,缺乏交流。从人类进化史来看,任何封闭的组织,其发展都会是滞后的,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则必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给组织造成灭顶之灾。 第二,严厉、周密甚至不近人情的管理制度虽然维持了远大表面的有序,但它却催生了一群被制度奴化的员工,成为扼杀远大创新精神和员工创造性的根源。 举一个例子,在远大,倘若丢失了一台电脑,就不仅是一个管理疏漏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道德的问题,最高领导一定会暴跳如雷,责令许多部门和相关人员彻底调查。但是如果一名干部辞职离去,远大决不会花费多大精力去调查是什么原因使他离开。对凡是离去的员工(包括辞退和辞职),公司领导人都会认为他们都是属于该清除的异己分子。 事实上,由于等级森严的日本管理与最容易产生等级和专制的中国式家族企业的结合,远大的干部已经习惯了“失去自我”——不暴露真实思想、不越界做事、怠于引进新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而时时、事事看老板眼色行事。许多人只管自己按文件执行,没有责任,是非不管、正确错误不管、效率高低不管、是否影响经营不管。 当员工被制度奴化后,远大就必然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因为缺乏忠臣的“死谏”,远大错失了最佳上市机会;错失了通过兼并、合资成就空调霸业的机会;错失了及时转轨,摆脱8年困局的机会。 第三,制度主义下的远大管理体系早在8年前就孕育了一个潜在危机。那就是,如果远大公司将战略中枢或分部转移至发达城市,这种管理是绝对无法与周边环境接轨的。即使不进行大的战略位移,这种管理模式也无法适应公司的发展规模。 2005年,张跃在深圳与华为总裁任正非会晤,华为的发展给了张跃太多的震撼和启示,也使他重新审视远大。张跃说:“对比同年创业的华为,远大太自卑了。” 凡有自卑,必有比较,凡有否定,必有超越。张跃否定了自己的成绩:“远大看上去井井有条,但剥开整个制度的内核,发现我们的制度都是孤立的,系统之间大多脱节,系统本身也经常出现断层。”华为制度是流程化的制度,彼此相互连接,远大有一部分制度却是即兴产生的。 独立企业行为之伤 像远大这么“牛”的民营企业并不多见:省里主要部门负责干部来了,公司领导也常常不屑于出面接待;即便财政部官员去远大考察,在参观完厂区之后,远大送给来宾的礼物也只是一支成本两元左右的圆珠笔;每月只给高新技术开发区送一份财务报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远大提出了“不靠政府、不要政策、不走捷径”等独立企业行为。张跃认为,企业不应该跟政府有太密切的关系,因为密切就意味着不公正,甚至还有不廉洁的嫌疑。 远大提出的独立企业行为表面上虽很清高,很有面子,但太脱离现实,必然为远大以后的发展和外联工作留下隐患。因为,一个成功的企业,至少必须兼备两种能力,一种是把企业内部运营好的能力,另一种是政府公关能力,成功的政府公关可以让企业的发展事半功倍,这对于任何国家的企业来说都是如此。 远大的“不亲和”姿态很快就有了不少“不良”反应,而最激烈的当是2002年远大搬迁事件。远大搬家的直接导火索是湖南省1号工程变电站项目的高压线将与远大城相邻。张跃认为这对远大的厂房、员工的安全构成了影响,所以进行了抵制。而事实上,高压线设置本身不影响远大城的运作,只是影响了远大直升机和公务机的起降。尽管远大最后只是将总部搬到了北京,生产基地还是留在了湖南,但远大与当地政府的积怨因此公开化。 远大终于尝到失去“政府宠幸”的苦涩:当远大城因为污染问题一次次与当地农民发生赔偿纠纷时,政府的协调角色不再偏执一方了,“公事公办”成了很好的理由。当远大多次提出为“集成建筑”的样板工程特批一块地的申请时,被市政府“以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为由,一次次轻松弹了回去。 理论上,远大坚持独立企业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在当今法制不很健全的环境下,一味选择软对抗是否值得则需要商榷。 商业模式转型难题 “技术偏执”导致市场萎缩,陷入“做不强”也“长不大”的怪圈→“道德经营”胜过企业生存,对内加重企业运营成本,对外赢利乏力→制度主义导致企业奴性,阻断谏言通道和创新通道,错失自救机会,陷入连年困局→独立企业行为导致孤独,失去政府宠幸→远大走向没落→远大被迫转型。 8年前,刘亚军预测的这条没落轨迹,居然不幸言中。对一个创业近20年来无一年亏损、连续13年无贷款的优秀企业而言,似乎很难将其与“没落”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但是,远大所具备的资源和它这些年徘徊不前的发展轨迹,又确实散发出一丝没落的气息。 所幸的是,张跃开始发现了这一点。如今,远大正从战略上进行大幅调整。一方面从原来的只提供主机设备转向提供主机、分机、管道铺设的空调一体化运作,从单纯的设备供应商转型为“交钥匙”的工程承包商;另一方面,尝试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从原来的简单“卖设备”转向同时“卖气”。这意味着远大开始从一个空调制造商转型为空调运营服务商。 远大这一新的运营模式似乎转型得很成功,2006年10月的中博会上,远大一举拿下了130亿元的非电区域空调大单。 但放弃“技术偏执”和“绝不多元化”的远大在为找到新的赢利模式而欣喜的同时也开始了紧张。因为这一商业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远大需要承担对所有空调机组的投资和运营,需要建立地缘上极其分散的新型管理框架。 因此,远大要想真正转型并借此摆脱历时8年的停滞,有两个重要的关键:一是弱化或者放弃以“道德经营”为内核的制度主义管理模式,建立新型管理构架以迎合战略位移需要;二是寻求金融工具的支持,因为这一模式的完成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 而这两个关键都是远大既不擅长又很排斥的领域,放弃了“技术偏执”和“绝不多元化”的张跃,会为这一模式再进一步牺牲自己的初衷吗? 这一切都取决于张跃自我救赎的决心。
【发表评论】
|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