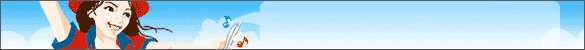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艺人郭德刚:让更多的中国人喜欢相声
★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成为“两会”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之一。
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呼吁,要对各民族杰出传承人尽快普查、摸底与认定。民间文化的活态保护,主要靠传承人的口头传授。如果传承人消失,就意味着文化的消亡。故而,对传承人的保护的关键,是要保证代代有传人。
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代表认为,我国的文化产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实力还较薄弱,路子还在探索。若要加大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处理好民族文化资源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资源是有生命力的,能够成为文化产业的支撑点。而我国目前民族文化资源流失严重,民族文化创造力在急剧下降,如此状况怎么谈得上发展民族文化?没有民族文化资源作基础,以什么发展文化产业?
而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坚守。
33岁的小郭是天津人,生长在双职工家庭的他,小的时候,因为没人管,就被当警察的父亲放在辖区内的红桥俱乐部玩。俱乐部里常常有戏曲、曲艺等演出,小郭就看,然后就喜欢上了。
8岁那年,小高拜天津评书艺人高祥凯学习评书。后来,小郭还跟天津相声艺人常宝丰学说相声。小郭很高兴也很刻苦。不管刮风下雪,他每天四五点钟起床练习基本功。评书、戏剧、曲艺、相声,什么都学,什么都练,直到太阳出来才结束。
天津相声界的常宝霆先生曾对小郭说:“学相声最主要的有三点,天赋、兴趣、刻苦,缺一不可。”小郭一直没忘。
1995年秋天,为了自己的相声梦想,小郭第三次来到北京寻求机会。“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这几样,我有自信。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折条腿,这辈子不冤。如果等到八十了,打开电视,我只能跟孩子说,瞧见没有,上边这孙子当初还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强。孙子要问我:你早干嘛去了?那太没劲了。”
刚到北京时,小郭的日子过得很苦。因为没钱,他住过平房、桥洞,经常会为几毛钱而认真算计。有时下班太晚,没了公交车,小郭便徒步从城里走回郊区的住处。有一次发烧,小郭没钱,只好把寻呼机卖了看病。最窘迫时,小郭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眼泪哗哗地流。
后来,小郭偶然认识了一位电视圈的人士,于是凭关系在些影视圈找点活儿干,才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再后来,小郭注册了文化公司,写剧本,写书,当电视节目主持,制作影视节目,出版音像制品……为了生计,小郭什么都干,但他一直没有忘记相声。
1996年,小郭开始在北京的小剧场里演出。小郭说,哪怕只有一个观众,我也要演出。有一年冬天,天上下着大雪,很冷,小郭和同事们在剧场门外的街上打着板,招揽观众。“天气很冷,路上除了我们几个,连条狗都没有。”小郭说,自己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能熬出头,小车不倒只管推,不管怎么艰难,想做就做。
10年来,小郭把做文化公司赚的钱都投在了剧场相声里。04年之前,他的小剧场相声一直赔着,一个月动辄赔个八九千,上万的时候也有。小郭不后悔,他说:“我可以为相声去死。”
10年来,小郭的观众从没有人到一个人,再到七八人,再到三四十人,艰难地壮大着。有一次,台下来了99个人,小郭在后台都乐疯了。
在小剧场里,小郭认真而自由地享受着相声的乐趣。在小剧场里,小郭有一股子“草莽气”,生猛、鲜活,无所顾忌。他的《论50年相声之现状》,对相声的几十年的兴衰作了认真的思考和讽刺,许多人都听哭了。当然,大多数时间,他的相声让大家发出了久违的会心的笑声。
有人说,小郭的活儿搁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一普通说相声的。现在老一辈相声演员走得差不多了,就显着他了。有人说,小郭就是尽了一个相声演员的本分。
2005年底,小郭火了。火的速度和程度,一点不亚于“超女”,有人称他为“超男”。他演出的小剧场常常一票难求,开始出售站票,10元一张;据说,现在小郭的剧场开始“挂号”,甚至出现了“号贩子”。据说,一个月之内有100多家媒体采访过他,还不包括采访不上的。除了小剧场,小郭开始在各大电视台和各大剧院说相声,出场费据说上了几十万。
坚守了10年的寂寞后,小郭在几个月之内,火得一塌糊涂。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个说相声的小郭,郭德刚。
心愿:能坐五六百人的小型剧场多一些,能认真说相声的演员多一些,在中国能欣赏相声的地区,观众多一些。这就是我心目中相声的幸福生活。
前十个“五年”:那时的百姓在想啥?
“一五”期间(1953-1957)
吴大芝,男,73岁,农民。
当时我刚结婚。结婚那天,中午家里吃了一顿菜饭,平时早晚都喝稀糊糊。因为还没入社,所以租着别人的田种,很想多打一些粮食,将来好让媳妇吃上一顿干饭。那时刚解放不多久,对以后的日子也没有太多打算,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只是蒙着头皮过。当时家里住着草房子,也穿不暖,很希望将来可以穿暖吃饱。
“二五”期间(1958-1962)
梁月英,男,71岁,农民。
“那时应该是刚刚入社。但是,入社了,日子反而更难过了。食堂里的“粥”更稀了,吃饭都不用筷子,就像喝水一样。每天队长一吹哨,就赶紧上工。那时每天大概可以挣到1毛钱,从来不敢偷懒,希望可以多挣一些工分,这样秋天可以多分一些粮食。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周围有人开始饿死,那会儿总感觉很可怕,幸亏平时经常挑野菜,家里没有饿死人。这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尽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只要自家里不饿死人就好。”
“三五”期间(1966年-1970年)
张卫国,男,53岁,私企老板。
三五的时候,我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村插队当知青。每天凌晨2点就起床去干农活,6点多回来吃饭,冬天也这样。很多人挑沙子的时候肩膀都压出了血,有的扁担都压折了。开始的时候不适应,觉得很苦,但是干活是挣工分的惟一途径,不干就没有口粮。一开始,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学会农活。后来都学会了。从头到尾,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顿饱饭。年轻,干活累,所以老是吃不饱,每天晚上都梦见回城在家里吃饭,一大桌,可丰盛了。
“四五”期间(1971-1975)
吴洪林,男,48岁,工人。
那时候,我该上初中了。可学校老师说,我们家有地主关系不能上。我只能每天哭着站在墙外面听,幸亏父亲说服了老师,我才有机会继续上学。后来上高中,有人来学校招飞行员,我也跑去。各项检测都过关了,我很高兴地告诉家人我快要当飞行员了。可是上面忽然说我舅舅家是地主,成份不好。我当时就想,如果可以换一个舅舅,我的生活一定在另一个轨道。
“五五”期间(1976-1980)
陶骏,男,48岁,公务员。
1978年时,刚开始恢复高考,我就一心想考大学当“国家人”。本来想到学校参加复习班,可家里农活多。我只好在家里白天干活,晚上看书。那时候,劲儿可大了,一点也不知道累。我妈老是怕我考不上,惹别人笑话,有事没事的就和我说,谁谁谁家的姑娘不错,要不托人给你介绍介绍。我不理她,只管干活,看书。当时,四乡八里,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女青年都结婚了,有的都有孩子了。有时候,夜里躺在床上,我就想,一定要考上大学,要不然连个老婆都找不着了。
“六五”期间(1980-1985)
启凡,男,45岁,私企老板。
我当时是待业青年,家里没门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做服装生意的个体户。这个举动给了妈妈巨大的打击,妈妈当时还哭了好久。那个时候,“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个体户,大多被看作不务正业、不守本分的“二流子”,妈妈不忍心让我与他们为伍。
每周我都要去200公里以外的省城去上货,早上坐很早的火车去,8点多到了省城就去服装批发市场上货,晚上再坐最末一班车回来。为了省钱,除了托运以外,我自己还要扛一包衣服回来。冬天在火车上冻的要死,夏天又要忍受蚊虫的叮咬。等下车挪到了家,都已经是半夜12点了。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妈妈为我自豪,而不是当妈妈的同学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妈妈张不开嘴,觉得丢人。
没多久,我就成了“万元户”。
“七五”期间(1986-1990)
杨大美,女,40岁,公司白领。
1986年,我刚参加工作。虽然是个学经济的大学毕业生,可我对现实经济活动一无所知。“七五”计划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这可能就是时势造“英雄”吧。但工作后的工资收入我记得十分清晰——月工资32元。第一个月拿到工资后,我将其中的20元邮寄给了远在上海的养父母,并在“附言”中写道:“你们养的鸡下了第一个蛋”。
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结婚,并把我患有哮喘病的养母从闷热的上海,接到气候宜人的大连。后来,我就结了婚,嫁了个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助理。“七五”结束时,我丈夫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当时周围人夸我“嫁得好”,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迎来了“一切向钱看”的新时代。
“八五”期间(1991-1995)
刘衍,男,41岁,国企职工。
1992年,被公司派到荷兰去进修,平生第一次知道了股票。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时,很惊讶,也很好奇,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回国后,我开始看财经类报纸,1993我就开始买股票了。在单位,我经常跟一些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讲股票,拿着BP机看股市行情。有的同事批评我,说不应该跟大学生们讲这些东西。我说,这都是政策允许的,报纸登出来的,他们才不言语。
我当时想买一台29寸的日本“画王”电视机,在别人家看见过,当时大概要一万多块钱。
“九五”期间(1996-2000)
王小娟,女,54岁,下岗职工
1995年我和我爱人都下岗了。刚失业时,我联系了不下8家单位,但人家都不要,非常痛苦,不知道生活的道路在哪里。后来,我做钟点工挣点工资维持生活,每月全家的收入只有500多元,困难是可想而知。我最渴望的是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每月能有1000元的收入,苦点累点都没有关系,我都能忍受。
“十五”期间(2001-2005)
张萌,男,28岁,农民工。
我18岁就出来打工了,在城里待这么多年,要说也是个城市人了。这几年一直都是干工程,也没啥想法,就是图能赚个辛苦钱。老板欠钱的事也碰见过,咳,在外边这么多年能一个坏人也碰不见?开始也挺费劲,一起出来的几个爷们儿,还有哭的哪,我就不信邪,咱有理啊!最后还不是要回来了,这天下还是有说理的地方,不是咱总理都过问了。也想过回家,回乡下,咱老家这几年也越来越好了,可咱在城里还是挣得多,你说是不,趁着有劲多干几年呗!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伟采访整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