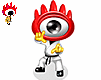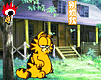| 侯若石:鼓吹贫富差距合理的经济学家有害无益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4日 19:54 新浪财经 | ||||||||||
|
 相关专题: 作者其他文章:
2004年9月4日下午2至5时,新浪财经、《外滩画报》社、《新远见》杂志社联合在京举行了“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们纷纷就效率与公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郎咸平与顾雏军就格林柯尔是否在“国进民退”进程中侵吞国有资产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先是张文魁与郎咸平就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是否正确展开了正面交锋,继而是张维迎抨击郎咸平是与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为敌,随后吴敬琏与许小年也在深圳主动做出了对郎咸平观点不尽同意的回应。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人士,甚至是网民,不由自主地卷入这场争论的人越来越多,争论本身更已由“郎顾之争”发展成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向、路径的大论战,争论的话题同样也在向纵深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不时提起但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的话题也被一再“旧事重提”。 最新召开的这场研讨会表明,此番论战的焦点已经上升到了改革开放中效率与公平的理论高度。 而我们也注意到,出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在这场大论战中官方声音始终付诸阙如。 本次研讨会由《外滩画报》副总编辑陈涛主持,出席会议的专家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侯若石教授、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星斗教授、中央编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金雁女士。 以下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侯若石教授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发言(讲话者根据速记稿修订)。 (侯若石:来晚了,题目不是很清楚。刚才对研讨的题目稍微知道了一点。从效率和公平问题谈起。 主持人:今天希望集中在这么几个问题上,一个是公平和效率,从20年的中国改革实践看这个问题,目的是想厘清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经验和看法,下一步如何走,另外是转型期的权利与财富。是在财富的重新分配过程中,权利已经起到的作用和应起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就是国外的产权改革的经验,特别是俄罗斯、东欧改革的一些经验问题。) 效率和公平,既是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它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引起全球关注的问题。当然,在现阶段,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要追求效率,就很难实现公平;要实现公平,效率恐怕就要受到损失。但是,从人们的良好愿望来看,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是效率和公平的均衡,既有效率又有公平。人们心里希望是这样的,不希望它是矛盾的。如果出于公众利益,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肯定是效率和公平能够均衡更好。然而,人类的这个理想至今没有实现。 人们理想的效率和公平的理想的状态会不会实现?我觉得总有一天会实现。人类正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换句话说,我们正处于争取效率和公平两者平衡的过程之中。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的,同时需要不断地纠错。 我之所以说人类正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有两个根据,一个是2000年的联合国的各国首脑会议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任务是减少贫困,提高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改善他们的医疗保健条件,使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现在,联合国和国际多边经济机构每年都要评估发展中国家实现目标的情况。另一个例证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企业主张企业负起社会责任,这个问题要多说一点。 企业要负社会责任,是不是社会良知的呼唤和社会道德的要求?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企业要负社会责任,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换句话说是效率的要求。如果说这是效率的必然要求,那么效率与公平的失衡的程度可能要减轻。如果说企业负社会责任只是社会良知和社会道德的要求,就很解释谋求利润的企业为何要负社会责任。近年来,这股浪潮越来越高涨,连道.琼斯公司都搞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财富》杂志也搞了有关的指标。发达国家的政府间政策咨询研究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9年制定了公司治理指导原则,提出包括劳动者和企业所在社区的居民在内的利益相关者都要参与公司治理。今年,该组织对这个文件做了修订,更突出地强调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劳动者的作用。这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一致的,即企业要尊重劳动者的利益,也要保护生态环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制定了跨国公司行为指导原则,也特别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2001-2003年,该组织已经召开了三次关于执行这个原则的研讨会,并出版了研究报告。西方一些著名企业在会上报告了执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一些跨国公司不但向公众发表年度财务报告,也发表执行社会责任的年度报告。 再有,前不久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到中国来。在此以前,美国的劳联产联提出中国企业不执行劳工标准,要求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所以,赵小兰到中国来了解情况。美国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由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部长到我们这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来检查劳工权利状况?实际上这并不奇怪。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出于效率的考虑。也就是说,不是说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仁慈,而是出于效率的考虑。这是为什么? 自从人类有社会分工以来,就产生了组织社会生产分工的特定方式。我讲的是社会分工,不是个人分工,需要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按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生产组织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市场,就是亚当斯密说的用“看不见的手”组织社会生产。第二种生产组织方式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用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的话来说,就是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从产品设计开发、加工制造、销售到售后服务,由一个企业大包大揽,所以企业要大而全。它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产物,是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全球性石油危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过度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为特征的大规模生产方式难以继续下去。所以,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同时,人们开始怀疑在规模化生产方式条件下出现的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怀疑现代企业制度。美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和媒体开始批评现代企业制度。在这方面,出版了一些专著。比较有影响的是哈拉尔写的《新资本主义》。他尖锐批判了现代企业制度。 同时,美国经济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后期,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跟日本相比下降了,所以美国制造业企业在重振竞争力的过程中就塑造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是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IBM公司发现电脑是一整块,不兼容,又不好修理,所以开始研究电脑的模块化,把电脑分为微处理器、硬盘、内存、显示器键盘等不同的模块。每个模块都是相对独立的产品。大家分别研究这些相对独立产品的时候,只需要制定共同的规则来实现怎么把模块连起来,至于模块内部怎么开发、怎么设计由负责模块的人解决。就这样电脑被分解了。那么IBM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也要分解。他没有立即这样做,所以苹果公司超过它了。经过几年IBM发现不分解不行了。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美国硅谷中小企业专搞某个模块的研发,另一方面大型加工制造企业专门负责生产。原来由一个企业包揽的产品的研发、零部件加工制造、组装、物流、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分解到多个企业。现在,世界上有五大专门加工制造电子信息产品的零部件和组装整机的企业,这五大企业专门给其他企业加工产品。这样IBM把相当一部分加工制造业务移走了,实行了外包生产。15年前,一台电脑由一个企业完整地生产出来;今天,任何一个电脑企业都不能完整地生产电脑,只能生产一部分。由于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技术和模块化技术的进步,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被分解。分解以后,设计、开发、营销、服务分到不同的企业。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称为企业之间的价值链合作。也有人认为这个现象发展下去,将形成全球生产体系。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企业之间如何合作?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由于发达的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应用,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方便,企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更容易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选择合作对象?对所选择的合作对象是不是值得信任?去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主题就是世界经济要发展,就是要增强信任,这不是空穴来凤,他们写了好几篇研究报告,也进行了调查。盖洛普公司调查的结果是,公众最不信任的就是大型企业。为什么信任问题被突出出来?就是因为企业被分解以后,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必须以信任为前提。信任如何建立?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制定一系列标准,如产品标准和技术标准,执行标准,落实标准,最后产品符合标准,才值得信任。所以才有了标准之争。在中国,有人提出我们要振兴民族精神,夺回制定标准的权利。 企业之间的价值链合作一定要实行产品标准和技术标准。但是,这是事后的标准。在合作之前,如何解决信任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能善待员工,能善待附近的居民,即保护生态环境,这个企业就是值得信任的。于是,产生了企业的社会标准,即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如果一个企业能实施这两个标准,这个企业基本上可以信任。因此,社会标准的产生是企业之间进行生产合作所必需的条件。换句话说,企业担负社会责任是生产的客观需要,而不只是社会良知的呼唤和社会道德的要求。由于企业之间的合作执行了有利于公平的社会标准,保障了生产合作的效率,所以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就有了实现的希望。 对中国来说,是否执行企业的社会标准,已经成为影响出口业绩的大问题。现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委托发展中国家企业加工产品,对加工企业执行社会标准提出严格要求。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给外国公司加工产品的企业已经受到外国公司企业的社会责任执行情况的检查。如果加工企业不执行社会标准,将要冒失去出口订单的风险。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了一本书:《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描述和分析了跨国公司检查中国加工企业执行企业社会标准的情况。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不足之处是,没有把这个行为与生产和效率的需要联系起来。深入研究的任务落在中国经济学家肩上。要求企业担负社会责任,使企业行为有利于劳动者和全社会,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之间生产合作的效率。这预示着效率与公平正在走向平衡。当然,要完全实现两者的平衡,仍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希望的曙光,应该大踏步地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但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派,一方面片面鼓吹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把效率看得高于一切,忽视了社会公平。对此,我提出了质疑。我的专业方向是研究世界经济,没有专门深入地研究过国内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企业之间的价值链合作提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出现,而现代企业制度已经过时。这启发了我。两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于是写了《质疑现代企业制度》一文。这篇拙文引发了一场争论。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反对者指责我不是搞学术研究,而是搞阶级斗争。在他们看来。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的意见很中肯。如有人提出:有破,但立的比较苍白;批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没能提出新的见解。也有人认为我是一个外行。功底不行。本人学术水平不高,也受到专业领域的限制。我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经济,这决定了只能从国外经验认识现代企业制度的变化。我用两年时间阅读了大量国外资料,写成《质疑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一文。但是我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远未完成。初步计划分三大部分:一、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出发,分析决定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历史,提出质疑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观点。二、从技术进步的历史事实出发,提出数字化技术和模块化技术是挑战现代企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三、从社会公平原则出发,指出改造现代企业制度的路径。显然,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起码是一部专著才能容纳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检讨把现代企业制度奉为至宝,随便是可行。根据国外的经验,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子可能走得太单一了。 中国已经加入全球生产体系,很多企业给人家制造、加工产品,不能不考虑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展自己?如果一味地按照大型一体化企业垂直的模式发展行不行?争当世界500强,一味追求企业的大而全,能不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是不是只能民营化和搞MBO?能不能多种办法并用?这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从当前的发展看,现代企业制度丧失生产组织方式的主导地位,可能分三步走。第一步,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被分解。第二步,垂直一体化企业的等级制管理向扁平方向转化,公司治理制度发生变化。第三步,产权制度发生变化。第一步的实际进展比较明显。这在电子信产业、汽车产业、机械设备产业、服装业、种植业都有体现。第二步正在起步,已经出现了公司治理的新理论,主宰企业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企业之间的协调也被纳入公司治理的视野,公司治理不再只是公司内部的事务,国际规则已经浮出水面。例如,由发达国家政府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了《公司治理准则》。第三步尚处于胚胎阶段,还在经济学家的头脑中。以股份制为表现形式的现代产权制度仍然有生命力。尽管出现了变化,但目前所能看到的是知识产权的作用上升,物质产权的地位下降。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提出:“将理论层面与物理层面分开是数字化革命的重要结果。这给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影响。现代法认为产权的转让是通过物质资产的转移来实现的。但即使不通过物理媒介,我们也可以传递数字化信息。反过来说,传递了信息也不等于转让了产权。即:以产权为前提的财产的可转让性变得不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信息数字化之后,信息可以被自由复制和加工,这样你就无法通过控制物理媒介来独占未来的财务收入。”那么,传统的物质产权制度就要变化。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现代产权制度诞生在100多年前,我们应该研究它是否过时了。 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不应该拿落后的东西唬人,也不要拿错误的概念骗人。有一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企业社会责任说成就是企业捐赠。我想,经济学家必须要科学、客观地反映情况,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不能一拍脑子就说话,还不允许大众批评,非要站在大众对立面,这太武断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应该允许大家讨论。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讲话,不能随便乱说。有人过去说股东主导模式最有效,现在又说要反对国有企业股份制。他的前后两段话是相互矛盾的。人们到底要听从他的哪段话呢?他又说:“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在他看来,只能实行私有化了。我不反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民营企业家,有很多困难我也知道。但说要善待民营企业家,说这个话有什么用?什么叫善待?我们对犯人也要善待的!谁不善待了?提点意见就不是善待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到底如何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谋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这个过程肯定是漫长的、肯定是曲折的,但是不能动摇,如果片面追求效率就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这是西方国家200多年来,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独立以来的惨痛教训。阿根廷当年比澳大利亚还要发达,现在怎么样了?我们绝不能重蹈只求效率忽视公平的“拉美病”的覆辙。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如果改革只谋求效率,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当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立一个目标,有人可能说这个目标太空泛了,可是这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尽量往理想状态方向前进。我们努力了才能实现,不努力永远实现不了。西方出现财务丑闻之后受损失最大的是企业,效率与公平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但人家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无论是政府、学者、普通老百姓,大家从心底还是希望最后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听众提问:你刚才说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越走越窄,还有哪些可以做,会越走越宽?) 侯若石:我读了西方关于公司治理的一些文献,从公司治理角度考察,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是多种方式的,应该比较各种方式的优劣。比如说MBO,在西方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有证据显示,越搞MBO,效率越低,所以有人持反方面的意见。 首先,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公司治理问题,路才能越走越宽。根据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公司治理只有经营者和所有者两个主体。作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应该实行利益相关者的模式,员工、债主、社区居民都可以参与公司治理,会不会损失效率?也有研究表明,这样不会损失效率,反而提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者的地位问题。 其次,不可片面追求企业的大而全。有些企业设立了许多附属企业,为的是搞资金转移,为侵吞国有资产制造方便条件。企业不一定是越大越好,发达国家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分解,组成企业之间的减链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同时鼓吹贫富差距的合理性,这样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经济改革的主张,我觉得是有害无益的。国有企业肯定要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肯定也要改革,但我们一定要尽量争取效益与公平平衡。就像孙立平老师讲的一点一点地做,尽量向这个方向靠拢。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国企产权改革路径选择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