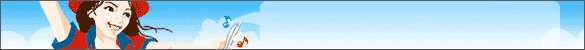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晏礼中 上海报道
引子
四周是黑的,像一个深渊。
王炼利拉亮了楼道里所有的灯。宿舍楼里寂静无声,中华造船厂的职工们都回家过年了。除了她。
王炼利把堆在桌上的书移到一边。摆上一碗米饭、一盘红烧肉、一瓶白酒。
月光透过窗户,映照得满屋凄幽。
无意间,她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她把一缕光亮浓密的头发从前额上拂开。那眼睛是深黑而明亮的。她喜欢自己的眼睛。她觉得它们很好看。
她拧开酒瓶盖,为自己斟了一杯。
“王炼利,今天是大年三十,你不要哭,等到将来你有好日子过了,不要忘记今天”,她用平时讲话的声音对自己说。然后,一饮而尽。
那天是1979年的除夕夜。
一
2003年6月,《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仲伟志上网查资料。他要撰写一篇关于上海房地产的报道。一篇题为《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文章引起他的注意。观点深刻而尖锐。作者署名王炼利。他引用了“这位学者”的一些观点。不久,仲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王炼利在邮件里说,“仲记者,我不是什么学者,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女工。我也不是什么‘老师’,我的“课堂学历”只到初中二年级,我是老三届中的67届初中生,我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是自学的,我曾经被人视为‘精神病’整整二十年……”
……
2005年的7月20和21号,我坐在王炼利家的客厅里。沙发、书柜、缝纫机,有平面的地方占满各种资料和杂物,纸箱、皮箱一直堆到天花板,不到十平米的客厅局促而凌乱。墙上挂着毛主席和她儿子女朋友的照片。墙纸早已泛黄褪色。
“如果不是你执意要来看看,我是根本不敢把任何人请到家里来的。”她无奈地说。
“条件太差了,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20年前什么样子现在就是什么样子,只是房子更加破旧了”,她从冰箱里取出一筒大雪碧,给我倒了一杯。
她找来很多照片,有的放在信封里,有的裹在塑料袋里,有的装在相册里。大都是她年轻时的照片。她照相时不戴眼镜,把它握在手里。眼睛好看的人都不喜欢戴着眼镜照相。乌黑的长发剪短了,染成栗子色。那样白头发冒出来时看上去不会那么明显。
她今年52岁。
二
时光回到半个世纪前。在一个叫做“洪福里”的弄堂里住着11家人。王炼利家住二楼。她家有一个十平方的晒台。四周围着方颈圆肚的花瓶状石栏杆,不疏不密的间隔恰好能容下她的脸盘。四下里是些低矮的民房。远处是上海大厦、海关大钟和和平饭店的尖顶。视野极为开阔。
王炼利喜欢呆在晒台上。她常把脸贴在栏杆缝中,羡慕地看着楼下玩耍的小朋友。她像所有小孩一样,渴望到楼下和其他的小孩一起玩。但她不能。
“楼下都是野孩子,你以后要当淑女,不能跟他们玩,你得在家念书”,即使在上学前,她就这样被父母要求着。
父亲在著名的康元印制厂工作,是高级制板师傅,曾被国民党的飞机接去重庆刻过印金元卷的板。解放前,她家就有电风扇解暑,能拿龙虾当早点。三年自然灾害时,父母把金条卖了换高价点心给她吃。父母很疼她。她家生活不错。尽管有些孤独,但她从来没吃过苦。
在她记忆里没有不识字的时候。她从小习惯一个人躲在家里读书。先是母亲的越剧唱本,然后是小说。第一本小说是《青春之歌》。那时,她小学二年级。她喜欢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发誓要做林道静那样的女革命家。
儿时的记忆是幸福的,直到小学五年级的一天,她发现了关于她身世的那个秘密。
那天下午,她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母亲正在整理抽屉。一个信封掉在地上。母亲迅速把这个信封收进抽屉。王炼利从小有个习惯,只要是文字的东西都喜欢看。她看见信封上的那几个字——“上海市公证处”。
从母亲慌张的神情和那几个字里,她隐隐约约感到这个信封里有一个跟她有关的秘密。
母亲下楼后,她从抽屉里找出封信,藏到衣服里,跑到晒台上打开。里面有她的小照片,有一封公证书。
就这样,她知道了亲生父母的名字,知道自己是“抱来的”。
她突然明白,为什么父母从不许她跟弄堂里小朋友一起玩,为什么父母比班上同学的父母都要老很多。
她突然明白,父母成了她的养父母。
她想知道她的亲生父母在哪里,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要她。
谁都知道她是别人不要的孩子。但没有人会说。
心怦怦地跳,她很害怕,想哭却又不敢哭。她不敢让养父母知道她知道了。
她偷偷把信放回抽屉。她把秘密埋在10岁的心里。
三
王炼利从冰箱里取出些冰块,放在我喝了几口的雪碧里。
“后来我才知道生母是在土改时遇到我生父的。她从农村跑到上海我姑姑家做佣人,我的祖父那时候是洋行买办,我父亲算是公子哥,上海叫‘小开’。那时候,凡是少爷玩的东西,他都玩。我生父后来去了美国。1989年,我找到了他,第二年他回国看我,我3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我父亲在2000年去世,我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在美国,但从来都没有联系。他们觉得我是少爷和佣人的非婚生小孩。是耻辱”,王炼利眼睛直勾勾地朝前看着,太阳在一道白云后面黯淡下去。上海的天气闷热而潮湿。
丈夫姓施。他们在1977年经人介绍认识。那时候,世界名著看得多是件时髦的事情。他发现她读了很多书,便对她有了兴趣。两年后他们结了婚。
她决定嫁他是因为他不在乎她曾受过批判,他决定娶她是因为他知道她受批判是因为看书。他喜欢看书的她。
四
王炼利喜欢抄书。
她抄李白、杜甫、高尔基的诗歌,抄毛泽东的书中的成语故事,抄鲁迅文集……
1969年,她把自己抄成了“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典型,被中华造船厂公开批判。那年,她十七岁,进厂工作不到一年。
“她会放毒,你们不能跟她接触。”团委对车间里的青年工人说。她想不明白,居然连抄毛主席书中的成语故事也能抄出“修正主义的毒”。
她记得那次“审讯”。
“你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著作,而去学这些成语典故?”批判她的人问道。
“荒唐,毛主席写的所有东西都值得我们学!”她大声地回答。
“你已经到了推一推拉一拉的边缘!你必须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交待问题,不能像挤牙膏!”
“你们这是对‘一打三反’的阶级敌人说的,我绝对没有到这个地步。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我不是阶级敌人。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对待,就使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你们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来对待,那你们的立场到哪里去了?”
“你年纪这么小,嘴巴这么老,你的问题非常严重,你必须写检查!”
“我没有问题!”王炼利的牙咬得紧紧的。
她绝食三天以示对“批判”的抗议。
很长时间里没人敢跟她说话。一系列的机遇与她擦肩而过。
1972年,她希望换个环境,与一个上海水泵厂的工人对调。办手续时,党支部书记说:“她能说会道,长得蛮漂亮,调出去会迷惑人,我们要对人家单位负责。”
1974年,全车间工人师傅推荐她上大学,车间门口贴出红榜,名单却不上报。理由是:受过批判的人怎么能上工农兵的大学?出红榜是为了照顾老师傅的情绪!
1975年,张瑞芳带队到厂选电影演员,在劳资科看到她照片后要见她,领导说,“她上夜班很辛苦,算了吧”。
1977年全国首次恢复高考,她高分通过录取分数线。她的体检卡上却赫然写着:“68年患过精神病”。
精神病?!一个莫须有的“精神病”。梦魇一般。整整二十年。
五
中华造船厂有5000多人。厂子大了,难免有些轻薄之徒。他们总想在她身上讨点便宜。她漂亮,又没什么亲戚朋友。可他们总是一鼻子灰。她性子“比火还烈”。
18岁时她腹腔肿瘤开刀。出院回厂后,她发现人们看她的眼神怪怪的。
“她子宫拿掉了,不会生孩子,想男人想疯了,想成了精神病”,颠来倒去就这几句话,已经在这个工厂里沸沸扬扬传了开去。即使是不知道她名字的人也都知道厂里有个挺漂亮的小姑娘“想男人想成了精神病”。
蚊子咬了人,还嗡嗡叫。这个故事,有文化的人和没文化的人都接受了。她抱定了宗旨不跟任何人解释。她知道解释也没用。哪个精神病人会承认自己有病?她一个姑娘家,又怎么向别人解释自己是有生育能力的呢?
连同班组的女工们有时也会围住她,用手指指着她,一勾一勾地说,“咦,王炼利,咦咦,王炼利……”像逗一只小狗。
那是她最熟悉的一条马路。从宿舍到工厂。路不宽,一站地的距离。她走了十七年。
她记得那天下午,她像往常那样走着这条路去上班。一个男的从工厂里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交错的一瞬间,他朝她脸上吐了一口口水。
“想男人,哈哈哈”,那人头也不回地迅速消失在这条马路上。
她掏出手绢,擦干了那令人恶心的液体。脸上发烫,身子却冷得打颤。抬头望望天。蓝天凝结得那么严酷,连一些皱褶也没有。她觉得浑身骨骼都脱了节。有些受不了。返回宿舍,倒到床上。突然间,号啕,颤抖,煞不住那呜咽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憋了许久的怨恨,借着枕头的柔软尽情发泄出来。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她必须发泄出来。否则,她就真的疯了。
她想起自己的初中语文老师。一个干瘦而腰板始终挺得笔直的老头。1966年那场风暴来临时,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张没有。他中庸,从不参与任何派别,不卷入是非纷争。他度过两年多的太平日子。一直到有一天早上,他以“逃亡地主”的“身份”被揪出来。那天,他穿着长衫,头颈挂着一把算盘,站在学校大礼堂台上,任人打骂,丝毫反应也没有。
当天晚上,他给家人留下一张“我到黄浦江去了”的条子,去了。
她不会“去”黄浦江。在那些被内部清醒和外部谣言夹攻的日子里,她通读了马恩四卷、列宁四卷、《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她喜欢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她知道了希腊神话,知道了歌德、浮士德……
“熬下去,总有出头之日,未出头时,多读书,拓宽知识面,调整知识结构,以待时机来选择我。不能向命运屈服,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不会,永-远-不-会!”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文革结束的消息从《美国之音》里传来。文革后期,一些人开始悄悄躲在家里“听敌台”了解外面和里面的世界。消息并不令她震惊,她早就觉得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她感觉自己的光明来了。
她错了。厄运依旧在她生命中游走。人们忘了她曾被批判过。人们只记得她是个“精神病”。
1985年,她上万言书到船厂党委,党委作为解决文革中遗留问题的特例让她换了个船厂。不过,对方厂提出中华船厂要接受他们厂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才能接受她。好在一个了解她的原团委书记刚当上劳资科长,他接受了这个条件。王炼利调离了折磨她十七年的中华船厂。
她终于到了新的环境。但一星期后,“精神病”的传闻又像瘟疫一样蔓延了进来。好在她在这里毕竟是个“新人”。一年后,“王炼利”同样在这家新厂里出了名。她获得该厂思想政治工作论文大奖赛一等奖和为振兴船厂献计献策大奖赛一等奖。
1988年,她开始从事工程预算。她从图纸都看不懂到能完成土建、电气、管道等一系列预算工作,全靠自学。她自学学完了高等数学,用数理统计法写出专业论文《论高层建筑的混凝土含钢量》。她始终记得列宁的教导:学习、学习、再学习!
她踏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轨迹。她不再是“精神病”。从18岁到38岁,整整二十年。
六
王炼利家住在六楼。那是上海港务局的家属楼。丈夫的房子。从1982年春节搬过来算起,已经23年。外出时,碰到邻居,她会朝他们点头笑笑。她没有和他们聊过一次天。原来忙上班、学习,现在忙着搞研究。每天,王炼利总是来去匆匆。
“早在70年代,我就知道有一天会有记者采访我,但没料想到52岁才有人来”,王炼利笑了笑。
她是通过互联网进入人们视野的。
2002年9月,她从外地回来。朋友告诉她,现在上海房价涨得厉害。她凭直觉感到报道中那些所谓的涨价理由“都不是理由”。她觉得经济学家们都在为房地产商们“说话”。她开始查阅大量公开资料,两个月后,她写出《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市场》,把文章发到网上。她出了名,成了“上海地产论坛九大思想者之一”。人们把她视为为弱势群体呼喊的学者、教授。人们开始叫她“王老师”。
她喜欢“老师”这称呼。她喜欢智力劳动所带来的成就感,就如同她不喜欢被当成一个初等劳力挑挑拣拣一样。她知道自己身份低微,从未想过要和那些经济学家们分庭抗礼。她尊敬他们,也觉得他们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不是命运捉弄,她早就和他们在一个平台上对话了。现在,她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王炼利现在每天都很晚回家。从今年春节开始,上海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委托她做一个“金融危机离我们有多远”的研究报告,并借给她一间办公室。她觉得这是对她的极大信任。为此,她至今没跟他们谈论报酬。
七
临行前,我为王炼利拍照。结束后,她走到镜子前端详自己。
她像所有爱美的女人一样关心自己日益凋零的容颜。她摸摸自己的脸。曾经雪白而紧崩的皮肤,已经布满皱纹,而且松松垮垮。她最漂亮的时候,是她人生最灰暗的时候。漂亮不但没能为她争取来幸福,反而成了她开始梦魇的地方。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打算去整容。这也许能让我的心态平衡一些,很多跟我同年龄的人,看上去比我年轻得多。我心态有点不平衡”。
她转过身,长长叹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