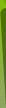经纪人:有性婚姻无性尴尬 婚姻与性的时代变奏(2)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2月02日 14:30 《经纪人》 | |||||||||
|
“一夜情”是个泊来词,和它有关的几个英文单词是one-nightstand,sexwithstranger,可分别译作一夜风流、邂逅性交、随意性交。从这些字眼儿上可以看出它们都指的是发生在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也包括了那些有直接金钱交易的性行为。
时至今日,再用道德的说词衡量“一夜情”这种社会现象不仅是不客观的,而且也未必有意义。《新周刊》曾做过一份有6263人参加的调查报告,32.22%的“一夜情”对象为网友。网友是“一夜情”的主力军,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许多专家认为,网络兴盛的最大卖点就是个性化需求得到了实现。现代人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倾向于摆脱繁琐过程直奔主题的快速获得满足的途径。 一项数据表明社会上对“一夜情”持否定态度的人数约占12%;可以接受,但自己不会去尝试的占40%;而表示可以接受,且有机会愿意尝试的已经达到近35%。有人认为,“一夜情”背后有着明显的亲和动机。 亲和动机是社会动机的一种,指个体害怕孤单,希望和他人一起建立协作、友好联系的一种内心诉求,其产生也与感情状态有着紧密联系。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这种渴望缩短人与人之间距离、加强相互依托和支持的愿望更为强烈,与陌生人说话,在他们看来是夜幕下最安全也最温暖的一种交流方式。 如果用“传统”的眼光看,它似乎被称为“一夜奸情”更为恰当。还有一种说法,是把“一夜情”,定义为那些没有现场的金钱交易、双方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但是没有婚姻目的指向的、双方自愿发生的性行为。或者是按流行的说法,总结为“不求天长地久,只愿一时拥有”的性关系。值得关注的是,“一夜情”几乎是不带有贬义的,且因为“情”字得到了突出,而使之具有明显的褒义倾向。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院长江晓原曾说:“我认为中国人近20年来的性状况正在逐渐改善,我们离性健康更近了。这主要表现在:人们能够更大胆、更自由地表达和满足自己的性欲望了;人们对于性的看法更宽容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性看成丑恶的东西,而是看成美好的事物了。” 一个有3687人参加的网易网站调查可能会说明些问题:在100对婚姻中,喜欢上网和异性网友调情、至少有一个情人的占19.2%;结婚以来都是一种姿势做爱的占9.5%;一方无论如何努力,另一方总是“走神”的占6.4%;丈夫回来倒头就睡、对妻子态度冷淡的占4.7%;而近一个月无性生活的占14.5%。 动机有了,条件有了,余下的只有两条:有没有合适的对象,以及当事人愿不愿意去做。所以,有过“一夜情”的人,事后总会说自己“当时正好碰到了‘可心’的,而且大家‘心情都不错’”的人。 进步与退步的悖论? 婚姻自由和性自由似乎是一对永远也难以调和的矛盾,婚外性的增加,某种程度上和中国人的离婚观念有关。当离婚还是被大多数中国人看作一条危途时,为了挽救婚姻,而“爱”又不能舍弃,婚外性就成为一个不算是好办法的办法。性学专家潘绥铭认为,婚外性对婚姻的破坏远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严重,只不过在这种冲击下,婚姻、爱、性三者的关系变了。 这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性化”刚刚开始盛行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性正在偷偷摸摸地越过婚姻,形成一股不小的社会风气。社会科学院的性学专家李银河当时在北京做了小范围的调查,承认自己有婚外恋的占有效调查人数的3.7%,80%以上的人对任何形式的婚外性行为都持严厉的不容许态度。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就对有爱婚外性关系的容许度要比无爱的性关系要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是中国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另一面,性健康领域正在流行着一个新概念:不安全性行为。什么是不安全性行为?亚洲和大洋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刘达临教授这样解释:从广义上讲,凡是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性行为,包括计划外怀孕、心脏病人的性行为等都是不安全的。从狭义上讲,不安全性行为则特指容易引起性病、艾滋病的行为。有资料表明,虽然通过性交传播艾滋病、性病的警告不绝于耳,但全球仍有41%的人在过去12个月里与新伴侣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也就是说,这种随机发生的存在不安全隐患的性行为比我们想像的要多。 很显然,刘达临教授的定义仍然局限于生理层面,仅是就性疾病的传播而言。其实,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中,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不安全性状态正愈演愈烈,成为家庭幸福的杀手,比如无性婚姻、婚外恋、“一夜情”等。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理健康,也严重伤害着人们的心理健康,并成为社会问题的隐患。 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开放的原因,在性的问题上,中国的男男女女们依然存在着种种暧昧、模糊,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观念:要么非常保守,视之为“洪水猛兽”,不能坦然地享受性爱的愉悦;要么过于放纵,性行为混乱,乃至冲破了道德与伦理的底线。 无性婚姻的无性企盼 世界文化中的无性族 性冲动甚至被部分人认为是推动人类文明的最强大动力。但是,性并非对所有人都是这样重要。专家指出,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性没有丝毫兴趣。人们一开始认为这部分人只占人口比例的很少部分,但实际上,他们为数众多。 据介绍,无性婚姻大致可分成两种,一种是“想做爱却不行”,另一种是“可以做却不做爱”。前者原因比较明确,一般起因是性功能障碍;而后者,却是心理上的,如夫妇离婚、感情受挫,或者认为性是肮脏的、不洁的。 在分析了英国一份针对1.8万人进行的性习惯调查后,加拿大安大略省布罗克大学的心理学家博盖尔特发现,有1%的人同意这样的观点:在性方面,我对任何人都没兴趣。 “无性族在自己的父母和亲朋面前大胆表露自己的观点,宣扬无性生活像选择双性恋或同性恋的人一样,是一种健康的性趋向。”《新科学家》记者韦斯特法尔指出,“他们实际上是在向世人宣布,他们在性方面不是有缺陷的人,更不是性无能。他们有着健康的性选择,而且不应被别人所忽视。” 他们自称“无性族”,并把字母“A”(无性的,asexal一词的首字母)作为自己的符号。他们捍卫自己的无性生活权利,并视之为正常生活。这些人已经形成自己的活动圈子,私下里寻找同道中人。在他们看来,没有性的生活不等于没有感情。现在,他们的观点已经得到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故事:不俗婚姻的最俗结局 我们熟悉的是台湾女歌手蔡琴和知名导演杨德昌的无性婚姻:1984年,杨德昌因拍摄电影《青梅竹马》而结识了蔡琴。一年后,蔡琴和杨德昌喜结良缘。“无性婚姻”的想法是杨德昌提出的: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不让这份感情掺入任何杂质,不能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于是,他们同居一室,却不同床而卧;他们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婚后,蔡琴继续为人们吟唱情歌,杨德昌则成为“台湾新电影”的实力干将。他的每部电影都融入蔡琴无怨无悔的付出。 谁知,10年后,这段不俗的婚姻有了一个最俗的结局:杨德昌向蔡琴摊牌:他有了外遇。表面上恩爱的夫妻关系轰然倒塌。杨德昌给他们的婚姻下的结论是:“十年感情,一片空白。”也许,这个故事说明了性之于婚姻的重要。 应“运”而生的无性婚介 2004年12月10日《法制晚报》报道,南京婚介行业新添了一项业务:为丧失性功能的单身男女提供无性婚姻介绍。 从12月8日正式推出“无性征婚”业务,才半个月的工夫,老板罗俊已经接到了600多个咨询电话,咨询者最远来自新疆乌鲁木齐,还有河北、湖南、山东、安徽等地的询问者。已经在罗俊这里登记征婚的有将近100人,罗俊说,要不是地域限制,登记的人会更多的。 罗俊说,来应征无性婚姻的有两类人:一类是生理上有障碍,久治不愈,于是对性生活再无期望;另一类是在心理上排斥性生活,他们在曾经的婚姻生活中受到了打击,于是向往无性的“纯净”婚姻。“相比之下,前者更加多一点。”罗俊说。 “爱情和家庭的温馨可以替代一切。” “我无性但我有爱,我有爱就想有家。” “激情、完美的生活,我20年前就不敢想了;孤独对我来说,早已经受够了。我只想要有一个家,有一个生活中的她。吃饭时,我给她添饭;睡觉时,我给她盖被;这辈子,我给她一生的爱” …… 应征者的征婚留言写得很真诚,让人动容。而一个打工者的留言被公认是最坦白、最真诚的:“我不行,所以不敢找一个正常的女人,怕婚姻不长久;你也不行,也不敢找一个正常的男人,也怕婚姻不长久。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呢,我们也可以组建一个家庭啊,有吃有穿,互相照顾。” 罗俊说:“他们最渴望的是有个家,有个能够相互照应的人,平平凡凡地过一辈子。” 该婚介所负责人罗俊告诉记者,开办全国首家无性婚姻征婚介绍所,主要是让更多失去性能力的男士勇敢应征,重觅自己的爱情。自11月中旬开始策划“无性征婚”公开报名电话至今,短短1个月内,来自广州、上海、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省市报名应征无性婚姻的人数已有200多人。 陆良(化名),今年30岁,小伙子条件十分优秀,1米78的个头,河南某大学研究生在读,家庭条件也好。小陆说,大学时,他曾有个十分相爱的女朋友。可是毕业后在两人同居的第一天晚上,他竟然发现自己生理上存在问题,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第二天一早,小陆来到医院,经诊断,他的生理问题是先天性的,十分难治。几年来,花费数万元看病,可病情却没有起色,女朋友也离开了他。“谁愿意和我这个半废人过一生呢?”小陆苦涩地说。从网上看到无性婚姻征婚的消息后,小陆起了试一试的念头:“这个征婚所的出现让我改变了想法,如果能找一个愿意和我过无性婚姻的妻子,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两人携手到老,有什么不好呢?” 有性无性皆显人性 北京师范大学学者赵合俊认为,今天中国人的性权利主要在3个方面得到彰显:(1)非生殖的性快乐也被看作目的;(2)性被看成是个人的事,是一种私人化体验;(3)任何人的任何性行为与性关系,只要没有妨碍和伤害他人,都被认为具有正当性。 敢于在这种活动中抛头露面的人,他们对无性婚姻的主张恰恰彰显了人对自己基本权利的坚决维护,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的觉醒。这种建立在夫妻双方性权利义务关系平等基础上的无性婚姻,是一次更高水平上的人性的回归,是人道主义的胜利。 由于我国社会伦理文化发展中的德性倾向,历史上对婚姻中的“非性”因素关注更多,耻于把性放在婚姻的中心地位。这是南京个案如今被赞许的深层次的原因。当然,现在社会伦理已经出现了新变化:普遍承认婚姻中性的中心地位,承认性在确保婚姻质量中的基础作用。 诸多媒体和专家发表见解:性生活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无性婚姻的当事人也需要性爱抚和性关怀,性能力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性生活的完全缺失,尤其是对感情基础非常好的“无性”男女来说,绝不是世界末日。与一些正常人名存实亡的婚姻相比,无性婚姻甚至有它更稳定的优势。 现代婚姻以及由婚姻所缔结的家庭,其主要功能包括生殖繁衍、追求幸福快乐与人的自我完善。生殖繁衍和由性交产生的快乐途径的缺损,并不代表婚姻基础的全部丧失。南京案例说明有无性婚姻这种社会需要,同时又能满足自主性和不伤害的两大伦理原则。 默然昭然不如坦然,同情理解不如给予帮助 性无能,是一个难以启齿的个人隐私问题。在传统的家庭、社会观念中,“性无能”是一件羞耻和不光彩的事,是人群中的异类。社会上的歧视、偏见、嘲弄,甚至是恶意的攻击,好似一座无形的大山,常压得一些弱势群体透不过气来,使他们备感生活的冷漠和无望,阳光与他们无缘,欢乐与他们远离。如此之下,导致一些失去性能力的人产生心理畸变,对生活失去信心,或性格孤僻,或性格暴戾,成为不能享受现代浪漫生活的孤寂群体。 但这样的观念也应该改变了,正如人的其他缺陷一样,自己需要坦然面对,社会更需要把同情和理解变为帮助。 “20年了,我渴望有个家。”一个并不奢望的渴求,一个难以在阳光下追求的愿望,让多少失去性功能的人在形影相吊中苦苦地祈祷,夜深人静时独自品尝着生活的不公和苦酒。他们同样有血有肉,同样有炽热的情感和细腻的个性。他们渴望社会理解,渴望人性救助,渴望阳光透过阴霾。 然而,现实显然缺少这样的社会空间和人性契机,关爱的话语总是与他们无缘。南京市丘比特婚介所冲破社会传统观念的桎梏,积极为特殊人群代言搭桥,努力创造无性婚姻环境,让性无能者鸳梦得圆,这既是一种婚姻观念的巨大进步,也是对夫妻生活的一种新诠释。因此,无性婚姻走向社会,冲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境遇已不可阻挡。从这个意义上说,给无性婚姻更多的关爱和生存空间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 更何况,所有的婚姻最终都将走到无性的阶段,只是时间早晚不同,因为上帝在塑造人类生命的同时,就已限定了性的“更年期”。到丘比特婚介所应征“无性婚姻”的老年人也占有相当的比例。与其他类似征婚者不同,这部分老年人几乎没有提到关于性的话题,大多数仅仅要求对方“懂得体贴人”就行。此外,这些老年人征婚都要求“特别保密”,尤其是要对子女“保密”。 让无性婚姻沐浴在阳光下,让无性人群相偕在阳光下,这是现代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消费也理财-生活 > 《经纪人》2005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