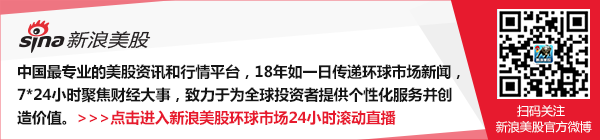北师大教授钟伟:美国也许应考虑加税 而非减税

钟伟:美国也许应考虑加税,而非减税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钟伟
编者按
美国启动自里根政府以来最大规模税改,以期推动增长、推升就业、改善企业及居民收入状况、引导海外资本回流。同时也令特朗普政府局面有所改观。对减税增赤,有人称之为“空中加油”,有人忧虑国际税收政策竞争及资本流动异常等外溢冲击。本报所刊之文,以独有视角给出了有些出人意料的解读。
一个经济学家在餐桌上,用餐巾纸勾画了一条简单的曲线,这根线的大致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税率过高,那么企业家创业和国民就业的热情就不足,偷漏税的动机就强烈,导致政府的税基薄弱,因此高税率不一定能帮助政府征到较多税收,也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如果政府采取较低税率,那么企业创业和居民就业的热情高,偷漏税动机弱,导致政府的税基扩大,因此低税率也许反而有助于政府的财税汲取,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低税率和高税率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最佳税率”,此之为拉弗曲线,构成了经济学供给学派主张减税的基础。许多学者甚至认为现行税率当然高于最佳税率,减税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认定放水养鱼总是有利于政府税收的可持续增长。
另一个经济学家叫做曼昆,在29岁时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也曾长期在白宫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对拉弗曲线和供给学派的评价不高,曼昆将此类学说称之为夸夸其谈之术士和庸医。
本文为什么要从拉弗和曼昆开始?因为特朗普政府在推动美国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减税计划,这令不少企业家和学者一片赞叹,并对本国如何应对资本外逃和产业迁徙感到忧虑。作为安静的旁观者,我们也许可以更超脱,而不是更焦虑。也许从当下看,美国减税计划作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多过作为美国精英层达成共识的产物,它并非美国当下最紧迫的经济政策。从略微长一点的时间(例如5到10年)看,美国更需要的也许是加税,而不是减税。这样的判断,会令到许多期待各国也步入减税行列的拥趸感觉不快。
低税率不等于好政府
政府职能的差异性,导致税率高低的差异性,低税率不等于好政府。世界银行每年搞一个全球各国企业总税率负担的排名表,在2016年这个排名是和普华永道联手进行的,美国企业的总税率在44%,德国为49%,各国政府总税率从略高于20%到超过200%皆有之。高税率国家中,有经济增长上比较失败的非洲国家,也有表现差强人意的拉美国家。中高税率国家中,有北欧这样社会经济表现很好的国家,也有日本、法国这样经济低迷的国家,以及处境平平的中东欧国家。而许多低税率国家,要么是避税天堂,要么是政府几乎丧失了税收汲取能力的失败国家。单纯以税率高低来说明税率应当如何调整,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
税率是否恰当,看起来应当结合政府收了这些税办了什么事来考虑。政府和市场不是对立的,坏政府扮演的是市场的“掠夺之手”,好政府则扮演市场的“扶持之手”。税收本质上是私人部门向政府购买服务,而各国政府的职能差异甚大,历史轨迹显示,OECD国家的现代政府职能,和二战之前有了很大不同。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断膨胀。政府是否提供了足够良好的安全法治、教科文卫、市场秩序、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良好职能,决定了政府是否应当汲取足够多的税收,也决定了企业和国民是否纳税的意愿高低。小政府少纳税,大政府多纳税,现代政府不仅是吃饭财政,也是建设财政,更是社保财政。类似中国和北欧等中高税率国家的税收正当性,恰恰在于政府职能的广泛和良好。为维持美国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转,看起来美国应该在国民安全、控枪、教育、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投入更多,也应该寻找到奥巴马医改的政策出路。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证据证明美国企业或个人能够替代政府更好地提供上述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
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美国政府是个治理能力良好的政府,也观察到政府职能的不足,以及持续的财政缺口,那么你选择把钱留在美国的大企业和大富豪,还是由政府汲取并改善一些迫在眉睫的公共职能?凡事过犹不及,东亚普遍倾向于强政府,美国则总体倾向于小政府,但还是略微存在右翼政治家习惯减税、左翼政治家青睐扩张政府职能的微小差异。特朗普是在步里根和小布什的后尘,其减税计划力度既非空前,也不会绝后。
同样地,在批评一些国家的中高税率时,也应该谨慎,不能陷入古典式的“小政府、轻税负”的幻觉,你应当批评的不是税率,而是政府是否恰当地用好了财政资源,是否有大手大脚乱花钱、罔顾国民利益的惯性?
减税就一定会成功吗?
难有减税成功的例子,不乏加税成功的范例,为什么总视而不见?有趣的是,人们对政府减税普遍持有好感和赞誉的同时,几乎列举不出一个像样的案例,说明某一个相对重要的经济体,在二战之后,遭遇经济转型困境时,通过减税政策,成功地刺激了经济增长,甚至达成了经济转型。至少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
有人立即会抛出伟大的里根政府,传说中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是运用减税政策的范例。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神话。撒切尔在经济上的成功,主要源自其对工党长期执政后,英国经济几乎高度国有化和缺乏活力,撒切尔先是小心翼翼地、最终是大刀阔斧地推进了私有化。里根时期是典型的“咆哮的八十年代”,围绕美国的主要是冷战、滞胀、拉美危机。从1981到1988美国经济始终步履蹒跚,里根经济政策更多是艰难地控制住了恶性通胀。真正让美国经济进入大放异彩的“新经济”时期,是克林顿政府了。1990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达到4.3%,通胀大约在3%,股市则黄金十年。也有不少人简单地将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科技和股市的繁荣,归结为里根政策的后续效应。这需要超越逻辑的想象力。里根和克林顿之间隔着老布什总统,老布什任期内美国忙于战争,经济平平。克林顿政府恐怕难以接受其政绩是里根栽树,克林顿乘凉的说法。有甚者可能会说,至少里根的冷战思维,促成了重大科技进步,例如作为互联网雏形的美国军用阿帕网的发展;也促成了苏东剧变,为1990年代全球化创造了良机。这种说法仍然是奇特的,冷战思维和里根减税神话无关,如果你非要将互联网和苏东剧变做如此解读,也许不如说,政府对重大科技研发的关切和投入,美国对开放共享的全球化的坚持,有利于美国而惠泽全球。曼昆对供给学派的嘲讽,主因就在于他洞悉了里根主义,除了带来美国的债台高筑,并没有收获其他什么。后续的小布什、奥巴马都尝试过减税,政策效果总体短期有效,长期遗患,贬多于褒。相信特朗普不会是例外。
在我们举不出减税成功推动增长和转型案例的同时,却意外地发现一些加税效果不错的例子。克林顿时期美国总体是轻微加税的,却无损经济增长,甚至帮助美国回到了黑字状况。
我们需要一个有一定经济体量的政府,其减税计划取得大放异彩之结果的案例,来说服我们自己。关键可能不在于税收的加减,而在于如果这些钱留在私人部门时,他们是用来投资和创新,还是沉睡在大企业大富翁的账户中?抑或是在政府手中转化为高效普惠的公共服务?现实世界中,更多的政府为维持生计在苦苦加税中,例如日本。
难以捕捉的最优税率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约在2003年2月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份广告,广告发起人是1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包括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莫迪里亚尼、索洛、夏普、诺思等人。他们批评小布什的减税计划是个严重的误导,尤其对免除企业股东股息税的做法提出激烈批评。在美国或法国均曾出现过一些富翁名人支持加税或者反对减税的广告。
拉弗曲线粗略地给出了最佳税收的假设,但在真实世界中,这个税率难以捕捉。税收的加减无论是整体性的还是结构性的,都是一桩非常棘手的事情,更是一桩难以评估政策效果的事情。
不妨尝试询问一下企业家,总体上政府应当汲取多高的企业税负才是大致合理的?这样的总体性问题,大多数企业家可能不感兴趣。
具体到每个企业和企业家,尝试询问针对他的最佳税率是多少?答案不会困难,越低越好,最大胆的企业家可能会要求零税率,并进而对零税率表达不满,因为企业家还将要求政府补贴。你真的愿意相信,存在一个既保护企业家精神,又激励其纳税热情的最优税率吗?经济增长的成果应当由政府、企业和个人相对合理地分享,因此企业税负是否合理,可能更多地应观察企业净资本回报率和波动率,以及富裕群体的财富状况等指标,而不是企业家对税率满意与否。
同样地,如果政府对财政资源的配置能力有信心,或者已明显地观察到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试图以扶持之手弥补市场缺陷,则不必过于忧虑企业家的抱怨声。企业家喜欢说企业家精神,公务员喜欢自称公仆,而教育从业者则被美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云云,无非是社会有分工,应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而已。所谓企业家精神,也许本质就是为逐利而冒险、实干多于空谈。企业生态中,中小企业依赖成本和效率,创造了大量就业,但通常生命周期不长,聚财有限,真正依赖创新从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少之又少。大企业则往往八面玲珑、八面来风,并有一部分逐渐发展到依赖行业集中、限制竞争、全球避税来积累巨额财富。不少专注跨国公司研究的学者发现,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要凭借一国之力,对类似世界五百强这样的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日益困难,全球资金调度和税收筹划之复杂,使得一国调整企业税的政策效果往往不彰,人们要考虑的不是特朗普的企业税从35%降低至20%,而是究竟有多少大企业的真实所得税率高于20%?究竟有多少大富翁按照累进式个人所得税,以最高档纳税?如果海外市场利润率更好,避税天堂税率更好,那你试图增加企业利润汇出限制、降低企业汇回门槛,试图将财富圈在本土也可能很艰难。
不要太过于相信最佳税率这种事情,对企业家和富裕群体不能涸泽而渔,但也不必迁就企业家的抱怨,抱怨税率,抱怨监管,等等。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过大,已威胁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分配。同样地,有学者指出,美国贫富分化之剧烈,已使得克林顿时期至今,美国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改善有限。特朗普在竞选时期对美国社会弊端的尖锐批评,折射出他试图通过减税计划,给富人以逆袭之机,但这未必妥当。
徒劳无益,不如创新
稍微年长一些的中国人会记得,北京西单之东南角曾有赫赫有名的邮政大楼,它曾作为8分普通邮票的图案走遍全国,如今曾经辉煌的邮政大楼已更名。美国经济史学家也记录着,鼎盛时期的美国邮政,为喂养邮政马车的农地曾占据美国耕地的1/10!如今各国邮政系统都在走下坡,原因在于电报电话和互联网使得尺素飞鸿日益稀罕,科技进步推动了人们告别邮政马车和邮差的年代,告别电话程控机和接线员时代,甚至告别了电信运营商,却已不知不觉中依附在微信中,期盼快递小哥来。产业变革的道理是一样的,人们总是尝试以更为高效、廉价、可靠的方式,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推动这一进程的是科技进步。工业文明战胜农耕时期,数字经济取代福特流水线,势所难免。当人们察觉一些国家的制造业在空心化,在不断延伸其全球布局,而本土仅仅保留部分研发、利润和销售中心时,隐藏之义是,一些传统工业已不足以提供有竞争力的净资金回报,它们不可避免地或萎缩、或迁徙、或接受工业4.0的洗礼,或从传统大规模制造转型为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产业必须升级,低附加值低利润回报低客户好评度的工业必须逐渐出局,其所占用的这种生产要素才能释放,为新型工业和服务业腾挪出空间。因此从长期看,推动经济发展的不是要素投入,不是全要素生产率,不是税率高低,而是邓小平在198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一个相对严肃的话题是,大国的再制造业化是可行的吗?特朗普看到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凋敝,以及类似苹果、波音那样的公司在深度全球化,减税计划能够挽救美国制造业吗?再制造业化,日本曾经尝试过,失败了;欧盟也曾尝试过,失败了。日本和美国都已度过了工业推动GDP增长的鼎盛期,要再工业化?很难成功。特朗普减税计划对美国主要行业的影响,极其粗略地可以分为主要受益行业和非受益行业。巴克莱银行的研究显示,受益较多的行业是电信、消费零售、银行、媒体、交通等平均税率较高的行业。它们目前的处境都比较艰难,西尔斯关闭了,沃尔玛也不景气,银行在撤并网点。但这些行业究竟有多少国际竞争力?几乎无法从减税计划受益的行业是硬件/软件服务业、仪器设备、生命科学、制药等,其目前税率就低于20%,所以难以受益。很不幸的是,这些行业都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强势行业。
好了,减税计划确实在扶持衰落行业,冷落强盛行业。衰落行业获得的减税收益,究竟是用于投入研发,谋求涅槃;还是维持现状,得过且过?为什么扶持衰落行业会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或转型?也许将减税计划的收益,让渡给向墨西哥等地迁徙进行再布局的传统行业,让渡给R&D支出或全额抵扣所得税,让渡给教育科研部门,让渡给创造就业能力较强的服务业尤其中小企业,更为妥当一些。科技创新是莫测和冒险的苦修苦行之路,它将机会留在未来,而再工业化,无论是以减税计划还是振兴计划为名,都将希望寄托给了昨天。
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
实现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无非是发钞、增税和赤字三条路。就国家治理而言,财政和货币是两条裤腿,看起来彼此独立,但只要视线向上,就不难看到关键所在,财政和货币都是国家信用背书而已。减税计划当然会增加财政赤字。上一次日本、美国录得财政盈余的年份分别是哪年?很少会有人记得吧。赤字,赤字,还是赤字。
什么是一国的健康财政?传统说法是量入为出,政府不应透支国民的未来,尽量不留赤字。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则是以丰补歉,即通过逆周期的操作,在经济景气时增加财政汲取但不增加支出,在经济衰退时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财政汲取,但从跨代的长周期看,财政收支仍然是大致平衡的。很不幸,西方国家的财政既非量入为出也非以丰补歉,而是寅吃卯粮日复一日,政府赤字余额不断积累。似乎新财政现象是,赤字仅仅是政府背书的永续债,国家不倒,举债不止。本质上,日本危机是财政货币双危机,欧债危机是南欧债务危机,次贷危机也是华尔街利用“两房”透支联邦信用的债务危机。
特朗普减税计划的通过,是以未来十年美国再增加1.5万亿赤字为代价的。这究竟是个什么含义?简单粗暴地说,就经济增长而言,预测减税计划在当年和之后,能够推动美国经济多增长1.7%和1.1%,此后正面效应逐渐衰减并持续约五年。用相当于GDP的8%的财政赤字,去购买不太确定的仅相当于GDP5%的增长,值得吗?同样地,据美国税收基金会的研究显示,特朗普减税计划大约能创造630万个就业岗位。而1.5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650万中位数收入的美国人8年的总收入,这值得吗?更多的人可能会怀念欧盟的国民基本收入计划(Basic Income Program),简单来说就是按人发钱计划,它至少是将钱送到了普罗大众,而不是富裕阶层税负更轻。
广义地,弥补当期财政缺口,无非是发钞、加税和举债三条路径。里根让美国历史性地债台高筑,在他任内,美国从全球主要财政盈余国沦落为主要债务国。而奥巴马任内,美国经济累计仅增长了30%,联邦债务却实现了翻番,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则膨胀了5倍。当下美国财政赤字在约19万亿美元,对GDP的比例略高于100%,以当下美国就业人数约1.55亿人、中位数收入并假定其储蓄率为10%来看,美国国民需要约45年才能清偿联邦债务余额,这还不包括州债务和市政债务。除非特朗普减税计划使美国经济出现超出预期的景气,否则未来10年美国联邦的债务负担率不会减轻。
除非你将美国联邦债务看成永续债,否则要么发钞,要么加税,要么削减政府开支。总体上美联储对美元相当负责任,对发钞谨慎克制,总体上美国政府削减支出的余地很小,那么控制债务膨胀的方式,看来只有加税。减税带来的债务膨胀是个梦魇。在美国债务负担率不低于100%、美国经济增长不高于3%的搭配下,美国将被迫锁定低利率政策,过高的财政赤字余额,吞噬掉经济的成长。
我曾写过《国家破产:国际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研究》一书,其中探讨了西方国家的沉重债务,并臆造了“重债富国”一词。西方国家因国民选票不敢削减赤字,因债务积累是历届政府之集体责任,而非当届政府之过。逐渐地,财政赤字常态化、长期化,福利许诺和减税举措任期化,这将使美国推动创新转型的爆发力日益衰减。整个西方社会都在呈现出财政政策斡旋空间逼窄,不得不更多依赖货币政策的迹象。同时持续的赤字积累,要么折射出西方国家不愿承受转型之痛,要么折射出西方国民正在以有损其后代福利的方式,维持其少劳多获的生活。
减税既非紧迫,时机也恐不妥
李肇星先生曾说过一个小故事,他和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联合国开会时候,奥尔布莱特约李肇星到走廊走走聊聊,期间奥卿就问李大使,中国外交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李大使打太极说,是为了友谊。奥卿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外交无非是为了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leadership),并分清谁是伙伴国(partnership)。李大使问,那伙伴国之外呢?奥卿说,既不服从美国领导,又不是盟友,那就只能是敌人。总体上说,二战以来, 美国为维持国际秩序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得还相当不错。但时至今日,美国的政策开始悄然转弯。
特朗普就是引领美国政策、社会和经济转弯的总统,美国是否需要坚持全球领导力的同时,容忍国家间的和而不同;是否继续引领开放的全球化还是有所退缩?是延续建制派的主流精英思想,还是总体滑向保守和孤立的右倾?大量问题纷至沓来,一个大国的转弯谈何容易,无论是竞选还是就任,特朗普一直处于争议中,美国社会看起来,更像总统和国会都坐在驾驶舱,而方向盘却只有一个,这种“双驾模式”使美国和全球都深受困扰。缓解这种历史性转折时的“双驾”困惑,给美国及全球一个清晰和可预期的声音,也许很急迫,但这也许恰恰是特朗普应当做到,却无力做到的。就在这样的纷扰中,摇摆的国会通过了减税法案,只待总统签署。和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的减税计划相比,这次的减税计划几乎是在嘈杂和仓促中出台,诸多细节尚不清晰。
也许困扰美国最紧迫的挑战,是如何在“双驾模式”中找到平衡妥协的方向,那么,减税计划是否也在一个可能会收效良好的时机落地的呢?也未必。里根减税最重要的积极效应,是增加了就业,一些野心勃勃的军事计划也推动了科技投入。这是由于当时美国经济处于多次恶性通胀和失业高企之下,减税对纾缓失业的好处比较明显。小布什的减税计划除了收获一些对小布什本人的批评之外,其实没有太多实效。奥巴马的减税也许有助于美国走出次贷危机,但付出了财政赤字从不足10万亿美元飙升至19万亿的代价,也使得中产阶级一蹶不振。相比之下,特朗普减税的时机,和小布什仿佛相似。
小布什是在开放的全球化和放松监管的热潮中向右转,而特朗普这是在这种热潮渐次退潮中向右转,面临政治风险。同时,小布什试图减税的2003年,是美国经济熬过纳斯达克泡沫和9·11之后,经济渐有起色的时点。从2003到2007年,美国经济表现还不错,并不太需要减税计划来添把火。此时甚至连日本都创下了连续经济增长69个月的记录。欧洲和中国经济也都还不错。当下的美国经济有些类似2003年,经济总体也是温和向好,如即将卸任的耶伦所盛赞的那样,美国走出了次贷危机,金融机构更稳健,通胀温和,失业率仅4%,已接近充分就业。美联储乘势在捕捉加息缩表的机会,使得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相信欧元区和日本也会陆续跟进。
此时机选择减税计划,特朗普能够收获什么?指望2018年经济增长超过4%吗?这有难度。指望连续十年每年创造65万个就业岗位?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这也许仅能收获劳动参与率或者起薪水平的提高,何况真正能创造较多就业的小企业并未从中受益多少。指望再工业化吗?此行不通。指望美国企业2.6万亿美元的利润回流吗?这需要美国本土有更高投资回报率的吸引,和对避税天堂的抑制。指望中低收入群体显著改善吗?不幸的是,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不是预期的10%,而是12%,税制对富裕群体和高收入的中产更有利,对中低收入的中产和穷人不太有利。指望金融稳定吗?次贷危机以来,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已增长了三倍,估值比美国GDP大两倍,高于巴菲特合理估值的上限。国债市场既有美联储缩表的压力,再遭遇未来十年赤字多增1.5万亿美元的压力,叠加中东和东亚主要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迟缓的背景,美国股债市场维持平稳的困难不小。
从紧迫性和时机选择、从减税力度和结构看,特朗普减税计划都称不上伟大,它看起来更似匆忙间的政治产物,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经济方略。如果美国经济从2015年开始已持续温和复苏,那么恰当的政策也许是先让出货币政策常态化的空间,弥合内部分歧,并在增长持续改善之后,择机选择结构性加税,改善政府职能、科教投入和基础设施。如果未来数年美国经济遭遇意外不测,对冲性的财政方案也在情理之中。
各国担忧什么?
美国减税冲击几何?各国该担扰什么?全球税收政策竞争?资本外逃?都不是。
和对难以证实的拉弗曲线以及鲜见的减税成功案例迥异,网络舆论场充满对特朗普减税计划的赞美,并顺带对全球税收竞争、跨境资本流动担忧,相当自然地,人们期待各国政府采取类似的减税计划。
许多人忧虑全球税收政策竞争,这只是一种微弱的可能性。里根和撒切尔两人的政策在时空的巧合早已不见。从小布什开始的美国减税并未引领全球效仿风潮。时至今日,整个西方财政政策的斡旋空间在缩减,对超级央行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依赖在加深。几乎可以肯定,刚从欧债危机泥潭中脱身,并看到复苏曙光的欧元区不会贸然减税,欧央行货币政策如何常态化看来更紧迫一些。日本则还是会尝试提升消费税。至少在当下,主要国家都会视美国减税计划的落地效果及其外溢效应,然后再酌情应对。
许多人忧虑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资本外逃会否加剧。资本总是追逐利益,流向风险收益高的区域。当下美股高企美债低迷,加上美联储加息所表的压力,大类资产很难对此进行战略配置。不仅如此,全球外汇储备余额从2015年开始持续下降,欧洲、中东和东亚都缺乏可向美国回流的足够资金。特朗普减税计划会一定程度上有抽水机作用,吸引一些资本回流,这可能主要是美国大企业部分海外利润的汇回,以及外国资本向美国科技行业的投入。
新兴经济体会否因特朗普减税而加剧资本外逃?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资本外逃峰值过去了吗?资本外逃有方吗?资本在美国能挣钱还是会遭遇追税?总体看特朗普减税主要是着眼美国国内,兑现竞选承诺,而并非针对其他的某一国。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家清楚地知道,在美国办企业挣钱不易,而从美国政府全球追税中逃脱更不易。因此并不必担心特朗普减税会导致这些国家的企业家蜂拥进入美国,何况即便进入了,也未必是坏事。
那当下新兴经济体面对特朗普减税计划,就无所作为了吗?并非如此,首先要安抚企业家,让他们清晰地看到和珍惜本国经济发展的远景,同时也提醒他们注意本国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异性。其次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精简政府职能,压缩甚至剥离那些低效甚至无效的政府投资,以及着手探索和财富分配结构相适应的税收体系。再者,对人力资源、研发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府投入和财税倾斜,通常比作为止痛剂的减税,更具长效性。
作为叙事的结尾,政治家们和实证经济学家们其实也并不太忧虑,他们很清楚各国政府职能的差异性和总税率的不可比性,他们也清楚西方财政赤字的不可持续性,他们清楚企业家逐利避税的本性和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他们更清楚作为权宜之计的减税政策的局限性。许多人都在饶有兴趣地观察一个有趣样本——日本。日本既是量宽型货币政策的始作俑者,也是政府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发达国家,更是遭遇潜在增长率低下和老龄化少子化的持续困扰。过去25年,日本仍然维持在一个高人均GDP和高质量国民生活的平台之上,日本将如何应对看似山穷水尽的财政和货币问题?无论日本最终是成是败,其经验或教训都足以为后来者仔细剖析,并对重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有所裨益。(编辑 欧阳觅剑)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