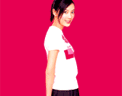|
法制变革与金融创新
——兼评《证券法》、《公司法》修改实施后的金融创新法制环境
- 蔡 奕
《证券法》、《公司法》(以下简称两法)的全面修订是我国资本市场法制建设的标志性事件,许多重大条款的修订为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创造了条件。两法尤其是《证券法》的修订,调整了证券市场的制度框架,增加了证券市场交易品种,为市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空间。但从证券立法史分析,基本法律的修改只是为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提供了条件,要将法律提供的空间转化为现实的自主创新实践和资本市场生产力,还必须满足若干要素。本文旨在明确法制变革和金融创新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对两法实施后的金融创新环境进行客观的评估,并试图解析实现金融创新的法制要素。
法制变革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
套用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济创新”理论,金融创新即在金融领域内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新的结合,是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形成的市场改革。它泛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手段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内容。它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制存在着密切联系。
法制框架的确定对金融创新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在一个守法的社会中,法制的基本框架决定着金融创新的命运、空间和发展方向。在一个保守的法律框架下,市场主体欠缺创新的意识,甚至于法律本身抑制创新的发生;在一个开放的进步的法制框架下,不仅法制本身为创新提供了空间和条件,而且市场上也会有自主创新的市场导向。
上世纪90年代我国《证券法》制定时恰逢亚洲金融风暴,我国证券市场也出现过度投机、高风险事件频发的趋向,因此《证券法》创设了相当多的保守的刚性条款(禁止性或限制性条款)。尽管这些刚性条款在早期的确起到了抑制市场投机气氛、缓解金融风险的作用,但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许多条款显得过时,过于保守的规定成为金融创新和市场发展的掣肘。这些备受诟病的条款包括禁止发行上市一体化、发行手段和交易场所单一、禁止银行资金入市、只允许股票现货交易、禁止融资融券、禁止国企炒股等等。滞后的法制框架制约了不断发展的金融创新需求,使得近年来业界进行的一些创新努力始终在“地下”或“灰色”状态中运行,并时时面临着突然夭折的风险。
金融创新的发展对法制的变革有重要的反作用
法历来有“良法”与“恶法”的区分,亦有“恶法非法”这样的命题。以证券市场的发展为标尺,能够有效促进资本市场长效发展、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可称为良法;反之,不能促进市场发展,甚至妨碍市场创新与活力的法律可称为恶法。无论是良法还是恶法,实际上都有促进金融创新发生的作用。良法对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当然体现在它为金融创新提供法律依据、制度空间、规范章程、法律保障方面,那么恶法与金融创新又有何种辩证关系呢?
明代的方孝儒曾经就守法求治当中的良法与恶法之间的关系写下如此一段精彩的文字:“夫法之立,岂为利其国乎?岂以保其子孙之不亡乎?其意将以利民尔。故法苟足以利民,虽成于异代,出于他人,守之可也。诚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虽作于吾心,勿守之可也。”这实际上是“恶法非法”原理的一个重要表述,将其原理套用于资本市场法制与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当法律的滞后性妨碍到市场创新的根本性问题,进而危及到市场主体的利益,造成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时,就会有暗流从地下出现,进行规避性的产品或制度性创新。尽管这类创新游离于法制的范畴外,但却可能是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因此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并在市场上引发广泛的示范效应。当此类创新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就成为突破地表的熔浆和野火,推动法制顺应时势,作出相应的变革,正所谓“势易时移,变法宜矣”。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二次会议期间,有多达230位的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和建议,要求修订《证券法》。
两法修改实施后的金融创新法制环境评估
两法颁布后,许多市场人士乐观地认为,两法能够直接促进金融创新的发展,私募、多层次市场、T+0、做市商、衍生品种、混业经营等金融创新全面推开的日子指日可待。实际上,从既往的经验及中国的实际出发,仅仅依靠基本法律的力量不足以实现根本性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需要众多法制因素的配合。完备科学的基本法律能够为金融创新预留空间,但要实现将法律提供的空间转化为现实的自主创新实践和资本市场生产力,还必须满足若干法制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括:
法制权威性。确立法制权威性是法治的根本,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法律在整个资本市场调整机制和资本市场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市场主体的行为均须以法律为依据。在崇尚实利的资本市场中,往往有“法律实用主义”、“法制工具化”甚至“法律无用论”、“法律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如果不在法制框架下进行金融创新,则可能所谓的金融创新会步入歧途,甚至列入非法的范畴。在两法颁布之后,许多预留空间的领域都施予了限制性条件,如国务院的批准、认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批准等等,这些都亟待相关配套法规规章的出台,在游戏规则未明确之前,仓促入场的金融创新可能面临返工或被清除出场的风险。
法制整合力。证券监管法律体系是我国专业领域内规范数量最多、体系最庞杂、层次最复杂的部门法律体系之一。据保守估计,除去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和证监会内部规章外,就有320余件有效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中有些规范功能区划不明确,内容安排不合理;有些规范形式不合法,体例不统一;有些规范效力层次低,权威性不足;有些规范废、改、立不及时,信息披露不透明;有些规范制定程序存在瑕疵等等。证券监管配套法制数量繁多、体系紊乱、逻辑松散的缺陷,严重阻碍了相关金融创新的发展,加大了市场主体对规则认知的难度,如果不对现有规则的内容进行有效的全面梳理和重构,将在基本法律层面下形成“次级法律黑洞”,抵消基本法律对金融创新的积极意义。
法制执行力。法谚云:“徒法不足以自行。”仅仅有两法的基本框架,并不足以赋予两法足够的实际执行力。所幸两法在明确其执行机关的基础上,赋予了执行机关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的手段及保障。例如,在《证券法》中新增加了监管机构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财产权登记、通讯记录、工商登记资料、户籍资料等权力;增加了对银行账户的查询、冻结和查封权;完善了对公开发行的监管和对非法发行的查处权;增加了对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证券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延伸监管和查处权等等。在执法环节,如何加强执法力度,完善执法程序,合理区分金融创新和证券违规经营,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监管机构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客观来说,两法的确赋予执法机关尤其是证券监管机构较为强大的监管和执法权,但与其面临的监管责任和任务比起来,这些职权如何落实为具体的执行力,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法制公信力。在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资本市场,如何重树证券法制的公信力,增强市场主体的守法意识,是一个需要各方面共同协调努力的课题。在处理义与利、法与情、理与事的诸多矛盾中,需要以法制的权威性和统一适用性一以贯之。法制公信力的提升不仅有赖于对合法金融创新的扶持与法律保障,而且也必须依靠对非法行为的打击和制裁。只有扶正祛邪,扬善除恶,才能在市场上树立和弘扬合法创新、守法经营的观念,将金融创新与非法证券经营相区别,将金融创新纳入法制的轨道中。
法制创新力。马克思说过,“法制作为经济生活的记载,总是植根于一定的经济生活而又落后于变化的经济生活。”尽管两法的颁布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基本法律相对于资本市场经济现实的滞后性,但证券市场仍有许多领域的法律和制度需要更新和创制。金融创新需要法制创新作为先导,否则许多领域的创新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例如,在衍生品领域,迫切需要国务院对股指期货、权证等衍生品的明确界定;在发行领域,需要公开发行的具体规则和私募的具体规定;在交易领域,需要明确多层次市场的构成,明确公开发行但不上市股票的转让问题;在业务行为领域,需要对融资融券、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等作出规则指引;在违法违规查处方面,需要制定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的具体认定标准,并对非法证券发行交易、短线交易、违法信息披露等结合两法的新规定作出实施细则等等。
总体而言,两法的颁布为证券市场的金融创新打开了空间,提供了宽松的法制环境,但法制的嬗变需要法制权威性、法制整合力、法制公信力、法制执行力、法制创新力等众多因素的配套提升,这一过程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立法、执法和自律机构任重而道远。反馈到金融创新领域,也意味着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是伴随着法制变革的渐进式进程,要遵循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复论证,深入推进,任何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功近利的思想和实践都是不现实的。
完善证券法制体系,发展金融创新,改善金融生态
自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金融生态”这一命题后,加强金融生态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已经成为金融理论界及各方关注的热点议题。“金融生态”范畴是对金融业的一种拟生化概括,充分概括了金融像生物一样的有机本质,体现了金融业的“生命性”、“竞争性”和“自适性”的生态特征。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证券业也同样面临生存、发展、竞争、自适等金融生态的一些共性问题。金融创新和法制环境是衡量金融生态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报告》认为,法律和治理是金融生态建设的核心,金融创新是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和生命性的源泉。两法中有50余处明确授权国务院或证监会制定具体的规则或细则,这为重构证券法律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两法颁布实施后宽松的政策环境,也为完善立法,加强执法,提升资本市场法治程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鉴于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和系统工程,要作的工作很多,以鼓励和促进金融创新,改良证券业金融生态为出发点,应科学规划,分出轻重缓急的改革层次。笔者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应做好如下一些工作。
证券业立法框架及目录的制定工作。两法授权的职能部门应深入研究需要规范的主体、业务、行为和程序等事项,形成一个指导未来立法工作的规划,初步划定所需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性规则等规则的目录,勾画证券法律体系的框架和骨干,确定其调整范围和内容分工,前瞻性地对所需调整的创新事项进行研究,收集相关领域的境内外立法资料,增强立法工作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尽量避免以往的无的放矢或应急性被动立法情况的发生。
过时规范的清理工作。两法授权的职能部门应对现有的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等进行逐件逐条的清理,列出失效文件或条款,尤其应加紧清理那些对金融创新构成实质性障碍且与两法规定不相符合的法律规范。
创新性规范的立法工作。两法存在大量的授权性立法条款,现实中存在的大量金融创新也需要立法规范。创新性规范的立法进程有两种选择:理想的方式是在两法开始实施时,按照立法规划,整体系统地推出创新性法律规则,但在数量多、时间短、人员少、工作量大的情况下,要求职能部门在短期内全部实现授权立法项目有较大难度;现实的方式是分批整合,按照创新的紧急和难易程度,逐步推出,优先制定、修改现实需要紧迫的规则和创新实践比较成熟的规则。
现行有效规范的整合工作。根据资本市场的监管实践,对既存有效的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编纂,通过“废、改、立”和“合并同类项”的方式,整合若干同一类型或同一方面的内容,制定分门别类的专门规范体系,以整饬市场反映较大的监管法规体系繁杂、缺乏逻辑性和可预见性的问题。在大类的设计上,可按发行管理、上市公司管理、证券公司管理、交易市场管理、证券服务机构管理、境外上市管理、未上市公众公司及多层次市场管理、行政行为规范等体系来进行。
改进立法方法,增加立法透明度。在立法调研或具体立法过程中,应通过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或者网络、报刊等媒介,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利益取向不同的各类市场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将“内部通知”、“备忘录”等透明度不高的规范内容,吸纳到公开的立法活动中。通过这些措施,既增加了立法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也使立法的透明度大为提高,增加了社会对证券立法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执行力。
科学界分各类法律形式的调整范围。法律层次分为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自律性规则等内容,其中问题较大的是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界分。对于那些具有相对稳定性,属于对市场和监管对象进行实质性规范,需要全体市场参与者及广大投资者知悉的,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够反复适用的内容,应以正式的行政规章的方式制定;对于那些在监管部门体系内划分工作权限、提出
工作要求、布置具体任务或者属于探索、试点阶段,缺乏稳定性的内容,应以一般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制定;对于不具有强制性的指引性、建议性、倡导性的内容,主要应由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的自律规则加以规范。
事后动态检查和反馈机制。在金融创新试点试行过程中,应给予市场主体“试错” 的机会,在规章规则的起草制定过程中,应针对亟待规范的创新试点颁布暂行或试行规则,并建立事后动态检查、评估和反馈制度,对于试点成功的情况,应及时总结经验,制定更为完善、更为正式的规则;试点失败,应及时果断废止相关规则,结束试点,不应在未作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盲目移植一些缺乏实践基础的境外做法,或推出风险不可控制、结果难以预测的所谓“创新”制度。-
作者单位: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