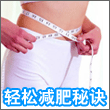|
|
李肃:通货膨胀全景新解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04日 16:11 新浪财经
通货膨胀全景新解: “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与我国当前的改革与发展 今年1月中旬,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播放了吴敬琏与厉以宁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同台谈话,让人回想起许多当年亲历的改革往事,特别是那场颇为闻名的“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这也引起我对20多年来三次宏观调控的反思,推动我重新研究两位大师的宏观经济思想、微观企业理论与中观产业认识。我认为,在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通货膨胀之时,揭示这场争论的本质内涵,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20年前的“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是一场不同改革思路与不同发展政策之争。这一争论涉及到改革的前提条件、改革的手段方式和改革的基本目标,并时起时伏,延续至今。 20年前,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处于十分关键的十字路口。当时的经济背景,与今天有同有异。最大的不同点在于那是一个短缺时代,而相同之处则是同处于物价抬头的通货膨胀期。 1988年,中国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性制度设计。即:企业原有的计划内产品按计划价格,新增产的计划外产品可以按市场供求灵活定价。由此而来,“寻租空间”急剧增加,导致日趋猖獗的“官倒现象”。为了加速价格并轨,1988年制定出价格闯关的改革方案,结果引发了抢购风潮与通货膨胀。针对当时改革的难题,“吴市场”与“厉股份”之间的理论之争全面展开。 1988年底,我在北京社科院经济所当副所长,并与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世界经济导报》共同成立了一家体制改革研究咨询中心,并就“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召开过两次研讨会,会后,我给《理论信息报》写了一篇文章,概括这场理论争论的本质,其主要观点有三。 第一,在改革前提条件上,“吴市场”关注市场环境建设-价格改革,“厉股份”重视市场基础再造——所有制改革。 在吴敬莲看来,价格信号是市场竞争的前提,也是传统国有企业展开市场竞争的基础。吴老认为,价格双轨制已使我国出现了严重的市场扭曲,不做根本调整,微观体制改革也将无从着手。因此,价格改革与市场环境再造是重中之重。在厉以宁看来,双轨价格也有价格,也在刺激企业市场竞争。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国有体制下的企业承包制没有造就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从而分割封闭了有限的生产要素,使其无法按市场供求变化自由流动。因此,应唯传统企业的股份制再造唯大,市场环境建设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制改革。 第二,在改革的手段方法上,“吴市场”主张国家强力干预,力主用政府手段紧缩经济和抑制需求达到供需平衡,扫除价格改革的最大隐患——通货膨胀;而“厉股份”认为通过股份制改造市场主体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以此达到短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效率的全面提升,才是供求平衡的最终解决之道。 如何解决双轨制难题?是这场争论的焦点。吴敬莲认为若要避免价格放开后的轮番涨价与通货膨胀,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调控手段,紧缩、紧缩、再紧缩,把过热的投资与需求拉下来,形成较为宽松均衡的经济(市场)环境,然后再放开价格,解决双轨制问题。而厉以宁与之相反,认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靠发展来解决供给不足。厉老认为股份制改革才是从根本上改造经济环境的关键,靠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产权制度,使资源要素在各产业和各企业间自由流动,以利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加有效供给,最终达到相对的供求平衡。因此,所有制改革才是市场不断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的制度保证。反之,刚从计划经济中脱胎出来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不仅不利于改革,而且不利于发展。 第三,在改革的最终目标上,“吴市场”主张靠经济紧缩淘汰无效企业的“水落石出论”,“厉股份” 则主张靠经济高速发展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的“水涨船高论”。 吴敬琏的价格改革以市场环境建设为首要目标,认为紧缩经济和淘汰劣势企业避不可免。因为,只有经济冷却的市场环境,才能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在正确的价格信号下平等竞争并“水落石出”。即,通过经济紧缩的压力实现优胜劣汰,由此形成有序竞争的经济环境,在此条件下对优胜的企业进行改制。厉以宁的所有制改革以经济高速发展为前提,他更关注短缺条件下的经济结构调整,认为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资金资源的高效流动,不可能在经济衰退中实现。因此,牺牲发展速度换来的价格改革,与短缺时代的发展目标相悖。 1993年以后,吴老与厉老又发生过两次理论交锋,我虽然忙于管理咨询与投资银行实务而远离理论界,但却十分关注他们的争论。一次是2001年的中国股市之争,另一次是2004年的重化工业发展之争。两次争论我都是厉老的支持者。最近,两位大师的央视谈话,则是对30年改革得失做出的全面评价。在我看来,这三场争论都是“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的延伸。 2001年吴老与厉老的股市之争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股市到底是投机者的博弈场,还是资源配置的交易场?──这仍然是当年“改革前提条件”之争的变奏。吴老强调股市的市场环境,反对股市投机。这一观点至今是“股市过热论”的理论基础,代表着对当前股市打压和抑制的倾向。厉老关注股市的主体再造,更关注要素在股市的流动配置。在他看来,虽然历史上股市曾经是国企脱困的机器,也因大批国有控股公司的衰退而成为庄家操控重组的乐园,但是,这都是股市发展的表象。今天,股权分置结束后形成的“市值时代”,已经把股市变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与企业分化重组的主要渠道,这是几代股民不断努力的结果,离不开股市发展的历史。因此,新兴国家的股市只能积极引导,不能消极打压。 2004年的重化工业之争局限于较小的理论圈,但其现实意义至今尚存。重化工业应成为宏观调控中政策倾斜与扶植的对象,还是被视为过时过热过剩的产业受到投资限制,这不仅仅是对该产业本身看法上的分歧,也是改革手段与改革目标之争的延续。厉老认为,在我国成为全球消费性产品的制造业基地之后,能源资源全球性的持续涨价显然是一次我国重化工业进军全球的绝好机会,新一轮的重化业投资不仅不会象吴老所警告的那样,造成我国的能源危机和环境破坏,而恰恰会因后发优势的新投资,不断增加供给解决短缺危机,并形成能耗与成本明显更低、经济效率明显更高、技术与品质也明显更好的全球产业竞争力。从最近一次的央视谈话看,厉老认为重化工业未来发展的真正障碍,在于能源资源和重化工业领域的国家垄断过于强大,所有制改革还有回潮。由此造成民营资本向重化工业的合理流动备受限制,从而错失全球性发展的重大机遇。将厉老视为宏观调控的反对者无疑是一大误解,恰恰是他最先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精辟概括。厉以宁所反对的,是在短缺领域中消极性地打压经济发展。他主张政府要在全球竞争的视野上而不是在国内视野的井底里制定产业政策,引导资本和其他要素向重点支柱产业流动,以此提升我国产业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007年1月,两位大师的同台谈话,围绕30年改革得失的评判。表面看来,谈话的直接冲突不烈,但其涉及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则事关未来改革的大局,需要全面解读。 在改革成绩总结上,厉以宁旗帜鲜明地以所有制改革为轴心,认为承包制解放了中国农民的生产力,为制造业向乡镇转移积累了资金并输送了1.8亿农民劳动力;股份制改变了我国企业配置资源的方式,迎来了股市大潮下的“市值时代”;民营企业已经发展成势,对整个经济发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这三类市场主体的再造,是30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不可忽视,也不能逆转,更不能损害。但在所有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上,厉老认为这一成就还局限在竞争性行业,垄断领域不仅没改,还有倒退。对厉老的上述判断,吴老的质疑十分明确,他仍然以市场环境建设为主线,关注三十年来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历史,关心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提高。 在改革不足的评价上,厉以宁除了批评大国企的垄断之外,另外批评了我国经济政策长期以来存在的两点偏失。第一,厉老认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够高和结构调整力度不够大,导致城乡二元经济没有彻底改观,国内市场内需远没有激发出来。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不是过快过热了,而是远没有发展到位,还必须加快。其潜台词,是厉老对吴老“紧缩,紧缩,再紧缩”主张的再次批评。第二,厉老认为中国不仅要靠相对较高的发展速度来解决民生问题,而且要用更多的政府财力搞好福利、医疗和教育。但30年来的经济发展政策有误,八十年代的紧缩经济政策造成了政府的贫困,九十年代的紧缩政策与经济衰退迫使政府加大基建投资引导内需,造成政府该做的社会福利等工作没做,社会责任的欠帐过多。 在改革前景的预期上,厉老的希望有三:一是希望靠经济高速发展而不是紧缩衰退,来加大国家福利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二是希望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以便不仅具有自主创新力,还能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三是希望每个公民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地位相一致,成为有信用的社会成员。与厉老的最大不同,是吴老更关注政府职能的转变。 总之,围绕30年改革得失的评论,吴老与厉老二十年前的理论争论仍在继续。 二 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影响了我国20年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吴敬琏的价格改革思想一直是几届政府宏观调控的指导方针,有得有失。厉以宁的所有制改革主张始终是几代企业家追求的制度境界,有进有退。 1986年,我在北大讲演时得到厉老的第一次教诲,他是我从政府机关走入理论界的启蒙老师。80年代,我不仅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所有制改革派,而且一直请厉以宁出任我们体制改革研究咨询中心的顾问。厉老对我思想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吴老,则是一位我一直心存歉意的长者和大师。1988年在长春召开的全国承包制研讨会上,我把价格改革的障碍归罪于承包制体制,认为企业承包制的推广导致商品定价权全面下放,并因每个企业的自我封闭而难以进行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供给结构的调整,由此形成企业轮番涨价和通货膨胀的局面。针对此症下药,只有推进股份制改革,打破承包制格局,开启并加速资源向短缺产业领域的流动配置,并借此增加生产供给来解决价格上涨问题。在那次会上,吴老请刘纪鹏找我,让我参与他主持的微观经济体制研究。我在与吴老的交流中深感其大家风范和学识深厚。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我与吴老开始合作之时,理论信息报记者将我过去的一篇采访谈话发表出来,文章在全面评价厉以宁与吴敬琏的理论思想时有些偏激倾向,全面否定价格改革为主的改革思路,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些许不甚恭敬之辞,并非都是我的原意。20年来,我始终对吴老心存歉意。 时隔多年,我们超越当年的个人关系来客观评价两种理论,评判两种改革思路对我国经济走向的影响,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结论。应该说,吴老的价格改革思想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极深,历届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针多源于此道,且有得有失。厉老的所有制改革思想对中国微观经济的影响极大,几代企业家的发展目标源于此理,亦有进有退。 除了目前正在展开之中的这次宏观调控外,30年来我国大规模宏观调控先后两次,第一次是80年代末的治理整顿,第二次是90年代中全面紧缩。 第一次宏观调控的经济背景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 1978年到1986年,农村承包制的全面推广,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城乡间的流通开始搞活。而后,承包制进入城市,从国有企业到地方政府全面展开。放权让利的承包制给全社会增加了巨大活力,也刺激了市场需求的急剧膨胀,计划时代普遍性的商品短缺矛盾更为突出。这时的“通货膨胀”因价格管制而以“价格双轨制”的形式体现,价格“寻租空间”高达GDP的20%。大量的行政权力渗透其间,全民皆“商”和大肆贩卖批文的“官倒现象”一度猖獗泛滥,严重扰乱国家经济秩序。 吴敬琏的“价格改革方案”由此出台。他认为价格之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因而该方案被形象地称之为“价格闯关”。但是,消息一出,短缺经济的供求结构与“价格闯关”心理恐慌结合,导致了1988年的价格暴涨。从1981到1984年物价指数每年只涨2%,但1985年猛涨了11.9%,之后虽稍有回落,但1988年很快又攀上20.7%的高峰,当1988年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后,抢购风潮闻风而至,到8月份更是演变为涉及到绝大部分消费品的全面抢购潮,价格闯关被迫中止。 伴随价格闯关的失败,吴老价格改革理论逐渐趋于成熟。即:用紧缩手段平衡供求,在市场平衡后放开价格,靠充分竞争的失常淘汰劣势企业,而后再展开企业制度改革。为此,从1988年开始,我国政府推行了长达3年多的“治理整顿”,中国改革史上第一次宏观调控应运而生。这是一次全面紧缩型的调控,政府采取了吴敬琏的政策主张,并在治理通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果,不仅刹住了投资增长过快和需求增长过快的风潮,而且使价格双轨制因供求平衡而趋于消失。客观地讲,吴老的宏观调控思想和调控方式,对八十年代末的两界政府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但是,这次紧缩同样也有极大的负面影响,称得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大有“泼脏水倒孩子”之嫌。其突出问题有如下几点。 其一,清理整顿公司,明显打击了中国社会已经成长起来的市场活力。当年确有不少并无真实性业务、仅靠权力钻营生存的公司。但是,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去强制关闭市场主体,恰恰压制了正在觉醒的体制外活力。到1990年底,全国撤并各类公司达10万多家,占原有公司总数的35.2%,其中既包括行政权力性的“翻牌公司”,也包括各种类型的市场化公司。整顿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将经济活动“回归”到传统的经济主体结构,这无疑与改革开放的方向严重背离,并使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步伐大大减慢。 以我们当年的经历为例,1988年我正在给团中央策划设立中国华青总公司,组织一亿共青团员投资集股,设立一家拥有全国分支的企业集团,组织新一代人才提前进入商业社会,为我国经济的超速发展助力。当时的团中央组织部长徐永光和团中央书记刘其葆为此踌躇满志,志在必得,为共青团组织的重大经济转型而激动。但是,不久开始的清理整顿公司,使我们的宏大计划梦断襁褓。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奥秘在于“体制外突破”,体制外经济力量的出现和成长,以其“鲶鱼效应”,激活和带动了国有体制的转型,也由此促进了整个经济的高速发展。民间活力的强大与雄厚,市场经济“体制外发展”的人民战争,正是中国奇迹的核心所在。而当年的清理整顿公司,却有着明显的反体制改革倾向,欲将经济发展格局重新纳入旧体制的范围,以达到对经济整体的可控性目的。 其二,全面性地抑制投资、紧缩信贷,使1990年到1991年出现相当明显的经济萧条与生产衰退。与传统中“不患寡、患不均”的思维定势相类似,我们在宏观调控中一直把通胀的威胁置于萧条的威胁之上,从来没有认识到:与通胀对民生的破坏性相比,经济全面萧条的破坏性显然更大。 我们至今经常在讲扩大内需市场与缩小城乡差别,吴老与厉老对此的看法高度一致。而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农村承包制涌现的大批万元户与流通领域出现的全民经商,强烈刺激着城市职工工资的上涨,由此产生了超强的市场内需。我曾经在农村插队十年,对农民的收入变化十分敏感。记得1987年,我们给联想公司当顾问挣了八千元咨询费,轰动人均工资不到百元的社科院。我当时调侃地告诉同事们:比起我插队乡下的农民,还有漫长的路要追赶。如今看来,如果我们当时更多地重视厉老的资源配置理论,用所有制改革来刺激供给,我国经济一定会循着供求良性上升的轨迹持续发展,并从内需拉动的高速度正常发展转入内外互动的超常规发展。 其三,治理整顿的调控政策助长了反改革思潮。由于第一次宏观调控手段较多行政色彩,也由于其他负面影响,在经济中反改革的倾向有所上升。当时,国内发生了改革方向的严重分歧,“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之争也变得日益严峻,“左”的思想也明显反弹。 1988年,我们为股份制试点企业“小飞乐”设计配股方案,并通过柜台交易完成了上海“老八股”的第一例二次融资。但是,到了1989年,治理整顿与清查结合,开始清算我们的所有制改革,说这是渐进式私有化,是盲目集资投资,是偷税漏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许多企业家为改革而受到政治迫害。1989年4月,我们刚帮助福州二化厂长苏乃熙—最早向中央呼吁给企业松绑的第一代改革家完成股份制改造的方案设计,他就被捕入狱,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我始终认为,当年所有制改革难以实施,很大程度上是旧意识形态作崇。在很多人眼里,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制度”,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第一次宏观调控的确解决了双轨制价格带来的严重问题,但其代价相当沉重。不仅使GDP增长过慢(最高时只有4%),而且抑制了改革开放时期的财富积累和需求增长,打击了短缺经济时代的发展扩张力,并把所有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一股脑打入冷宫,使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大大延后。 第二次宏观调控的背景是1993年的经济急剧升温。 1991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犹如一把时代之火,点燃了新一轮改革的燎原火势,再次激发起整个民族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活力。从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199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7800亿,增长44。4%,1993年又增51%,达到11829亿。各地招商引资奇热,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超过6000个,占地达1.5万平方公里。正是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导致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8.2%,建材供求矛盾尤为突出,上涨50%以上。1993年,零售物价在小城市上涨13%,大城市高达25%。于是,5年前的“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再起争端。 全面体制改革派认为:应该把海南封关开放,甚至可以让台湾参与共制;应该利用经济高速发展推国企改革,卖光优质国企;应该加速金融改革,加快放开股市;等等。因此,借助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全面解决所有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与此对应,规范市场秩序派认为:经济过热已成大敌,海南房地产投机已不能容忍;开发区占地已危及粮食安全;通货膨胀将造成社会动荡;全社会的集资热潮必定形成骗钱成风;等等。因此,全面紧缩经济是规范市场秩序的必然选择。这时,我国经济理论界不仅有吴老的深刻影响,而且他的众多弟子直接进入了宏观决策层,加上国际上的学者和世界银行的专家纷纷助战,由价格改革思想衍生迩来的规范市场秩序派渐成主流。1993年中,尝试过治理整顿和紧缩经济效果的中国政府,按照自己天然的思维惯性,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紧缩经济的宏观调控。 以1993年中出台的《十六条》为标志,这场紧缩性调控以严格控制货币发行、严厉纠正违章拆借资金、严肃压缩信贷总规模、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等为主要内容全面展开。面对局部性过热,政府按“吴市场”五年前的药方抓药。全面紧缩、收紧银根、控制投资、严控税收。1993年7月,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领导人要求各大银行当反腐败一样来推进全面收贷工作,足见其行政铁腕式调控的力度。 这些紧缩调控措施的成绩无庸置疑。短短三年的时间,高达20%以上的通胀率被压到6%左右,很大程度上理顺了经济环境。紧缩调控的同时,中国还相应完成了财税体制、银行体制、投资体制与外贸体制的全局性的改革改造。1997年,猛烈冲击东亚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金融危机,也由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而使我国能够安然地置身事外,未受波及。 与此同时,吴老在八十年代力主的“水落石出论”,在九十年代开始灵验了。1994年,经济紧缩给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政府开始用各种方法帮助国企脱困。但是,在紧缩调控和衰退潮中,“有意栽花、无心插柳”,用尽气力去改造、去扶植、去提升的旧体制力量(即国有企业)死多生少、起色不大。但是,在“体制外”的乡村民企,却凭空生长出数量庞大、生命力蓬勃的制造业大军,让当局、也让大多数理论人士始料不及。曾经实力雄厚、不可一世的城市竞争性行业国企在短短几年中就迅速衰败,代之而起的是广东的、特别是江浙的大量乡间民企,以及众多的合资外企,形成中国经济大地上蕴然成潮“产业大换血”现象。以最为典型的纺织业为例,一刀切的压锭限产,本来是一种打击投资过热、压缩过剩产能和扶助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措施。但是,这一政策没有帮助纺织国企脱困,反而将城市国有企业的4600万锭产能逼入困境,并最终几乎全军覆灭。与此同时,在此短短数年中,我国纺织业民企在乡村新生,重新投资再生了8000万以上的的民营产能,实现了纺织产业从城市国有向农村民营的战略转移,也奠定了我国低成本纺织业称霸世界的产业格局。 但是,不可否认,第二次宏观紧缩调控也确有负面效应,它给我国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尚存。 首先,在持续两年多的海南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以及股市热之中,迅速生长起一批城市化、知识化的财富阶层。与80年代中后期的官倒式“倒爷”相比,他们在视野上、操作能力上和财富创造力上都有质的提高。其中,许多人并不满足于原始积累的初期暴富,已经开始利用手中的财富收购改造当时的一些优质国有企业,进行重组、上市,并进行产业调整。但是,由于紧缩政策过激,绝大多数“下海人”的财富在此次严厉紧缩中灰飞烟灭。 其次,由于对海南热、房地产热和投资过热的紧缩处理过急过严,我国银行的损失高达5万亿以上,迫使国家本应投入社会福利的大量资金用于弥补坏帐。当时,如采取更为开放更具胆识的策略,对海南实行境外主体式的“封关”处理,将其变为国际化的海岛特区,不仅海南极其全国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烂尾楼和空置房,银行的大多数坏帐可以避免,而且,海南的发展也将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由于打压消费、抑制需求,导致了明显的经济衰退,中国大中城市的一大批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在那个时期成批成片地消亡衰败,导致建国后30年中在竞争性行业中辛辛苦苦积累形成的国有存量资本,近乎丧失殆尽。由此带来的遍及全国的城市工人下岗潮,也无疑引发相当广泛持久的不安定与不稳定隐患。1995年起,中国陷入长达五年多的通缩困境,促使政府不得不以特殊手段给政策、救国企。在此期间,我们采取国企加速上市、重点放贷、债转股等等手段“脱困”。这些看似是“厉股份”所有制改革的措施,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往往流于变相的“输血”脱困,难以形成企业自身的“造血”功能,效果自然不佳。因此,这次调控而来的“水落石出”,是以牺牲城市国有工业和一代企业家为代价的。如果从1993年开始,我们仅仅适度控制通胀,全面促进国企改制,鼓励金融资本与企业家联手推MBO,城市制造业的转移会更平稳,原有产业的技术人才、市场人才、管理人才和金融人才的流失与浪费不会如此严重。 第四,有人说,九十年代的产业大转移是天大的好事,乡村民企发育出的低成本制造业脱颖而出,中国由此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但是,这一现象确有双刃效果。因为,由于多年紧缩经济导致内需严重不畅,新生的民营轻工消费品产业只能舍国内就国外,以低成本战略拼命挤入国际低端市场,最终产生出一直延续至今、积重难返的“外贸依存度过高”之弊。其次,由于技术人才、市场人才、管理人才和金融人才的空白起步,新生产业往往起点不高,在产业链的低端多年徘徊,粗加工、低薄利的帽子极难摘掉。另外,由于制造产业在农村再生,劳动力进入工业的成本奇低,一亿八千万农民毫无控制地流入城市,已经构成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巨大难题。最后,还有一点值得关注,这些新兴企业大多是家族管理起家,直到最近两年才开始重视职业化和股份化,融入上市增殖融资的大潮,晚了整整十年。 第五,1997年前后,紧缩导致通缩问题发生,为了启动经济,政府又大量投资搞“拉动内需”,搞基础建设,甚至直接进行大规模产业投资。其效益成败姑且不论,却导致政府干了许多不该干的事、花了许多不该花的钱。而该干、该花的却无力去干、无钱去花。这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致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失业及其他必要社会保障工程体系上欠帐过多,至今难补。如果当年经济降温和缓,如果银行烂帐较少,如果优质国企全面出让,如果金融改革能够加快,我们的政府必然会去承担最该承担的责任。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今天,吴老与厉老两位大师对福利欠帐的看法已殊途同归。 总之,在第二次大规模宏观调控中,“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争”的深刻影响,在新形势下再度显现。吴敬琏思想在第二次宏观调控中的政府政策层面得到充分实施,有得有失;而厉以宁的所有制改革思路,却在民间自发无序快速发展,有进有退。 新浪声明:本版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 新浪财经吧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