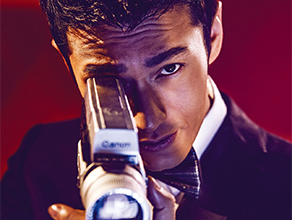康复医疗的发展路径
凌锋
772
2016-05-30
151
凌锋
推动中国康复医学的发展是我们医生的一个梦。我当了40多年的外科医生,开刀无数,见到的创伤无数,有在车祸中严重受伤的,有撞成严重残疾的,也有缺胳膊少腿的,也遇到过病人原来状况不错,但是因为疾病做完手术后变成残疾的……所有这一切,我都曾见过。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个人的残疾,有一些我能够帮助病人治好,但是更多时候我是在救命,而不是在治疗残疾,大家都应该体会到救命和治残是两个概念。
不光是救“命”,还要“命”活得好
“人”不仅应该活着,还得活的好,生活的有质量。如果一个人因疾病、外伤导致生活质量骤然下降,或者因为衰老等自然规律导致他的生活品质下降,那作为一个生命的体验会觉得不快乐,这是一直以来、时刻在撞击我心头的痛。医生有责任帮助他们,让他们尽可能感到生命的快乐,尽可能让病人恢复到一个能够回归社会生活、回归家庭,回归正常生活的状态。
我曾经有一个门诊病人。她受了外伤,她的家人倾尽所有,要求医生无论如何要把她救活。结果医生救活了她,但是落下了严重的残疾,而且得了严重的外伤性精神障碍。
回家后,病人在家里成天摔东西打人,她的两个姐姐都辞了工作在家里伺候她,但是她发病的时候把姐姐的头发一把一把抓下来。家里没有一件完整的器皿,全被她砸光了。
她的两个姐姐带着她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十分悲哀地问我,“凌教授,你还有没有办法治疗?早知道她会这样,我们当初何必要倾家荡产救她。”
这句话、这个病人一直到今天都很揪我的心。我虽然治病无数,但是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救“命”以后,是不是能让这个“命”活得更好?
“海若”启示
我一直坚守一个原则,就是在我做手术的过程中,特别仔细的保护脑的任何一份组织,避免损伤脑和脊髓的任何部分,就是希望病人手术后不能有症状的加重和功能的损伤,但是即便是这样,也仍然很难保证完全没有损伤,毕竟是“火中取栗”,是在脑或者脊髓组织中间把病变拿出来。
病变就像一个豆腐里包着的一个丸子,要把丸子从豆腐里拿出来,没有办法不把豆腐切开就能把丸子拿出来,这个过程对神经组织必然有损伤,我做再多的努力,有的时候也是不可逾越现实技术的。
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病人在被损伤的情况下获得比较好的康复?我治疗过的病人海若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是给了我什么名声,而是给了我很多启发。
第一个启发是,人的生命和功能多数是可以重塑的,她给了我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过去,我们公立医院做完手术以后,因为受到平均住院日的影响,病人刚拆完线最多十一天、十二天就要出院了,至于他以后恢复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有办法告诉医生恢复的状况,这是好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很少;大多数病人出院后就杳无音讯了。病人将来会怎么样医生无从得知。但是刘海若因为各种原因,我们看着她在我们眼皮底下康复了一年半,从一个昏迷的病人到能够自己走,自己生活,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都在继续好转。这是她让我看到的生命重塑的过程。
第二个启发是,从哲学的角度,治疗一个病人毕竟要靠整体的理念,要尊重病人本身的自洽能力来保证他全面的康复和全面的康复过程。从康复的角度,刘海若使我充分认识到“康复对一个病残者来说是一条新的出路”。即使我们外科医生做得再好再认真,也不能保持万无一失,因为还有外伤还有其它的损伤,还有不得已的损伤,那么我们只有求助于“康复”。康复是让病人获得很好生活质量的另外一条康庄大道,这个国外有很多现成的经验和可借鉴的发展历程。
重症早期康复介入的价值
海若是受伤五天后,我赶到伦敦会诊,一个月后带她回到北京。上午运到北京,下午开始讨论,康复科的王茂斌教授也参加会诊。第二天王教授带着人就开始给海若进行康复治疗,所以在重危病人早期急性期进行康复是特别重要的。
越早期做康复越好,肌力慢慢恢复,张力也被克服了。可是很多康复医院没有办法来接收这样早期的病人,就因为没办法稳定住病人的生命体征,病人气管切开,鼻饲营养,插着尿管,意识不清,内环境不稳定,这样的情况哪个康复医院敢接?早期的病人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康复,等康复的时候“木已成舟”,很多功能就不回来了。
所以,我要建的康复医院,不仅是所有的康复方法全部要具备,更重要的是要包括重症,重症是一个掌握维持生命的重要岗位,需要很高的技术。这些技术和能力如果能够把病人的命给稳住,同时我们所有的康复手段都能及时用上,对病人真的很好。
我们最近有一个病人,是从某三甲医院转过来的,脑干出血昏迷一直住在ICU(重症监护室),所有康复医院都不敢接收。病人有气管切开,还不断在发烧,但是我们这里可以接收,我们有重症监护室,有呼吸机,有整个一套班子,有医生护士24小时强化处置。病人到我们这儿醒了,我们可带呼吸机直接进入高压氧舱,在舱内既可以吸氧也可以吸痰,在重症的状态下可以执行我们对他所实施的所有治疗,包括中医针灸等都可以直接上监护室做。到现在是50天,病人醒了。
我们国家残疾人有八千多万,各种原因导致的残疾,有先天,有创伤,有手术伤害等等。其实这八千多万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早期是可以通过康复减少残疾的程度,恢复一些能力,使他变的更好的。
但是我们很多病人、医生,对康复的认知还不到位,认为手术回来就慢慢养,包括在我们宣武医院,我查房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我们的病人都躺在床上输液,其实有大部分是不需要躺的,50%是不需要输液的,但是病人自己觉得开了刀就得躺着,病人家属也说好好躺着休息,医生也会说好好休息、慢慢恢复,他恰恰是忘记了最重要的概念——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康复。
我们努力推康复的价值的时候,真的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复讲,就这还未必能深入人心。
康复是什么?康复是科学指导下的运动。只有科学指导的运动才能够恢复生命的活力。而我们恰恰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和宣传,总觉得躺着自然就能恢复,就好像有苗不愁长一样,撒在地里苗长就是了,其实不是,不浇水施肥,那苗长的就不怎么样,就不好好结果实,任何一个生命是需要维护的,同样的道理,人也一样,生命需要维护,这个维护也包括康复。
观念、人才的国际差异
从康复手段上来看,国外康复的手段和方式,我们北大医疗康复医院都有,而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因为国外没有中医、藏医,高压氧等。国外有一个比我们好的是,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很发达,比如支辅具、义肢、机器人支配的支具等等,都比我们好。
骨科手术完了必须加上康复才更好。在国外,基本上手术后第二天就开始康复。我们的心脏病人,从来都是手术完了以后卧床不动至少一个月,这种概念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
但是国外的病人,第二天开始下床,第三天开始洗澡,护士会帮助病人,然后要进行训练,一个星期病人就回家了,正常生活。而我们这里还是大车拉小车推回去躺的平平的。
国外差不多是一家综合医院配有一家或者两家康复医院,这样才能使病人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训练,而且康复的病人完全是被医疗保险覆盖的。上次统计,我国现在有3000多所康复医院,而综合医院两万所,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医疗单位是九万。如果按一比一算,至少需要两万所康复医院,才能让综合医院的病人有一个很好的康复去处,有一个很好的恢复过程,现在的差距还是很大。
此外,康复医学人才匮乏,很限制康复的发展。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医科大学有康复系,也不是到处都有康复医院,因为人才的供需关系是互相联系的。需方越多,刺激着供方不断的发展,就像现在缺儿科医生了,就开始使劲加快儿科医生培养,其实这样有些无奈,因为医生的培养哪能拔苗助长,其实最重要的是未雨绸缪,事先把培训放在前面。
从教育系统看,国外比我们的教育水准要好很多,因为国外的康复人才来自两个渠道——医生是从医学院毕业的,理疗师专门有理工学院,里面有专门的康复专业。实际上,国外的学术跨界非常多,医学中间有很多理工科,理工科中间有很多医学,所以康复师和医生所掌握的知识宽度要比我们现在的多。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有一些急功近利,就想一竿子插到一个尖上,其实底子很薄,基地很窄,这就限制了整个康复医学的发展。因为我们底子很薄,国家没有一个专门的理工学院建康复科的,所有的康复都是在医学院,医学院建一个康复系,而这个康复系还是大专最多,或者本科,硕士博士比较少。这个层面我们比国外差几十年。
值得高兴的是,在“十三五”规划中,专门指出要建设中国的康复大学,这是在残疾人事业中间残联提出的。未来从医学+理工,共同结合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或者为中国康复培养人才的大学指日可待。
我们也可以跨界,在这所专门的大学里,医科、理工科、工科都可以互相融汇,将来会有更多的医生和康复师为老百姓服务。
我的康复医学心愿
康复科在公立医院占的份额很少,康复所需的设备、条件也非常不全备,可能存在很多这样的窘况,有PT(物理治疗)OT(作业治疗);ST(语言治疗)的科室;可能没有认知治疗,而神经系统很多方面是靠认知的训练;有认知治疗没有心理治疗,有OT、PT、ST的不见得都有高压氧;有高压氧的未必有中医;有中医的未必有ICU……没有一个医院的康复科是所有的治疗手段都很全的。
当病人需要的时候,包括海若,不得已满北京到处走;到处请中医、针灸、心理医生,同时在认知治疗方面,还专门飞到英国,在英国进行了半年认知训练,还专门到香港进行了水疗。
海若所经历的这些所有事情,我在想,这些都是对病人有帮助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医院,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地方有齐全的设备和治疗所需条件,那病人怎么办?我们的病人为了求得某一种治疗,得坐着飞机到不同的地方寻求。
我们为病人服务的宗旨是什么?应该是所有的技术都要围绕着病人转,而不是病人满世界找医生、寻方法。
从海若获得很好康复之后的这两年,我就开始萌发要建一个康复医院的想法。
我想,我一定要建一个按照我的理想,按照我认为病人所需求的所有的治疗方法都能让他在一个医院里全面实现。这样所有的人都围绕着病人转,病人就安逸了,病人的就医体验就好了,病人就能够获得最好的治疗。
当一个病人能获得最好治疗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医生最大的快乐。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梦。我跟中枢神经系统打了一辈子交道,我特别想知道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以后是怎么恢复的?恢复的途径是什么?是原位对接了还是绕道而行了,还是从别的地方伸出援手了?这些现在很难说我们已经全都搞清楚了,我们不知道它是走什么途径,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价这种恢复的途径。
现在,我们在功能核磁共振中,可以找到这些不同的信号,可以通过不同的序列表现出大脑和脑电图互相之间的联系,以及大脑信号的传递和功能的表述。比如,我在说话的途中做磁共振,可以看到管说话那个地方的脑子在发亮,假如我在唱歌,管唱歌的地方在发亮,和说话的不是同一个地方……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功能,互相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联系的途径如果损伤了用什么办法,用什么样的途径去连接,就好比像我们的公路,G7如果堵了,我们可以从G6绕过来还是从下面的辅路过,总得找到一个道,那么这个“道”在什么地方?
磁共振、脑电图、脑干诱发电位、肌电图等等这一切电的设备和磁共振的设备都是帮我们揭开脑功能恢复的神秘面纱。我希望了解这些,进而找到这些康复的途径,找到各种康复的手段,了解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能让病人恢复,哪种康复更好,比如是针灸更好、按摩更好,还是用哪种手段好……这样我们可以设计不同的组别,用这种客观的指标来判断病人恢复的过程。
揭开这层神秘面纱,让大脑在我们面前逐渐透明,想起来我就非常兴奋,干起来乐此不疲!我的梦就是这样:了解大脑,为病人找到更好康复的途径,让病人获得更好的康复。
链接
凌锋,女,主任医师、首席
专家,专业特长:将手术
和介入手段综合应用在脑与脊髓血管病的治疗上,尤其在脊柱脊髓血管畸形的诊断治疗领域做出了系统性、创造性贡献,至今累积治疗1500余例,为世界最大病例组,使该疾病的治愈好转率从原来的46-63%提高到82.2%,获得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国内率先全面开展手术和介入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建立了颈动脉支架成形术、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脑动脉支架成形术、颅内外动脉搭桥术的综合团队,目前每年治疗相关疾病500余例,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和中华医学科技奖。
进入【新浪财经股吧】讨论
责任编辑:支全明 SF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