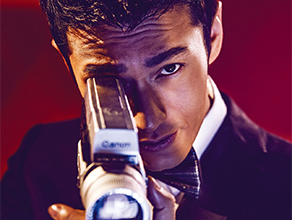6亿中产从何而来
771
2016-05-23
148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有多大。去年瑞士信贷宣称,根据美国的标准,中国有1.09亿中产阶级,随后马云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有3亿中产,他预期未来十五年中国将有5亿人成为中产阶级。这个数字也可能保守,一些学者预期,到2020年,中国中产人群规模会达到6亿。
即使考虑到各自不同的研究框架和参照系,这些数据也可能没法做严谨的比较。所以很多人吐槽他们只是“被中产”。不过人们之所以如此热衷地预测和讨论与此相关的数据,很大意义上是因为,这对未来中国意义重大。从普通创业者到商业大佬,几乎都迫不及待地竖起为中产服务的大旗,将中产当作核心目标人群。
这并非毫无来由。不管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确正在诞生一个日渐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他们意味着更加旺盛的需求和强劲的购买力——商务部数据称,2015年中国人境外消费1.2万亿元,从马桶盖、电饭煲到品牌繁多的奢侈品,乃至各类美容和医疗健康消费,这一海外消费大军中的主力即是中产人群。
这是一个体量庞大的人群,有时候他们被看作是非理性的——这可能让他们更受欢迎。海外购物的数据证明,他们有强劲的消费能力,但是国内现有的商业体系无法满足他们,所以马云说,我们的钱可能是中产阶级了,但是我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依旧是初等阶级。
就此而言,当我们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差不多是在问,提供什么样的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让中产人群心甘情愿地花钱?当我们谈论中国经济从投资推动到消费主导时,几乎是将中产的崛起当作了假定前提。但是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无限商机时,也许忽视了最重要的问题:这6亿——也可能是3亿或5亿的中产人群,他们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如何成为最有实力的消费者,进而如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成熟社会的“稳定器”。
这正是决策层关心的问题。5月1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前者近期多次被中央层级会议专项研究,而后者系十八大后乃至党的历史上首次被中央层级会议专项研究,如果说这是战略级的考量,也许并不为过。
我们理解,如果将小康社会大致看做一个中产社会,不管以怎样的收入标准划分,客观上不仅要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还要让百姓分享经济成长的红利。也就是说,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在此过程中,粗放的资源消耗型的的发展方式无法延续,实现新旧引擎的切换就成为关键。从这个角度看,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放在一个会议上讨论自有其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决于创业创富潜能能否尽情涌流,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企业和企业家。所以会议提出,发挥好企业家作用,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并要求加强对各类产权的有效保护。
历史地看,传统经济引擎的升级换代和新引擎的成长,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新经济在向作为消费者的中产人群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持续不断地“生产”着新的中等收入群体。反之,一个经济停滞创新乏力的社会不会培育出新中产,还可能失去曾经拥有。这正是多年以前大前研一曾描述的日本,在那里,收入阶层的分布往低收入和高收入上下两级移动,最终迈向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型社会”。
也许不用纠结于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是看得见的大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在讨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时,会议还提出“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这或许是因为“安全感”和“获得感”几乎同等重要。分好蛋糕可以保证人们的“获得感”,“安全感”则意味着让中等收入群体在这片土地上有尊严的生活。
进入【新浪财经股吧】讨论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