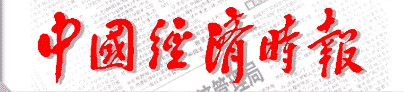不支持Flash
|
|
|
|
编选的理由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7日 08:56 中国经济时报
■闵良臣 北京的一家《青年周末》刊出一则报道,说是北京高中语文课本换血,除了将金庸的《雪山飞狐》替掉了鲁迅的《阿Q正传》,另外还作了一些篇幅的调整,因而闹出不小的动静。 其实,换,是正常的,不换,倒非正常了。别的作者不说,就是鲁迅在世,也未必就希望他的文字一直占据在教科书中。而况且不说鲁迅作那些文字时是绝没有想到将来要上教科书的,甚至一再希望他的文字“速灭”。八十余年前他在《写在〈坟〉后面》就说:“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换不换,换上什么,又替掉什么,而是那几个编委对他们的这种换自我感觉良好,总觉得他们不论替掉的或是换上的都是应该的。这就让人觉得有几句话想说。 我当然知道,这些编委们即使不能算是“各学科的带头人”,也都是在自己的专业上“有两把刷子”,即这编委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得了,或说谁想做就会让你做的。 不过,只要承认,是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好恶,编委们也不可能例外的话,就应该想到不论替换掉的还是新换上的——特别是新换上的——都是这几个编委的“意思”。我敢说,随便再挑几位别的编委过来,不论是替掉什么还是换上什么,肯定与这几位编委的有所不同。 我们先来看看为何要换上金庸的《雪山飞狐》,或说这《雪山飞狐》是如何替换上的。报道中这么讲:“《雪山飞狐》进入这次北京版的高中语文课本,并非偶然。”为何“并非偶然”呢?原来“编委中有不少金庸迷,62岁的薛川东说自己就爱读武侠”。我们从这篇报道中看得出,薛川东不是一般的编委,而是很有点“核心”的味道。既然这教材编委的“核心”就是一个金庸迷,在所编的教材中上一篇金庸的作品,岂不是“小菜一碟”。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编委中还并非一个“金庸迷”,而是“有不少”,“编委之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是个知名的‘金迷’,曾多处举办关于金庸的讲座,出版过《笑书神侠》等金庸研究著作。他做客人民网时,曾提到金庸塑造了不少‘相当高明’的中国人形象——既有韦小宝,也有康熙;既有张无忌,也有张三丰”;这还不算。“这次把金庸武侠小说推上教材的,不是孔庆东,而是67岁的北京版语文教材主编顾德希。”报道中“薛川东笑着这样介绍:‘顾老师可是金庸的“粉丝”。’”读到这里,对于上这篇《雪山飞狐》,你还有什么话说?顾老师的年纪并不重要,是不是金庸的“粉丝”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北京版语文教材主编”,是“北京四中的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有了这些,“顾德希亲自推荐了《雪山飞狐》中的这一段”,才能“最后被确定下来”。 这本武侠小说好不好,在下没看,不便置喙。既然“编委中有不少金庸迷”,这让我相信,这本书确实能吸引一些人,或说肯定有不少人很喜欢;然而我也确切地知道,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也有不少人不喜欢,甚至很厌恶。这从一些网友的跟帖中是能看得出的。比如一位叫“007”的网友就是这样说的:“金庸是无法和鲁迅相提并论的,鲁迅是一根针,专刺人最痛的地方,他让人们在堕落地活着的时候还不至于绝望;金庸更多的是像在一些腐败的僵尸身上套上一身华丽的官服,在满足自己幻想的同时也让很多人自我麻醉、自我满足。”这种评语对不对,要看他说的是否事实。如果是,那么,在当下这个社会,我们是需要金庸还是更需要鲁迅,也就不言而喻了。至于像文化学者傅国涌先生所说的“金庸作品进教材,至少传递出多元的信号”,并且这是“几位在中学一线教语文的朋友”在“简单讨论过这个问题”时“几乎一致”的意见,那就只能另当别论了。 此外,此次北京高中语文课本换血,还选入了《红灯记》、《杨门女将》等京剧选段,而“过去的经典戏剧作品《雷雨》,则在这套教材中消失了”。 为何要让《雷雨》消失呢?报道中语焉不详,大约“正如该教材编委薛川东所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教材;教材的变化,往往折射着时代的变化”吧。 至于为何要换上“京剧选段”,“薛川东说:‘我们觉得,京剧作为国粹,也该受到学生的关注。的确是语文该承担的事情太多了。刚好这两篇也写得比较好,很不容易。’”但我想,就因为是“国粹”,就是选进教科书的理由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中国的“国粹”多了去啦!一些,或说也不知我们有多少所谓的“国粹”也正在走向死亡甚至灭绝,我们又如何去抢救?这且不说,让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国粹”是否“也该受到学生的关注”,或说关注它又有什么意义。 据知,中国传统戏剧艺术,是歌、舞、剧三者的结合体。从周秦时期的“优伶”、到汉代的“百戏”、再到元代的“杂剧”,几千年来发展至今,形成了中国戏剧的众多传统剧种。然“发展”到今天,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在全国能叫得响的不是很多,也就那么十几二十个。我注意到,2001年11月下旬,在南宁落下帷幕的第七届中国戏剧节上,也只展演了36出剧目,涵盖的也只有22个剧种。这二三百种也好,这十几二十个也罢,说句不太客气的话,都是在作“垂死挣扎”。我们现在是拼命努力想把一些剧种保留下来,“发展”下去。然却事与愿违。 自己曾在1992年《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戏剧不易改良》中引用我国戏剧研究专家徐城北先生举的例子,说是一个京剧团原本想去外地演出赚一笔,不想后来连回程的路费也没挣着。后来,央视《东方之子》节目采访评剧艺术家、后改行演小品且名满全国现已去世的赵丽蓉,问他对当前戏剧的现状有什么看法,这位艺术家咂了咂嘴:“我琢磨戏剧还是要改。”至于如何改,她至死也没说——想也说不出。从央视《东方之子》2000年10月17日播出的节目中看到采访中国京剧院院长吴江,这位院长也认为:“京剧如跟不上时代发展,不合社会潮流,完了就完了呗。”张中行先生在他的《文言和白话》一书中讲“变文”时有这样一小节话:“夸张,繁复,绘影绘声,多不合实际,都是变文的旧传统。近年来有些人注意这类通俗作品,有的人并且多方搜集,编为目录。但究竟爱读的人不多,所以没有辑本或选本出版。”还有梁实秋先生在《听戏》这篇文章中更是反对喊改良戏剧:“我只知道一种艺术形式过了若干年便老了衰了死了,另外滋生一个新芽,却没料到一种艺术于成熟衰老之后还可以改良。”并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又补充说:“我常想,我们中国的戏剧就像毛笔字一样,提倡者自提倡,大势所趋,怕很难挽回昔日的光荣。”为什么呢?“时势异也!”几年前,北京举办中国京剧票友大赛,笔者关注不多,更没认真观看,只是从“午间30分”的节目中知道,好像参加者年纪最小的只有四岁,年长的近八十岁,很是热闹了一小段时间;与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那阵子的热闹劲儿差不多,真是大有再次掀起京戏热潮之势。然而到底如何,看看“200周年纪念”之后,就不难得出答案。殷鉴毕竟不远。此外,我还有篇《传统戏剧的前途》,发表在当时的《太原日报》上,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 中国的京剧,谁都不能说不好。不好,还能叫“国粹”吗?可好倒是好,我却早就觉得:它们“至多是保留在博物馆里,陈列在那儿,供后来的人们神往和怀念。我认为,戏剧一旦达到‘非常完美的境地’,也就老了,或说也就离‘死’不远了。”即使成了国粹,说句该掌嘴的话,也还是“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这样说,也绝非是在诅咒戏剧。因为这是一种规律:‘完美’了,就不思改革,也很难改革。而不能改革,必然落后于时代,而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只要落后于时代,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用句老百姓的大实话,便是‘除死无大灾’”。 既如此,今天在教科书中换上这种“国粹”,怎么看,都不是“时代”的需要,也与“该教材编委薛川东所言”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教材;教材的变化,往往折射着时代的变化”不大吻合——我们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教科书上换上“京剧选段”也是“折射着时代的变化”吧;极而言之,我们要让那些孩子关注这样的“国粹”干什么?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