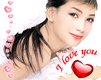|
卫西谛
《弓》是金基德第十二部作品,这对于一个1996年才拍摄自己处女作(《鳄鱼藏尸日记》)的导演,速度是令人吃惊的。据说《空房间》拍摄用了13天,而《弓》花了17天,这种速度同样令人吃惊。当我们看到金基德电影的完成片时,不得不承认这种速度来自他有一个足够简单的套路,一个足够有力的构思,和他对画面构成方面的直觉——这得益于他在法
国学习绘画的经验。在他2003年的转型作品《春夏秋冬又一春》的最后,金基德自己扮演了一位僧人,他用一组极长的镜头,描绘自己如何将一尊佛像放置在群山的巅峰,从而使自己获得了一个“俯瞰人世”的全知视角。实际上在他去年获得柏林和威尼斯最佳导演奖的《撒玛利亚女孩》和《空房间》中,我们看到他使用的就是这种“俯视的”悲悯态度,他渴望用一种东方式宽容的态度,为我们写赎罪的故事。《弓》大致延续了他的这一视角和态度。
《春夏秋冬又一春》之后,金基德开始从致实的象征主义隐喻——比如《漂流欲室》水草象征女性下体——转变为一种较为空灵的神秘主义手法——比如《春》中女子化为佛像、《空房间》里的隐身。我个人其实并不喜欢“神神道道”的电影,在看似有着多层涵义的符号道具和令人啧啧称奇的故事背后,并看不到真正的人。金基德的电影也有这样的令我感到不满足的地方。在他的电影里,我几乎没看到所谓的“边缘人群”或者“残酷人性”,这些在我看来只是他的画面和故事的装饰品,而不是他的主题。我们在他的电影中基本看不到人和社会的关系,所谓“边缘”是不成立的(这和李沧东的电影不一样);而人性的残酷也无缘由变成单纯的描绘。《弓》在这个方面的缺陷,更为突出。这部影片在我看来更像是他的“休闲小品”,从任何角度看都比较“单薄”。就最近这四部电影来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撒玛利亚女孩》——它有个实在的精神内核,而不是一个聪明想法包裹着的空洞。
《弓》基本没有讲述故事,只是讲述了两个人物——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女,围绕的核心是弓(箭)。弓(箭)在电影里有几种功能:作为武器,是老人和少女的语言,是抗拒外部世界和表达彼此情绪的工具;作为乐器,则完全是导演视听效果的需要;作为象征,是老人的阳物,在影片的最后,获得少女的处女之血。我在《弓》中,唯独看到的是一种状态——紧张。老人从头至尾,都恐惧来自外面的力量将少女夺走,直到死亡。按照金基德自己的话来说:“我希望自己直到死亡,都能活在一种紧绷的状态下,就像是一张弓。”在金基德的电影中,基本上是一个紧张的封闭世界,这是他作为导演私人的世界。《弓》更比较拒绝别人进入,所以这部影片除了唯美的视听效果之外,很难获得别的满足。《弓》更像是金基德的一次自我迷恋的产物。
金基德再次让他的主角闭上嘴巴,但他们既不是《漂流欲室》的哑巴,也不是《空房间》里面一对陌路情人。老人和少女在为他人算命之后,由少女告诉老人卦象,再由老人告诉顾客结果,这一过程有“耳语”的画面替代。显然并非他们没有说话,而是金基德不让观众听到。在保持神秘气氛和悬疑效果的同时,多少显得有些刻意。关于对白,金基德一方面认为“西方观众更能够接受我的电影,所以,我在影片中尽可能地减少对话,因为我担心错误的翻译会破坏我大部分的工作。哭和笑已经是最好的语言。”一方面他认为人类的语言不可信,只有行为是诚实的。但是必须指出在《弓》中,他的沉默没有显示应该有的力量——这部影片情绪的传达并未依靠人物的动作完成,只是通过男女主演的眼神来完成(顺便说一句,他们的表演是完全成功的)。
最后,毋庸置疑的是,《弓》的画面是漂亮的。有几度我都误以为银幕化作了画布,化作了海水——这是金基德热衷的场景。在这个水的平台上,金基德继续展示着他迷恋的小道具:船、鱼钩、随身听,而且更为频繁的借助于韩国传统文化的元素,用以装饰他的电影。但就在人们认为影片会在平淡中结束时,金基德用他拿手的“神异手法”让观众吃了一惊。金基德最近这几部影片都以虚实交替,现实与神秘的叠加完成他的作品。《春夏秋冬又一春》最后一章、《撒玛利亚女孩》最后的梦境、《空房间》最后的三人生活,以及《弓》最后的一支飞来的箭使少女到达高潮。也许,正是这画面的美感和故事的神秘性,构成了金基德电影之所以令人着迷的原因。《弓》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