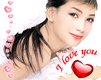向政策专家提问:领航下一阶段现代化提问实录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9月10日 14:03 新浪财经 | |||||||||
|
2005年中国企业高峰会于2005年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中国企业联合会与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举办。会议的主题是:“中国下一阶段现代化:制定科学与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下是向政策专家提问:领航下一阶段现代化会议提问实录: 提问:
前一阵子有人说中国对于公共的产业、卫生、教育进行了投资,我也同意你们刚才讲的,中国财政政策的下放会不会导致全国性的增加投资的政策?中央政府政策是否能够适当的在地方政府加以实行?对公共投资是否是一种限制? 樊纲: 我想中央和地方不同的职责分工和财政的责任方面总是有一个问题,目前所有的这些公共政策它的资金都是来自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两级的,这是一种通常的做法,所以一旦中央政府宣布要采取一项新的政策,首先要从中央的财政中拿出钱,说我们要把这些钱用于政策上,之后才会让地方政府进行额外的出资,基本上是这样的做法。从长期来讲,我们要改革,当然现在还处于不同的转型期,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我们有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的历史,现在开放了,怎么做?人们正在想办法用目前的方法处理这些问题。中央财力方面还不是太大,中央只占30%,每年增长幅度不是很大,主要还是地方。 余永定: 在很多年以来,中国都想从西方国家学习,建立小政府。现在中央支出可以达到30%,和欧洲、美国相比是比较低的,现在大部分人都问中国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支出。我有一个数据,卫生保健这一块,中央政府只占16%,美国44%,但美国并不是福利国家,其他的发达国家是70%,中国在这方面支出比例是比较低的,应该要增加。 樊纲: 但是我们只有人均1000美元的GDP,看总收入多少了,我们确实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增加比例,但增加太多的话。 余永定: 我也不是说增加太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比例是太低了。我觉得中国人基础设施缺乏也是带来很多的不便之处。 樊纲: 我也同意他的说法,中国比较不能跟美国、发达国家相比,就像拉美也不能跟发达国家相比。 余永定: 在140多个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可能排到,我们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 白重恩: 现在卫生支出4.2%,也就是公共和加上私人是4.2%。卫生保健完全由政府支出是不可行的,我也不反对在公共保健方面政府支出增加,也是可以的。比如在传染病研制方面,应该政府出资。但其他的卫生支出,比如车祸,这个医疗费用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掏。我认为模仿欧洲医疗保障体系在中国是不能够来应用的,卫生保健方面问题比较多,这些问题不光是来自于它资金的使用方式,理想的社会保健制度是德国的制度,它是由公共提供资金,但由私人部门提供医疗服务,政府出钱。中国正好相反,我们是私人出钱,公家看病。我们有很多行业存在进入的障碍,医疗服务由市场提供这一点还很难。 钱科雷: 和增长之间也有问题,不光是增加增长的数量,还有卫生保健病人接受的医疗质量怎么样,也是一个问题。他们可能支出比较高,但医疗服务却非常的低下。 白重恩: 在中国我们医疗服务质量确实不太好,可能是因为我们竞争不是很强,我在大学里面看病,我看病的时候可能会等3、4个小时,但看病只看2、3分钟。 樊纲: 我同意,政府必须增加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不管是公共提供还是私人提供,由于资源有限,定目标是可以提供的,因为可用的总资源不多,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特别是农村家庭,如果一个人得大病的话,可能要平行下去了,这种社会保障是需要的,你是要增加你的公共支出,但不能超越你总体的资源允许范围。不是服务质量本身,而是政策效率,也就是说你的钱要用在真正需要它的这部分人身上。 余永定: 是的,我们是经济学家,我们讨论问题都是推测,一半满一半空,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感到丢脸的就是你是社会主义,你要照顾所有的人,但所有的公共支出在公共这一块如此之低,增加支出是需要的,增加政府支出是一个信号,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会要求政府对公共卫生支出要增加。 提问: 暂且不要讨论农村的事,在城里讨论,城里的公共卫生提供的效率有多高? 余永定: 可以说是非常坏,我照顾我妈妈,我的看病经验非常的不好。 白重恩: 公共卫生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医院挣钱60%都是卖药,这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你想把看病和卖药分开的话,你可能会受到医院和制药厂很大的阻力,有些人一直想把它分开,但一直没有成功,现在还有人提出要把它们分开,给医院一个宽限期来做,我不知道这个宽限期是否要拖下去,有人说如果不卖药我们医院活不下去,这是可能的。 余永定: 我陪我妈妈看病,我问医生,医生让我挑四种药,我打电话问朋友,因为我不知道医院是否反映是它真实的情况。 提问: 现在允许私人对大学投资,此政策是否会继续发展?李教授。 李维森: 我刚从国外回来,这个事我不是很了解。 白重恩: 我来回答吧。有些领域外商投资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比如商学院,中国有中欧国际商学院,我的很多朋友都在那里工作,挣的钱比我还多,他们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赞助。因此,可以看出外商投资学校是可以的。但从无到有想打出自己的名声是很难的,我认为在几年内你投资可以把学校建成顶尖的是很难的。 钱科雷: 中国现在大学发展非常的快,我到一个小城镇看到了,他们正在准备在乡村里面建大学,好象雄心勃勃的。 白重恩: 有些是公营,有些是私营,像有些地方在吸引北京大学等大学建分学院,私人大学也在那地方发展,但可以说是比较低端。 钱科雷: 私人大学教育质量怎么样? 白重恩: 我还不清楚,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在过去十年中,高校领域政府支出增加比较快,某种程度来说增加太快了。另一方面,质量就下降了,因为只是增加招生人数,但并没有招聘高质量的教授,没有提高他们的质量。太多的放在大学,农村教育不够,这是一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更严重。农村的人现在还没有受到足够的找工作的教育,受过大学的教育的也不多。 钱科雷: 中国基础教育重点是什么?我刚从印度回来,跟那边相比较,中国在降低文盲率来讲是比较好的,印度在美国宣传好象说印度都有ID方面的文凭,好象给我们这样一个误区,印度文盲率是45%,是比较高的,接受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精英并不多,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基础教育是非常好的,但软件设计和研究方面,印度研究院做的比较好,中国是否能够在这方面赶上? 余永定: 中国大学,特别是清华和北大,不能再抱怨钱的问题,我完全同意樊纲的观点,不是钱的问题,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应该改善教育质量。我们要花更多的钱普及农村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人权,教育应该得到保证,这在《宪法》当中已经写出来了。 李维森: 我不同意余永定和樊纲的观点,我不认为大学的钱政府给的足够多了,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不是以积累知识为出发点的,我们的教授工资和北大、清华教授相比相差太大,北大、清华几百万呢,给我们设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如果所有大学都这样做,大学都像公司的话,怎么办教育? 钱科雷: 我想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想吸引全球的人才,我知道以前清华有一个教授现在在商学院教书,清华要给同样的钱他们才能来,但清华其他的老师肯定就得不到那么多钱了,因此人们不断的同教育部门讨论,看能不能就此进行一些纠正和调整。 白重恩: 在谈到教授工资方面,因为我是清华的,如果政府再给我们增加一点儿钱我也不会不高兴,但我同意余教授和樊纲教授的观点,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基础教育的问题,我刚才讲到政府不应该试图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收入差异的问题,这样可能适得其反。余教授刚才讲了,农村的孩子也是《宪法》赋予了他们权利,应该接受教育。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基础教育应该予以更多的重视,从长期来讲,要解决收入差异的根本办法,就是要解决农村孩子们的基本教育问题。但另一方面,我并不是说我们在清华就觉得百分之百就满意了,应该对第三产业更好的分配,并不是给第三产业投资更多。我觉得中国教育部不应该做的就是给我们寄太多的表格让我们填,去年我作为系的主任,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填来自教育部不同的表格,一份又一份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教师也要填不同的表,这样才能够得到政府的资助,不填表根本得不到政府的资助。 提问: 我想知道中国在公共事业部门改革部门面临什么挑战,比如要引进KPI等等,引进公共和私营共同的做法,你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做来改进中国的公共服务? 樊纲: 余教授在牛津读过书,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余永定: 虽然我在牛津读过书,但我在这方面也并不是专家。 提问: 97年布莱尔执政之后,重点放在教育方面。 余永定: 我觉得中国并不一定要借鉴这样的做法,这个做法对中国的意义并不大。我想英国大学面临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讲到大学,有一次系主任跟我说,你一定要给学生进行考试,否则他们就不来上课,那样我就会把你开除。 提问: 我的问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商学院他们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加拿大的商学院也不例外,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有关知识发展的问题,我想问在座的我一位同事,就是一个新中国大学知识创新的发展需要多长时间?这些想法在中国进行当中实现商业化需要多长的时间? 李维森: 其实我对这个也不太清楚,我想樊纲先生可能会回答这个问题。 樊纲: 你的问题意思是新知识创新,还是产业化? 提问: 就是对于过去10年当中对研发当中的投资,它是不是能够有什么产出?是不是能够实现商业化? 樊纲: 我觉得我们整个体制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现在人们也是非常愿意不断的发展,学校的研究机构和商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但目前的发展还处于初期,并且还有非常长远的道路要走。刚才讲到整个高等院校的体制,是国家控制的一种体制,这些学校的人以及市场上的知识商业化、产业化,以及学校的人力资源的管理等等,这些都是处于发展的初期,这是比较初步的一个状态。即使有的话,规模也不是很大,而且现在政府社会还处于学习的过程当中,学习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自己知识的创造。 钱科雷: 中国这些高校,以及中国的学术界,在全球的领域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些技术和知识人才的流动模式,我的说法可能不太对,我认为是中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樊纲: 仅仅是20%是中国的模式,80%都是外国公司创造的一些新的模式,所以中国这方面还是任重道远。 钱科雷: 中国同日本不一样,中国完全是自主在做这个工作,中国很多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外籍的教师,大家可以到清华和复旦去看一看,基本上都是靠自给自足来进行竞争的。 樊纲: 所以从长远来讲,跟日本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讲印度和中国的对比,我想讲几点,我想说对印度来讲,对印度的高等的研究英语的培训等等,他们这么做已经有1、200年的历史了,但对于中国来讲,才仅仅有20、30年这么长,所以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中国现在的水平还比较低,这方面即使同印度也不能相比,但中国的学习曲线是非常高的,在不断的上升和发展,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中国来讲,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充分的民主,但对于穷人来讲是更有好处的,当然中国教育体制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整个体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是不错的。再讲到就业、生产行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不像是印度,这些机会总是给精英人保留的,这是中印之间最大的区别。 钱科雷: 现在还有五分钟,我们可以再提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之前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刚才人们提到但没有深入讨论就是土地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经营日报》有一个朋友前几天写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的土地改革以及中国省份不同农民暴力性的抗议活动,有的时候政府就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从而自己获利,比如房地产,为了保护农民农用地不能被很轻易的用于商业目的,但有一些人很有权力,他们能够通过政府的官员达到让农民离开的目的,然后在桌子下进行一些交易。你刚才说土地对服务业是一个问题,从更广的角度来讲,中国要解决腐败以及收入差异的问题,但中国如何来处理土地使用和农用地的问题呢?要保护最大数量的农民使用土地的方式是什么? 余永定: 这个是在中国具有根本性,也是很有争议的问题。我读过一篇文章,他讲到在中国社会保障方面,对于农民方面这是他们福利保障的基本线,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这些方面持续出现一些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不能再持续进行土地的私有化了,原因是社会安全的问题。如果农民出售他们的土地,今后他们未来是没有任何保证的,这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目前为止一个办法就是,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努力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钱科雷: 也就是加强政策的执行,而不是增加新的政策? 樊纲: 我们现在正在制定一些政策,这些政策涉及使用土地的程序,以及对于失去土地农民的补偿标准的问题,有一些工作已经在进行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社会问题,但这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当然还有其他的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决策要考虑到的,我知道这方面的路很长,但一定会有一些规定,之前是没有任何规定的,以前在中国一个地方根本没有统一的规定,现在有了,我们把它叫做过渡。 白重恩: 我想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要冒昧的讲几句,这与地方公共融资有关。很多时候税收的权利都是归于中央政府的,因为地方政府对于税收收入有75%,但他们只能留30%,因此地方政府非常依赖于出售土地获得收入,因此出售土地占他们收入很大一部分,阻止地方政府迫使农民出售土地,我们应该进行财政政策的改革,这样地方政府就不会迫不得已这样做了。 提问: 我的问题有关宏观政策的,可能大家讲起来比较大,刚才讲的医疗、教育等问题,都是关系中国的经济的战略发展模式和管理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就此我的问题是中国的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它有此带来的能源等等急剧需求的增加,以及环境的破坏都产生了,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不能够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老路,我们也不能够学习北欧福利化国家的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资本,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需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另外要建立“和谐社会”“公正”等等,现在谈这些为时尚早,还有很多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平衡,到底是平等重要,还是效率重要呢? 白重恩: 讲到平等的问题,并不是平等和效率的权衡,还涉及目前的平等和未来平等的权衡,现在是要更多的平等还是今后需要更多的平等呢?我只想说现在过多强调平等会使效率丧失,也许会在未来带来不持续的平等,我们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观点,这样就能够有一个长期的平等,并不只着眼于目前问题的解决。 樊纲: 你说涉及资源的问题,比如商品市场和能源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任何国家都不能说它的能源资源是足够的,你如果在全球市场上工作的话,应用是全球的资源,你看日本并没有资源,但它也发展起来了,它应用是全球的资源。当然你要解决自己的效率和能源的问题,但并不能够避免所谓的能源或者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资源就不应该发展这些产业,如果不发展某一个特定产业的话,我们就无法有更多的就业岗位让那些剩余劳动力就业。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很多,包括占密集型产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市场上得到这些资源?比如说发生了战争,军事的手段将会阻碍我们得到这个资源,当然这不是1、200年之前了,我们是不是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得到这个资源,这是长期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政府这些政策、国家的战略是否真的能够允许中国的公司通过公平的交易能够得到这些资源,这是一个问题。 钱科雷: 我讲最后几句话,因为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回答这个问题,大家也有不少问题,但我想这些演讲的嘉宾都非常辛苦的,本场论坛到此结束。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滚动新闻 > 2005中国企业高峰会 > 正文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投资3万元年利100万! |
| 治口臭口腔溃疡新突破 |
| 高血压治疗上的飞跃! |
| 揭开牛仔淘金的秘密! |
| 名品折扣店聚财新模式 |
| 韩国儿童名品折扣店 |
| 50个好赚钱的精品项目 |
| 儿童EQ教育最新资讯! |
| 看盛唐茶庄如何赚钱? |
| 车价狂跌,钱狂赚! |
| 经营爱情,赚浪漫钱! |
| 拯救男人,还你健康! |
| 治疗高血压不花冤枉钱 |
| 新韩国快餐年赚百万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