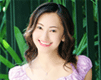樊纲:政府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缩小分配差距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8月30日 09:00 中国经济时报 | |||||||||
|
——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本报记者 柏晶伟 现在,人们不仅越来越关心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同时,在经济转型时期,人们对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公共政策越来
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发展阶段可能很长 中国经济时报: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一国贫富差距的程度,并将0.4作为警戒线。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说明我国收入差距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樊纲:在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不平等因素在加剧,收入差距在拉大,而且短期内看不到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根据我们最近的统计,基尼系数是0.44,有一些研究小组的数据超过0.5,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社会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虽然没有拉美国家高,但已经是非常高了。 中国刚刚进入一个收入差距扩大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一个社会不平等扩大的阶段。仔细研究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的这个阶段可能拉得很长。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这么说? 樊纲:因为我们有特殊情况。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是因为腐败,因为权利分配不公平。 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我们从一个农业社会向一个工业社会转型,过去占劳动力80%的是农业劳动力。在温饱实现以后,农业部门不再成为收入增长的源泉,人民的福利增长不再靠吃得更多,当靠非农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过去25年、26年的高增长,全国劳动力40%从农村转出来,还有40%的劳动力留在农村。按照规模讲,还有两、三亿的劳动力在农村。他们的收入不能增长,仍然是弱势群体。劳动力市场决定工资水平,只要有农民工的大量存在,就有扣发工资、停发工资问题。严格来说,只有到农民这一群人充分就业实现那一天,他们的工资水平才能逐步得到提高。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收入平等的一个转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在中国可能非常之长。因为我们人口规模太大。据说,中国将来人口不是16亿,而是14亿,一下子减去2亿,这是一个好消息。过去我们25年转移了2亿的劳动力,而在今后有可能需要30、40年的时间,再转移2亿的农村劳动力。你说,这个时间不够长吗? 缩小收入差距,关键是根除体制弊病 中国经济时报:按照您的研究,我们在发展的过程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不平等阶段。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会积攒更多的民怨?权利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是不是会更难解决? 樊纲:面临现实,需要我们寻找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学者、媒体、包括政府,要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理性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分析。情绪化分析,历史上很多,现在也很多。新的、难的问题是怎么在其他国家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在经历过这些平等和不平等,发展和不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中,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为我们这样一个大的难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中国经济时报:解决不平等难题的尺度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要求政府最大限度地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让老百姓的生活有基本保障。但是,现在显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比如,公共财政并没有真正实现为民所用。 樊纲:公共产品的确是一个好东西。它不仅带来社会的和谐,而且能实现我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对穷人,意味着有了更加平等和受惠的机会,使他们有一个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对富人,平等也是一个好东西,如果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得太大,社会的不满情绪太大,甚至出现社会紧张、社会动乱,这对于富人财富的增长、对于富人本身的财富也是一种坏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进行更理性更细致的分析。 怎么解决不平等的差距?现在一个大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政府做事情,要求政府提供这个那个保障,给这个那个钱,转移这个支付那个支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的。过去这20多年来,由于贫穷,由于我国25年才增长到人均1000美元的GDP,我们往往忽视基于经济增长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等事情,对弱势群体的需求和诉求有所忽视。加上没有一套完整机制,政府做的事情比较少,解决的问题也确实比较少。要增加政府要做的事情,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当中,有学者提到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型。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增加政府支出。政府确实需要做一些事情,现在确实是需要学习去补这个课,扭转不公平格局。 但是,我们要看到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仅仅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政府补贴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什么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我们的体制存在弊病。现在大家一说收入不平等,马上会转到对腐败和不公正的批判。这是对的,我们不平等是因为这些造成的。但是,不仅包括这些,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资源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很多不公平的收入当中,因为使用资源没有付费,反而成为企业的利润,这样的企业与没有占有资源的企业相比就产生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我们思考制度上的均等问题。改革制度不一定需要多花钱,我们要通过改革制度来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公正。 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就业创造,也无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樊纲:同时,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就业创造,就无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创造才是根本的东西。只要2亿农民还没有转移,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就根本解决不了。当然,这样的问题是很难通过政府补贴来解决的。收入差距是通过补贴来转移,但是很大的收入差距却是无法解决的。为什么发达国家有农民补贴﹖在发达国家,农民仅占20%,他们是用80%的非农人口补贴20%的农业人口。而我们现在则是要用20%的非农人口人去补贴80%的农业人口。仅仅以比较少的人去补贴比较多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来转移农业人口,通过农村人口的迁移等一系列措施来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仅仅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上,更要思考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增长问题。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落后的大国必须思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政府来讲也是一种挑战。而这个挑战又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如何在新的条件下,更多关注社会问题,解决该解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如何保持政府本身的职能和谐。 政府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解决均衡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怎样理解政府本身的职能和谐? 樊纲:我们首先要探讨一下和谐这个概念。在经济学意义上,和谐就是均衡。均衡是什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是由各种人群组成的。均衡就是从公共的角度来讲需要很多的公共品。这个时候政府的职能就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提供多种公共品。政府至少要做几件事情:为了经济的发展,建立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还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宏观经济稳定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财政不出现大规模的赤字。因为大规模的透支和赤字会使货币贬值,产生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使企业不能发展,就业不能创造,最后是使不平等的现象固定化。 政府还要搞社会保障。过去我们在收入保障方面关注得太少,所以才出现问题。但是,超越经济条件搞社会保障,一定也会出现问题,国外国内都会出现这类问题。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国家,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努力提高效率,并解决均衡问题,就必须集中有效的资源,去帮助社会最需要帮助的人群。 如何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比如,帮助农村得了大病的人,对他们实施医疗保障,以避免这部分人返贫。再如,人口、劳动力要转移就业,解决偏远地区农民的基本教育问题,使他们有资格出来打工,成为现代化的一分子。这些是政府集中财力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对一些弱势群体进行救助,比如灾荒的救助,恐怕是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把钱花到最需要的地方,使社会达到相对的平等。 政府在关心弱势群体的时候,也有一个和谐平衡的问题。在关心某一个弱势群体的时候,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弱势群体。比如,我们现在关注城市打工人员的收入状况和生活状况,他们确实是需要关注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把资源放在他们头上,解决他们的问题,也许会延缓另一部分不如他们的群体,即还没有进城打工的那2亿多农村人口。那2亿多人口都在我们讨论的视野之外。当然,进入城市这些人的问题需要解决,有关他们的利益仍然需要得到改善。这里需要有一种均衡和谐的观念来解决这个发展阶段的各种需求。 政府超出能力花钱,可能导致财政赤字 樊纲:我们既要关注社会差距的问题,要求政府多支出一点东西;又要注意经济条件的制约,政府如果花太多的钱,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就可能导致财政赤字。这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刚刚开始进入收入差距拉大的时期。在社会进入这个阶段后,社会紧张的诉求将会越来越大。我们学者的责任不是等事情发生以后才放“马后炮”,而应该在问题发生之前进行努力,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使这个社会真正稳定、持续、和谐地发展。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学人 > 正文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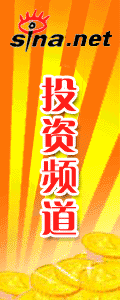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投资3万元年利100万! |
| 治口臭口腔溃疡新突破 |
| 高血压治疗上的飞跃! |
| 揭开牛仔淘金的秘密! |
| 名品服饰 一折供货 |
| 韩国儿童名品折扣店 |
| 50个好赚钱的精品项目 |
| 儿童EQ教育最新资讯! |
| 中国1000个赚钱好项目 |
| 房地产火爆 建材赚钱 |
| 经营爱情,赚浪漫钱! |
| 中华通典 惊世之作 |
| 治疗高血压不花冤枉钱 |
| 新韩国快餐年赚百万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