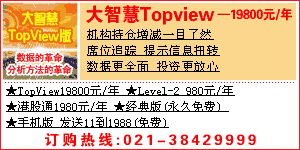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
三株:日不落帝国的崩塌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23日 06:16 招商周刊
三株:“日不落帝国”的崩塌 迄今为止,在中国食品饮料或保健品行业,可能还没有一家本土企业,能望当年三株之项背。 1994年8月,吴炳新、吴思伟父子在济南用30万元的注册资金、不到3年的时间,就撬起了一个80亿元的大市场,而其使用的杠杆,不过是盛着几十毫升“药水儿”的小瓶瓶。 就凭着“三株口服液”单一产品,山东三株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当年,销售额即达1.25亿元;次年猛跳至23亿元,第三年就达到了惊人的80亿元,三年累计上缴利税18亿元。 在全国所有大城市、省会城市、绝大多数地级市,三株近乎疯狂地注册了600个子公司,并在县、乡镇建立了2000多个办事处,其营销队伍更是达到史无前例的15万 人。 在一些城市,人们因买三株排起了长龙,二三十元一瓶的价格曾被哄抬至七八十元;在一些农村,农民们把买化肥、种子的钱都争先恐后地拿来买了“三株口服液”;“三株卖疯了”并不完全是其广告上的不实之辞。 实际上,吴氏父子祭起“三株口服液”大旗的时节,中国保健品市场正处在群体性萎缩、低迷期。新华社记者吴晓波曾引证说,在此前的七八年间,太阳神、娃哈哈、中华鳖精以及各种花粉、蜂蜜口服液掀起了第一轮保健品销售浪潮。然后,乐百氏的生命核能、巨人的脑黄金以及东北的沈阳飞龙等业已体味到了从鼎盛到衰落的跌宕。 可三株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下,俨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建立起了一个“日不落帝国”——吴炳新喊出如此口号时,豪情壮志无法掩饰,得意更是溢于言表。 遗憾的是,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是自然规律。吴可能压根也没想到,他苦心建立的貌似强大的“三株帝国”竟脆弱得不堪一击。 军事化市场营销 知情人士说,吴炳新其人几乎从不掩饰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拜。由于他56岁始创三株,属典型的“大器晚成”,为此,他甚至以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自比。 他大手一挥,将中国市场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南四大“战区”,四区分别设立“战区经理”,到了后期,他还建立了市场前线委员会(称之为“相当于国家军委”),在各省建立了市场指挥部(称之为“相当于前敌委员会”),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并进行战略转移,改打农村市场,然后“农村包围城市”。 在《吴炳新文集》中,他总结说,“我们将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于市场营销,我们还创造了一系列的战术,如迅速抢占市场的闪电战术;先打周边,锻炼队伍,取得经验后再打中心城市的战术;启动市场,广告宣传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人员使用上的‘扩大民兵预备役’战术等……” 布局既已完毕,“战争”全面打响,三株投下巨额的广告费用作为“重磅炸弹”对四大“战区”进行轰炸,似乎从不吝惜弹药。但其战术显得尤为巧妙,它不像秦池那样只在中央电视台黄金广告时段投放,而是“组合投放”,即在央视及一些中心城市电视台购买大量的非黄金时间的广告段位,用以播发拍得虽嫌粗糙但却充满了语言诱惑的三株系列形象片。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主题便是,“三株争当中国第一纳税人”和振兴民族工业。 一定程度上说,吴炳新的确具有战略家风范,且善出奇招。他利用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优势,开展人海战略,聘用了数以十万计的大学生充实到县级、乡镇级的办事处和宣传站,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搭建起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庞大网络。吴曾放言:“除了邮政网以外,在国内,我还不知道谁的网络比我大。” 与此同时,他还创出了一种“无成本广告模式”,即发给每个宣传站和村级宣传员一桶颜料和数张三株口服液的广告模板,要求他们把“三株口服液”刷在乡村每一个可以刷字的土墙、电线杆、道路护栏、牲口栏圈和茅厕上。以至于当时每一个到乡村的人都非常吃惊地发现,在中国大地每一个有人烟的角落,几乎都可以看到“三株口服液”的墙体广告,就像当年的陕北,处处都能见到“三项纪律八项注意”一样。 此外,三株还极为大胆且具有首创意义地走出了一条“让专家说话,请患者见证”的道路。三株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使用了“专家义诊”这种行销模式。在大中城市,每到周末,三株聘用的“白大褂们”就会走上街头义诊,其主旨当然还是推销三株口服液。再到后期,三株更把这股“专家义诊风”刮到了乡镇、农村。据不完全统计,在鼎盛时期,三株一年在全国各地起码要举办上万场这样的义诊咨询活动。 就在如此这般的“战略、战术”配合下,三株口服液,成了“包治百病”的“神水”。吴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这既是三株之大幸,又是三株之大不幸。 神话随一条生命一起终结 很快,这些造就了三株神话的“奇功异技”,其内含的种种毒素开始日渐集中地散发了出来。 先是“广东事件”。1995年5月,广东省卫生厅专门发出了《关于吊销三株口服液药品广告批准文号的通知》。该通知称,“济南三株保健品厂在《珠江经济信息报》上刊登的药品广告,超越了《药品广告审批表》审批的内容。”应该说,这是一份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宣判了三株口服液在广东省“死刑”的通知。尽管事后经过各方活动,三株口服液得以在广东继续销售,此事也未被媒体曝光放大。可是,即将来到的危机,此时迹象已显。尤其是,到了1997年,单上半年,三株公司就因“虚假广告”等原因而遭到起诉达10余起。 再是“成都事件”。三株成都市场部人员在编写宣传材料时,事先未征得患者同意,就把其作为典型病例进行大范围宣传,结果导致纠纷,并经新闻媒体曝光,敏感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也进行了报道,影响由成都一下子波及到了全国。 接着就是“常德事件”。1996年6月3日,湖南常德汉寿县的退休老船工陈伯顺听信了三株“有病治病、无病保健”的广告承诺,花428元买回了10瓶三株口服液。据陈家人介绍,患老年性尿频症的陈老汉服用了两瓶口服液后夜尿减少,饭量增多,但一停用又旧病复发;当服用到三至四瓶时,老汉出现了遍体红肿、全身瘙痒的症状,第八瓶服完,陈全身溃烂,流脓流水。6月23日,被送到汉寿县医院就诊,医院确诊为“三株药物高蛋白过敏症”。其后,陈病情不断反复,于9月3日后死亡。陈老汉死后,其妻子、儿女一纸诉状把三株告到了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年3月31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三株公司败诉的一审判决,要求三株向死者家属赔偿29.8万元。到此时,常德一案已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普遍关注。一审判决后,当即有20多家媒体进行了密集报道,其标题均为“八瓶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条老汉”。 这条爆炸性新闻,对于本已风雨飘摇的三株,无异于毁灭性一击。三株神话最终也随着这个陈老汉的生命一起终结。 从当年4月下旬开始,三株的全国销售急剧下滑,月销售额从数亿元,一下子跌到不足1000万元,从4月到7月全面亏损,生产三株口服液的两个工厂全面停产,6000名员工放假回家,口服液的库存积压达2400万瓶,相当市场价值7亿元。5月,就开始有传言说,三株已向有关方面申请破产,但因欠下巨额贷款,其申请最终未被批准。 记者注意到,有网络媒体提及,2006年3月,三株方面曾积极向国家工商总局申领直销牌照,意图借助直销模式“重建昔日辉煌”,但之后再没见下文;再后来就少有媒体继续关注三株。 想来,作为一个品牌的三株,已然淡出历史舞台,曾经梦想着把三株做成“百年老店”的吴氏父子,业已彻底游离出人们的视线之外。 记者注:本组文章借鉴了《南方周末》、《商界》、《大败局》等媒体和书籍的内容,在此一并致谢。 为何“其兴也勃, 其亡也忽”? 万杰、秦池、三株曾经的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或许,在今天再去反思它们的失误已没有多大意义,甚至还有些“事后诸葛”抑或是“马后炮”的意味。 但它们终究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对这些经典失败案例的反思与教训汲取,对于日后诸多企业避免重蹈类似的覆辙,应不无裨益。 资本运营宜选准领域 有些企业究竟为什么“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呢?青岛市委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程国有教授为记者分析说,企业的成功,无非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围绕着自己的主业或核心优势搞资本运营,并藉此不断获取新的优势,比如青岛啤酒,其只在啤酒生产与销售领域扩张,尽管由于扩张速度过快过猛,在一段时间里曾造成消化不良,但随着其无形资产的扩张,总体的发展还是继续向上;二是进入到有市场前景、市场正处在扩张期、可以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行业进行资本运营,也能取得成功;再就是进入暴利行业,比如早期进入房地产行业的那些企业都取得了成功。也就是说,能否选准领域和方向进行资本运营,是企业能否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 “其实,从万杰、秦池、三株这几个案例中并不难看出这一点。”程国有说,“比如万杰医院,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瞅准了高端医疗领域的市场前景,且这个市场正处于扩张期、能实现超常规发展,而且实际上还是个暴利行业,所以就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保健品行业仍是暴利行业,三株等企业即因此而风光无限;秦池白酒则通过大胆运作,在辉煌的几年中,通过白酒销售量的提升而使企业形象有了质的变化,也获得了成功。” 程国有认为,剖析这三个经典失败案例,有必要对“市场的变化”——这一重要问题重新认识。这是因为,市场环境、市场背景的变化,往往是企业进行资本运营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他进一步解释说,以秦池、三株为例,它们走向没落,其实都在1998年到2000年间,而其时恰是中国经济由通胀转向通缩的时期,百姓的购买力持续下降。换言之,市场环境、市场背景在当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加上这些企业的产品固化,不能及时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产品创新,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这也就直接引发了消费者的不信任——市场上普遍的购买力减弱与消费者对其产品的信任危机等多重因素相结合,最终就导致了其市场走向崩溃,进而失去了企业赖以生存的土壤,全面崩溃自然就在所难免。而万杰由盛转衰的直接诱因,实际上就在于钢铁行业市场环境的变化(国家政策面发生变化,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万杰居然对此熟视无睹,甚至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凭自己一己之力,可以与市场大势相抗衡,这就多少有点不自量力,其结果可想而知。 风险意识不可或缺 程国有教授的同事、同为青岛市委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的刘文俭教授则认为,这三个案例其实就提示出,企业必须时刻绷紧“风险弦”,他重点从企业周遭所潜藏的几大风险、如何规避这一角度谈了自己的观点。 刘文俭指出,概括说来,主要有七大风险。 第一个风险就是资金链风险,有些企业在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往往投资项目过多,而一旦政策面发生变化,碰上银行撤资,很可能一下子就会玩不转,资金链一旦断裂,很可能就带来灭顶之灾;第二就是货币政策风险,这往往直接就影响到企业的资金运作;第三是项目或产业风险,比如企业已经对某个产业进行了前期投资,可该产业本身就是高风险产业,企业如果对风险程度与自己的抗风险能力事先估计不足的话,风险甚至可能被放大;第四个风险是经营管理风险,有些企业已经患上了“大企业病”却不自知,对市场不能做到正确的把握、分析、预测,对市场变化也就表现出反应迟缓,很多大企业就因此倒闭。 三株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为了统一协调全国市场,三株总部设计了十多种报表,以便及时掌握各个环节的动态。但具体到一个基层办事处,可能没有那么多变化需要填,但上面要报,下面就造假。据说,在一次总结会上,吴炳新曾气愤地说:“现在有一种恶劣现象,临时工哄执行经理,执行经理哄经理,经理哄地区经理,最后哄到总部来了,吴炳杰(记者注:吴炳新的弟弟)到农村去看了看,结果气得中风了,他看到的实际情况跟向他汇报的根本是两回事,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不得了,尽哄人哪。”当三株发现了此苗头时,竟已回天无力。 第五个风险则是管理资源风险,有些企业老总,可能光觉得某个产业可能赚钱,却对自己企业的组织架构是否合理、人力资源是否充足等情况并不掌握,对所要投资的行业甚至谈不上了解,就盲目自信、匆忙决策,或是感觉自己实力很大,“应该没问题”,其实不然;第六个就是安全风险,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都是问题,有时出一个安全事件就可能让企业一蹶不振;第七个风险是结构风险,有些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对一把手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这就为非科学决策埋下了隐患。 那么,该如何应对这一系列风险呢?刘文俭的观点是:具体到企业方面,一是在经营方略上,应坚持“稳健经营”,做任何事情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量力而行,不能自我膨胀,妄图“蛇吞象”;二是要在企业内部形成科学决策的制度与氛围——多元化道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得走,但为避免拍脑袋决策失误,就必须注重科学决策;三是在跨入一个新行业之前,要对这个行业进行充分调研,对自己既有的资源充分了解,不能在资源、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心存侥幸,老是想着“东方不亮西方亮”,而应“亮了东方再亮西方”;四是要加强“营销价值链”的管理——“营销价值链”往往与“资金价值流”紧密相连;五是要注重资源整合,简言之,就是要知道哪些资源有用、哪些资源没用,该舍弃的舍弃,该保留的保留,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出自己的核心资源,以形成自己的核心优势;六是加强危机管理,企业有危机意识,要健全危机评测系统,决策层要知道危机可能在哪儿出现,从而及时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刘文俭看来,依当前的国情,对于企业的发展,政府理应从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其实就要求政府要积极发挥正面作用,比如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必须承担起来,而不能试图转嫁给企业。万杰的遭遇,很大程度上讲,当地政府是负有责任的——为了“稳定”,政府就让万杰背起钢铁厂的包袱,可此举不仅没能救活钢铁厂,反倒还累垮了万杰,实在谈不上明智;另外,政府应对大企业的危机信号保持高度敏感,该出手帮助时就要果断出手帮助,从而防止小危机演变成大危机,最终不可收拾,这也影响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咸鱼翻身”有无希望? 曾经的辉煌归于沉寂,难免令人感伤,设若咸鱼能够翻身,或多或少也能给予善良的人们一丝慰藉。问题是,它们还有“咸鱼翻身”的可能与希望吗? 刘文俭向记者坦言:几率极低,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轰然倒下又重新站起的史玉柱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但刘同时表示,首先可能得看原来的企业垮到了什么程度,是否还有剩余力量。如果重新选准主导、增长高的行业,找准关键项目与产业,集中剩余的优势资源,说不定还有希望。 “不过,这往往需要该企业实现脱胎换骨地转变,需要政府等外部力量的救赎。”刘文俭说,“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就曾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后国会通过了救助该公司的特别议案,银行贷款17亿美元为其输血,克莱斯勒的新一代经营者亦转变了经营思路,最终重获生机。” 刘文俭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在前头,这就是,企业必须找出破除“大企业病”的良方,首先解决因规模扩大造成的人员、机构臃肿以及由此产生的上欺下瞒、人浮于事的弊病,提高对一线市场的反应灵敏度。 他还以海尔对“大企业病”的成功疗法为例具体加以阐释:海尔独创的SBU战略,说穿了,就是使每个员工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业务单元,给予其行动的自由去实现其自己的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责。对企业而言,这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动车组”——海尔就不是靠张瑞敏一个火车头在拉,而是各个层面都在动,企业的治理结构也因此实现了扁平化、信息化,通过市场链“压扁”阻碍信息流动的层级式组织结构,让市场信息直接进入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如此一来,运转效率提高了,市场反应速度也相应提高了,企业的活力、竞争力亦因此得以体现出来。 刘文俭指出,“其实,许多企业坏就坏在这儿——摊子铺大了,机构庞杂了,系统传输速度变慢了,市场反应也就不灵敏了。如果想要‘咸鱼翻身’,这一问题不解决,是难以想象的。” 程国有教授则认为,对于曾经死过的品牌,想让它复活,简直难于上青天。他笑着打了个比方:这就跟明朝灭亡后有一些不满满人统治的汉人要“反清复明”的道理一样——对于反清者而言,“明朝”显然是“知名品牌”,但由于这个品牌美誉度已经严重不足,终使明朝这把“死灰”再也没有机会复燃。而三株、秦池等,因为曾经有“污点”以及原有团队的作鸟兽散,原有的品牌已经失去了它的市场意义,仅仅在口头上的广为人知并不足以成为其复苏的理由。 “当然,换个马甲再卷土重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比如史玉柱,弃‘巨人’、‘脑黄金’等原有品牌不用,‘脑白金’、‘黄金搭档’则让他笑到了最后。”程国有笑着补充。 □ 本刊记者 孙凤忠 跷跷板的两端 玩过跷跷板游戏的人都知道,在高速升起与疾速跌落的一刹那,均可直呼“刺激、过瘾”。 可经济生活中的跷跷板游戏,与此稍有差别。当高速升起时,那感觉确实叫“过瘾”;若疾速跌落,则恐怕只剩下神经上的饱受刺激。 得益于中国经济近30年的迅猛发展,中国企业群体性地具有了高速升起的先赋性条件。也正因为此,高歌猛进者的脸庞上曾一度写满了兴奋。 而如今,不少曾经“无限风光在险峰”的中国企业家正黯然品味着“辛辛苦苦七八年,一夜回到创业前”的尴尬。是否应怪“造化弄人”? 秦池、三株、万杰均曾创造了神话,如今神话又均已破灭,想来是充分体验了一把坐跷跷板的感觉。 其实,稍作延伸联想的话,中国企业自身即相当于一个“跷跷板”,而其扩张的速度与成长的稳定性,则是这个“跷跷板”的两端。有必要解释一下的是,之所以如此比喻而不是将企业说成放在地上的一根横木,是因为中国企业似乎总是只顾得上“扩张速度”这一端而忽略“成长稳定性”的另一端。这也就注定了其大起大落的命运。 为了速度,单单是为了速度,就将企业成长中必修的诸多功课能免即免,问题能拖就拖。一俊似能遮百丑,一叶障目从此不见冰山。追求速度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些致命风险?高速甚至是超速发展之后如何持久进而永续?可惜,这样的问题似乎从未列入其考虑的范畴,而不稳定的因素遂恣意滋生、肆意蔓延,以致不可收拾,终如触礁的泰坦尼克,无奈沉没。 对于高速扩张的企业而言,稳定性以及由此衍生的稳健运行法则,其实是一个自其产生以来便存在的永久性命题。当然,这是一个动态的命题,在不同的时空维度里,这个法则因时间而动,因空间而变。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中国经济当然不能例外。而中国经济最大的特殊,是所有的企业都处在一个巨大的转轨经济体中。转轨意味着诸多机会,企业因此而高速或超速成长;而转轨也同时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诸多风险,政策的调整足以使一个企业一夜暴富,亦足以使一个暴富的企业一朝猝死。 如此说来,把握政策风向标,是中国企业运行的生命底线和战略基本面;建立民主科学决策机制,并全面掌控战略资源链,则是企业在追求高速行进中避免因膨胀而导致翻车的良方;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组织架构实施“扁平化”改造,方有助于企业信息化渠道畅通无阻;而研究市场的态度认真与否,则关系到“乱投资病”究竟还有没有救——虽说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风险,但把鸡蛋放在一批破篮子里显然还不如放在一个结实的篮子里更为稳妥。 追求速度不是错,但忽略了稳定性这个跷跷板的另一端,就是大错特错。 值得一提的是,不愿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当然不是好的“企业公民”,但盲目担负社会责任者(万杰即为典型一例),似乎也谈不上“好公民”——把自己累垮了,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进一步说,自己垮掉后所遗留的社会责任,不还得由别人来担负么? 近30年来,中国企业“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一个个死去的“名企”虽未完全被人打入记忆的冷宫,但充其量不过是成为饭桌上的谈资,对后来者而言,“事情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与我何干?” 于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一拨又一拨小字辈的高速成长企业,重复着前辈们“昨天的故事”。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