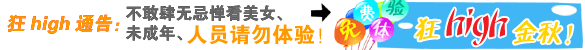|
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杨伯溆 博士生 李理
尽管播报新闻、传播信息的技术日新月异,娱乐文化的繁荣或者喧嚣依然是电视这一当代重要传媒的主旋律。浸淫于电视娱乐文化中的人类生存状态,早在拍摄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电视台风云》(Network)一片中就已被展现无遗:“电视一代”的情感被荧屏上的景象幻像化着,包括战争、谋杀在内的重大事件都被消解为荧幕上的娱乐元素。
然而,电视不是因为大众需要廉价的娱乐而诞生和扩散的。它的繁荣与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消费文化密切相关。工业化时代需要资本积累,因此社会意识形态提倡节俭。当社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尖锐。这就需要一个宣传商品并能够刺激物欲的平台。也就是说,市场需要培养这样的消费群体: 源于本能的自我在各种“解放”的理念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膨胀,受到自由话语体系包装的“个人主义”成为文化的主宰。然而,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无论是“自我”还是“个人主义”都必须纳入消费的轨道。这就需要操纵和控制。换句话说,所展示的“自我”必须是能和消费相关的自我,所崇尚的“个人主义”也必须是最后能反映到商品选择和购置的个人主义。就诱导和操纵或控制而言,电视的声色并茂和从点到面的传播特征恰好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平台。这是电视得以大幅度扩散和应用的前提和基础。
当然,电视除了以传播消费文化的方式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服务以外,往往还肩负着为政府和掌握着话语权的精英们扩散或者宣传意识形态的任务。作为形塑“意识形态”的机器,电视天生具有社会控制的属性。但是,市场经济的话语并不总是与政府或精英们的意识形态一致的。在西方,特里·伊格尔顿观察到: 把大量时间花在电视的收视上,事实上就占用了民众参与更加严肃的政治活动的时间。电视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相反,电视却把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消解掉了。于是依赖电视而脱离现实状态下的现代人,逐步失去其社会性,成为被符号所操纵的消费机器。当然,除了收看电视这一形式本身可视为一种社会控制之外,其传播内容所暗示的总体价值取向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忽视的部分。
在我国,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电视在春节晚会上告诉我们的首先是“恭喜发财”而不是“身体健康、合家欢乐、节日愉快”等等。然后又在幻境般的演播室里展示着“能挣会花”的意义。在合家团圆的除夕夜,“合家”盯着的是美轮美奂的电视幻境,而不是亲情的交流。那首“常回家看看”的歌曲的确是脍炙人口,但它没有了内容。最终以唤起廉价激情的方式,流入了通俗或庸俗的行列。这是电视反社会交往的极端例子,也是电视的基本属性之一。
但是电视还是有其“集体行为”含义的。只不过这种“集体行为”是社会学意义上离散大众的集体行为。从微观上说,这种行为表现在“卡拉OK"和“装修”等方面。大众不再满足于观看电视上流行歌手的表演,他们要自己卡拉OK。他们也不再停留在对电视上“成功人士”豪华住宅或宾馆的欣赏,个个要争先恐后的通过把那些“伪”装潢搬进家中来展示自我。问题是这里表现的个性是电视上表演的“个性”,是人人都模仿的个性。从宏观意义上说,基于本能的冲动,大众常常对节目的诉求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和激情。这就是“暴力”、“犯罪”、“性”。
以娱乐的名义,在消费文化的引导下,根据大众自己的口味,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以经典为标志的文学艺术都被复制了,一切能够想象到的景色都被毫不客气地摆到了我们面前。这使得传统贵族(如果我们近代还有的话)或一些精英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精致生活”黯然失色。的确,如果说这些贵族或精英对过去的“文革”是切齿痛恨的,那么他们现在面临的只有尴尬。我们从这两个层面上说电视还是有“集体行为”的。这是市场意义的“集体行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的造反派通过“革传统文化的命”而得到宣泄,现在则是大众通过电视“娱乐”而释放“激情”。区别在于从前者的“集体行为”获利的多是些政治野心家,从后者的“集体行为”真正获利的是商家巨贾。而无论前者和后者,都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斯文扫地”。
在电视时代,大众的“威力”源于广告的支撑。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政府或精英也希望利用电视教育民众。但电视在这方面显得那么软弱。电视观众是大众。而大众想要的是娱乐而不是受教育。当社会成为消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消费文化之后,无论是利用电视进行说教、还是弘扬所谓的高雅、精英文化往往是一厢情愿的举动。而电视观众和广告商则有着一拍即合的共同点,那就是超越阶级、民族、性别、年龄,植根于本能欲望的娱乐与消费。观众消费电视节目,电视台以把观众卖给广告商的方式得到制造娱乐节目的资金。广告商或是直接通过电视广告的形式,或是通过对节目内容间接的影响(往往是引导)来刺激观众的消费欲望。不管这种欲望是廉价的还是高雅的,我们必须明白,在市场经济下,无论是电视台的生存还是观众的娱乐都取决于电视广告的效果。也就是说,取决于投放广告的公司的满意度,而不是节目是否庸俗。这是市场经济下电视生存和发展的底线。此外,即便是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需要广告来支撑。从此意义上来说,广告是电视的生存之本源,收视率的高低掌握着某个电视节目甚至电视台的存活与否。也可以这样说,性、暴力、犯罪、娱乐等之所以充斥电视画面、一波又一波受西方电视娱乐性节目所启发的本土节目之所以炙手可热,恰巧是这类画面或节目特别适合于推销商品,和广告商个人的价值观取向没有必然联系。
因此,电视不是因为大众需要廉价的娱乐而诞生和扩散的。只是从效应上而言,电视以诉诸于本能感官的手段,通过唤醒人类心中普遍存在的本能欲望,使得以娱乐化生存为表征的消费文化得以行销天下。在这种以“欲望”为排头兵的文化氛围中,电视成为新的造物主或曰“速食上帝”: 它所推动的流行时尚决定着芸芸大众衣食住行的选择、喜怒悲伤的标准或模式; 它既可一夜间制造神话、明星,也可顷刻间摧毁之; 甚至当比尔·克林顿通过在新闻演播室里吹萨克斯来改善其媒体形象,连战和吕秀莲争着上《康熙来了》以提高各自民意支持率的时候,传统的政治权力也不得不在这股娱乐化狂流中以娱乐的标准来包装推销主张、观点。
当代知识阶层的一些专家对通过电视而进行的文化庸俗化和人类娱乐化生存现状深感担忧。因此,他们不断地批评电视这一媒介。当然他们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传统的知识阶层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基础被电视颠覆了。但就电视行业本身而言,电视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某些专家们所批评的节目“庸俗化”。电视已经在受众“娱乐至死”的实践中进行了终极表述。事实上,美国的传统电视自上世纪90年代便已经在走下坡路。但这主要还不是庸俗化惹的祸,而是新媒体的挑战。我们知道,庸俗或者说通俗本身就是电视的招牌,但如果电视连庸俗或通俗都输给互联网的情况下,传统电视的出路在那里呢?就影响而言,在我国的媒体生态结构中,电台让位于电视台才不过十余年的事情。互联网与传统电视之间的角逐会重演历史吗?也许会,因为互联网可能不仅比传统电视更能“庸俗”或“通俗”,而且对自我来说,可以具有电视所不能比拟的自由度。伴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成熟,这一天的到来也许不需要十余年。电视的终极表述是娱乐,互联网的代名词可能是“满足”。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我们进入全球化时代。我们以娱乐和满足的方式存在,但以“自我”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本身却可能受到市场社会的空前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