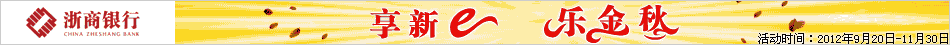美国教授:城乡二元体制是最丑陋的不平等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 文贯中
理想的收入分配格局,追求的是起点的公平和竞争规则的公正,却不追求竞争结果的强制性平等。这是因为人的天赋各有不同,加上各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千差万别,强制性地要求收入分配结果必须一律平等,无异于削足适履,矛头必然指向有发明创造天赋的人群,打击的必然是努力向上、积极肯干的人群,这必然导致全民的愚昧反智,懒惰懦弱,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结果必然是普遍的贫困。犹记得当年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对民营企业家、知识分子、科学家、自由职业者和手工业者推行的是制度性的歧视乃至全面封杀。结果,自然是打击了社会中最有生气和最有创造能力的人群。现在想来,何其愚蠢和短视。一般来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前现代社会,都是用身份和特权将人群分为三六九等,使人口的大多数成为二等公民,无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没有平等的权利追求收入的增加和财富的积累。
所以,一个理想社会要做的是不断清除由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对某些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使他们能成为社会平等的一员。从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西欧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它们所经历的诸如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虽然涉及的似乎是文艺、科学、哲学和世界观,但其经济学上的意义在于使生产要素逐渐得以冲破专制的禁锢,破除身份特权,废除对农奴的束缚,对第三等级的歧视,做到全体民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使他们各自拥有的生产要素在市场面前一律平等。这种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市场面前的平等是我们所说的起点平等的主要基础。西欧各国较早做到这点,使西欧的收入分配既能趋于相对平等,又没有破坏它们持久繁荣的内在动力。
从经济学的理论来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结合,是市场经济的首要前提。所谓生产要素,无非是指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投入。每个人至少拥有一样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或者人力资本。只有当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能够自由流动,并且能够自由而平等地在生产过程中和其他要素相结合,各种要素的拥有者才会从自利出发,有极大的动力通过不断试错,使自身拥有的要素实现最佳组合、使自身的价值极大化。而只有当所有的要素都实现了最高价值,国民财富的总值才能同时极大化。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法律允许一些阶层高高在上,拥有特权,另一些人则受到歧视,丧失作为平等公民的相应权利,这样的社会必然既无社会正义可言,也无经济效率可言。例如,一百多年前美国的黑奴制,便是一例。这种黑奴制虽然为美国南部的大种植园主和他们所代表的落后生产方式所支持,却严重阻碍美国社会的前进和经济的发展。这一野蛮制度既是对美国宪法载明的人人生来平等、自由这一理念的公然挑战,也严重阻碍着当时方兴未艾的美国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对要素自由流动的内在要求。很清楚,美国只有在清除了这种极不合理而又血腥残酷的黑奴制之后才能大步前进到一个兼顾公正和效率的现代社会。
我在不久前给《华夏时报》所撰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现在人为地维持起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制度还有很多,其中城乡二元体制是十分主要而又特别丑陋的部分。我们知道,贪污腐败也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至少在法律上贪污腐败是非法的,一旦被揭发是要治罪的,因而不能堂而皇之公开进行。可是,城乡二元体制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赫然存在的,有法律根据的,却因和21世纪的世界民主、平等的潮流格格不入而显得特别丑陋。
为何如此说呢?因为作为这一体制的两大支柱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都是公然歧视作为相对收入本来就已经最低的农民阶层的,因而和中国自称的社会性质特别格格不入。先看中国的户籍制度,它和世界上一般的户籍管理、登记制度截然不同,这一始于1950年代,三年大饥荒期间得到巩固、完善的制度,人为地将全体公民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并对农村人口的进城打工、就业、定居、子女就学、家属团聚以及住房、医保、劳保乃至政治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到了改革开放前夕,城乡二元分割已经成为几乎不可逾越的天堑,不幸生而为农村户口的亿万人群被这种户口制度严密地摈斥于城市文明之外。在其他国家作为人的天赋权利的自由迁徙和定居的权利,在中国的户口制度下长时间内成了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不敢梦想的特权和恩惠。
李佩甫在《城的灯》中描写的冯家昌作为一个不甘屈服于自己命运的农家子弟,为了冲破城乡之间的森严壁垒,尝尽人间的甜酸苦辣,饱受城里人的凌辱和白眼,不惜扭曲自己的人性,置深重如山的恩义于不顾,抛弃为自己做出巨大牺牲的初爱,为的不过是一个城市户口,以使自己和家人能永远脱离农村的贫困、愚昧,身为“乡下人”额上天然烙上的“卑贱”两字得以彻底清除。在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民获得了进城打工的权利,但要获得城市的户口,进而在打工地定居的权利,却还是十分不易的,由此而来的家属团聚问题,子女上学问题,乃至住房、医保和劳保等一系列问题,更难以解决。所以,户口制度造成的农村人口二等公民身份至今没有基本改观。至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另一支柱的土地制度,则问题更为严重,限于篇幅,只能留待下次讨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