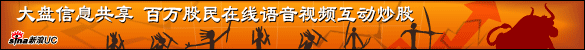不支持Flash
|
|
|
|
行走的主人公(一)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5日 11:59 经济观察报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wp9952@hotmail.com 贾樟柯在提到自己的影片《三峡好人》时说道:“两位主人公越过千山万水解决自己的感情问题,就像古代的大侠翻山越岭化解恩仇一样,只不过这故事发生在现代。”其中“古代”与“现代”被轻松地放在了同一个层面上,遥远距离的不同年代具有了一种空间上的对接。不同人们面对的问题虽然不同,翻山越岭前往解决的决心却是一样的。 这是从人物的角度来说的。从影片所提供的实际空间来看,古代与今天在空间上正好形成强烈冲突:一方面是自古以来秀丽的山川,是在这山川之下蕴涵的深沉丰富的文化,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废墟,是现代化带来的满目疮痍。某种对立和冲突是触目惊心的,现代化进程日夜掘进所造成的“废墟”,甚至成了这部影片令人印象深刻的真正主角。 然而人们同时希望看到的是:在这种猛烈的断裂中,身处其中的人们是如何应付的?他们的人性如何因此而经历冲撞?这之后在他们身上留下怎样的痕迹?显然这不是该片所想回答的。两位从山西来的解决自己婚姻问题的男女主角,对周围环境的突变并不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们像古人一样目光坚定地追寻自己的既定目标,不受环境的任何影响。他们的坚定与环境的脆弱,正好朝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人物与背景几乎脱离,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并没有去面对和处理真正复杂的问题。 叙事作品中“行走”的题材有一个好处,在于它的开放性。主人公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将不同地域、不同视野带进来,在不同的时空之间造成连接,让它们互相对话和对峙。在某种意思上,行走的开放性与现代性的开放性是一致的——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大规模的交通和交流,能够将彼此距离遥远的地域联系起来,并在这种地域关联当中提取出新的社会关系,即吉登斯所说的“脱域”(disembedding)。 一旦结合现代性这个视野,就会发现,现代的“行走人”与古代大侠的不同:传说中的古代侠客怀抱自己超世俗的理想抱负,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外一个空间,但是他主要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他与世俗世界不发生联系,他只是偶尔路过,他所穿越的那些空间之间也不存在地域性关联,它们仅仅是一些地名和风光。现代人的行走则不同,他从一个空间抵达另外一个空间,如果不是旅游观光,那么则是为自己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寻求一个安身之所,将这个世界的某处变为自己的新家。如此,他的行走便是在社会关系中穿行,是承受着不同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的压力。 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语境当中。如人们所了解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户籍制度,主要是为了限制人口流动,一个人的户口所在地便是这个人长久的工作居住场所,甚至几十年不变,终生如此。1990年吴文光的纪录片 《流浪北京》记载了那些最初吃螃蟹的人,他们主要是一些艺术家,为了实现艺术梦想他们不仅放弃了原先稳定的工作,而且放弃了拥有城镇户口的“原籍”,因而值得拿起镜头对着他们。 户籍制度最大的制约性体现在“城乡二元对立”上面——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不能兼容,拥有农村人口的人们不得在城市拥有一份正式工作,不能享受在城市工作的种种福利如住房、医疗保险制度等,无法在城市安身。因为出生地的缘故,占人口多数的几亿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这中间虽然经历了一些插曲,比如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就有城市人口下放往农村流动,直至文革后期的大规模知青下放和干部下放,但是农村人口仍然极少有机会到城市工作和生活。这种情况直至1990年代之后才发生真正改变。大批农村人口离开乡村,走向城市打工谋生。据有关方面公布,近年已有超过1.14亿农民进城打工,还不包括他们进城的家属。这个庞大的流动人群数目,构成了中国1990年代社会变动最触目的景观。当在他们从一个熟悉的世界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时,恐怕比城市人更加体会打破隔阂之后的 “关联”所引起的各种冲突。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之间,他们经受着最为严峻的冲击和考验。就与贾樟柯电影相关的三峡移民们来说,他们并不是从李白笔下的白帝城,一下子就跳到今天的遍地废墟当中,这中间已经经历了许多过渡性震荡。 近些年中国电影中频频出现的“行走”题材和“行走”的主人公,最早可以追溯到吴天明1984年执导的影片 《人生》。其中城乡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为主人公高加林在来自城市和农村不同女朋友之间的选择,因为关注的中心停留在“城市”还是“乡村”的“属地”问题上,因此“地域”于其中主要不是关联关系而是对立关系。1992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不同于高加林在城市女友的庇护下讨生活,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农村妇女秋菊只身前往陌生的城市。这种情况只有到稍晚一些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之后才能够出现。 必须指出,比起波澜壮阔和险象丛生的社会现实来说,电影中所呈现的,只是冰山之一角。出现在当代电影中有限的行走的主人公,比起中国现实中上亿的背井离乡的人们来说,连一小角都还算不上。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从电影这种媒介中得到的,与其说是现实本身的形象,不如说是人们对于某种现实的理解和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关注当代电影中行走的题材,重点是关注在行走的行为背后,人们是如何承受猛然打开的地域关联所引起的心灵和文化震荡,他们在这种震荡中是如何挣扎、如何自我理解和自我安置的,从中也折射出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现代性进退迎拒的复杂心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