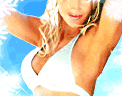索家村艺术营:被挟持的艺术人质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04日 14:09 《财经时报》 | |||||||||
|
一个自发成立的艺术营,在高墙外居然有保安把守,给人一种森严而又夸张的印象。它在短时间内散播出来的影响力,迅速激发了一批国外艺术青年的梦想,并在此聚集。而不久前一纸法院的“拆除”判决和强制执行,让很多艺术家再次踏上“漂泊”之旅。于是关于艺术与艺术生态空间、城市规划与艺术理想冲突、人文情感与法制约束等诸多现实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并成为我们城市发展中挥之不去的痛
□ 本报见习记者 赵倩 2005年11月15日,清早,艺术家任思鸿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推土机来了”。他说当时自己睡得好好的,逗什么呢,以为有人跟他开玩笑,可不到半个小时,一连6个朋友的电话,都在告诉他“推土机来了”。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真的,曾经预感的事情来了。任思鸿火速赶到索家村国际艺术营,因为这里,有他刚刚从朋友那里租下不久的工作室。 看到现场的一片狼藉,绝望之情由然而生。自己几年的心血全费了,租金耗费且不说,主要是他还有完成和未完成的画作都没来得及处理。 艺术家的SOS 其实,这已经不是任思鸿第一次接到艺术营要拆除的消息了,艺术营的艺术家们显然已经对提前两天得到的消息麻木了,他们没有做任何准备。 “当时来了很多法警,法警们并没有很明确说明,显然是封锁消息后拆除的,同时他们动用几辆警车堵住了门口,禁止人员出入,从小桥那边(大约距离索家村艺术营500米)就不让车辆通过了。” 雕塑家杨韬描述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被拆的那边,像尚扬这样的老艺术家,一生的精华就在自己的那间画室里了。尚扬的学生想把画作从屋子里搬出来,但遭到了法警的言辞拒绝,后来还引发了争执。” 这边,一个外国艺术家,正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边看着法警边喝闷酒;那边,一个上海艺术家,穿着立领的中山装,在法警中间走来走去,“警察看我,我看他。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我自己的家,自己的院子,我就蹿来蹿去!” 而任思鸿则站在法警和艺术家中间喊了一嗓子:“今天怎么没有‘李大钊’!” 几个月前,这里曾经上演过百名艺术家用SOS的行为艺术保存“北京国际艺术营”的活动。与此同时,一篇名为《百名艺术家签名呼吁挽救“北京国际艺术营”》的文章见诸网络,称:“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拆除我们这么一个已经成型被人看好的艺术营?我们恳切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与艺术家接触,倾听我们的心声,做先进文化的保护者和推动者而不是摧毁者!” 著名艺术家包泡更是发出了强烈的呼声:“推土机来了我第一个上!” 时隔数月,推土机真的来了,包泡在强制拆除的第二天就搬离了艺术营。 艺术家的群居生活 杨韬把这些艺术村、艺术营看作是和外界接触、交流等多方面的平台。“艺术家的社会积累因人而异,团体的力量永远大于个人。有些名气大的,比如方力均,他不需要扎堆,他已经很火了,‘我在哪儿都是别人来找我的’。但更多的艺术家是希望利益均沾的,这也是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 所以在索家村被强制拆除的事件发生之后,部分艺术家也私下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艺术家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群体,798的房租价格高了,很多人自然转到索家村这样的地方。但是出问题的时候大家又会用文化来说事。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索家村在当初招租的时候,每平方米每天不到0.5元,而同期,798的房租已经达到每平方米每天1.5元,索家村附近的费家村也在每平方米每天1元以上。 包泡非常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曾经对一帮艺术家说,你们是不是卖花生米的,不是搞艺术的吧?!还有媒体上说,我们是在这里‘等待天上掉馅饼’,等着外国资本家来买我们的画,我觉得这个太无知了,是对我们的污蔑。” 但不管怎么样,近些年北京的国际文化艺术活动呈几何级数增长,国内艺术家对创作空间的要求迅速扩张,大批国内外艺术家进入北京望京及周边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索家村的出现其实是对北京日益饱和的文化创作空间的补充。 多方利益纠葛 基于对文化的渴望,很多人喜欢把艺术营看作是城市的一种标志,所以很同情艺术家的处境,但艺术营建筑的非法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引伸出“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讨论。 其实在2004年艺术营建设开工不久,崔各庄乡规划科就得知,艺术营项目未经规划和审批,于是发出了“停工通知单”。但经过高又高公司的协调,一个月后又复工继续建设。 2005年5月11日,崔各庄城管分队向高又高公司送来《拆除决定书》。5天后,高又高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递交了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重新审议。 就在工程刚刚开工、违规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艺术营的招租工作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从2004年3月开始招租,短短半年时间里就有126名中外艺术家入住艺术营。 2005年6月10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下达了强制执行拆除的通知。 在这个过程中,高又高公司向艺术家隐瞒了艺术营的非法性,直到6月12日,艺术家们才知道艺术营将于16日上午9时后被强制拆除。高又高公司总经理黄志高说:“那时,我们希望暗地里找找关系。”而租赁土地给高又高公司的索家村村委会则表示,没有及时告知,是怕住户知道了影响不好。 这个时候,很多艺术家已经在这里安家,而且为自己的工作室投入了数万元的房租和装修费用。于是后来就出现了艺术家们在地上、墙上刷了各种“SOS”求救信号,并围坐在上面反对拆除艺术营,进行保存“北京国际艺术营”百名艺术家签名活动。 活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几天后,传出“出于文化建设的考虑,暂时不拆除艺术营”的消息。于是,高又高公司又向艺术营的业主收取了下半年的租金。艺术家继续在这里生活,几个工作室又开始继续装修。然而好景不长,11月15日由朝阳区法院对艺术营执行了强制拆除。 一个循环的悲剧 “这其实是一个循环的悲剧”,陈丹青这样跟我们描述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从圆明园艺术家被驱赶,到后来有了宋庄、798、索家村,整个过程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社会的容忍度、接受度也在提高,但是却很不幸遇到了一个法律问题。” 著名艺术评论家杨卫也发文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今年是2005年,十年前的1995年,一个名为”圆明园画家村“的文化村落被强行取缔,从此在地图上消失。十年一轮回。今年,又一个名为”索家村国际艺术营“的文化村落遭此厄运,被推土机强行推倒,化为了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同样是在秋天,同样是在万物凋零风飕飕的时节,两幕惨淡景色的对接,不禁使人怅然,令人伤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纽约决定大规模改造苏荷区为现代化商业区,但经过长期争论,纽约市长终于决定全部保留苏荷区旧建筑景观,并通过立法,以联邦政府的名义确认苏荷区为文化艺术区。几年时间内,苏荷文化艺术区帮助纽约成了世界艺术中心,但北京的国际艺术营似乎远远没有那么幸运。 “北京和纽约根本没有办法比,纽约政府专门立法,使之完全合法化,而北京全部是艺术家自己在那弄,北京的规划中从来没有考虑艺术,从来没有过。”18年的美国游学经历让陈丹青对此不无感触。 拆与不拆,是个问题 那么,保护“艺术”的名义,与政府的规划管理,到底孰轻孰重?在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教授的交谈中多次强调,索家村国际艺术营是未经许可的违法建筑,拆除是合法的行政行为。但是依法行政的更高要求就是要看是不是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而不是符合法律的条文。就这件事情来说,可以考虑罚款、修改和拆除三个方案,尽量选取损失最小的方案。 政府的公权力具有至上的权威性,拆除违法建筑本不是问题,但处理结果却能反映出政府的管理智慧。中国非常缺少像798、宋庄、索家村这样艺术阵营,大量国内外艺术家都需要在北京这个城市获得艺术创作和发展的空间,这本身就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陈丹青认为,我们从综合实力上来讲还是不能跟发达国家相比,需要解决的事情还很多。其法已经借鉴过来了,关键是政府应该把法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不关心艺术可以,但艺术家自己搞起来的东西就应该让它生存下去。 不论是哪种声音,都说明城市需要文化,合理处理艺术与城市规划的矛盾才是城市现代化的关键。 新闻回放 2003年,原在朝阳区崔各庄乡索家村种植草皮的高又高公司,租用55亩地建造成索家村国际艺术营。 索家村国际艺术营从2004年3月开始招租,每平方米每天不到0.5元,因此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入住。 然而,就在索家村国际艺术营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份《拆除决定书》。2005年5月11日,由于被确认为是违章建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下达了《拆除决定书》,要求拥有此处物业管理权的北京高又高经贸有限公司拆除索家村国际艺术营。 11月15日,朝阳区人民法院派出的法警和警察对涉嫌违章的北京索家村国际艺术营执行强制拆除作业,并将D排部分艺术家租用的房间拆除。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随笔砸谈 > 正文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12月大黑马免费送!! |
| 投资3万元年利100万! |
| 美国保佳教您赚百万! |
| 完美女人是怎样炼成的 |
| 开男士品牌名店赚疯了 |
| 名品服饰 一折供货 |
| 关注:肾病、尿毒症!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瑜珈美容俱乐部太赚钱 |
| 高血压治疗上的飞跃! |
| 开个咖啡店赚了几百万 |
| 拯救男人,还你健康! |
| 艾妃儿专业美容! |
| 好男人更强,更自信!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