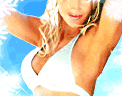|
八道湾里的旧梦五味杂陈,苦茶庵里的叹息,直到今天仍余音丝丝。在北京,曲折的胡同称为“八道湾”。观照周氏兄弟的一生,“八道湾”三字真是一语成谶
□唐涛
鲁迅在北京的八道湾旧居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毕竟,在这里他住了不到4年。然而,
八道湾里的旧梦却让人五味杂陈:阿Q出世、兄弟失和、文革批斗……苦茶庵里的叹息,直到今天仍余音丝丝。
在北京,较宽的胡同叫“宽街”、窄的叫“夹道”、斜的叫“斜街”、曲折的则称为“八道湾”。观照周氏兄弟的一生,八道湾三字真是一语成谶。
周作人的八道湾
对于一个在京的外地人来讲,拿着地图找“八道湾”实非易事。由于门牌号有些模糊,为了确认,我指了指八道湾11号院问纳凉的老人,“这是周作人的故居?”老人脱口而出说:“鲁迅,是鲁迅的老房子!写阿Q的地方!”语气里透着一种纠错的使命感。
踏进11号院,未见主人。这院子本是鲁迅将绍兴老屋卖掉后用所得的1000多块银元购置的。这是一套三进的四合院,共有20多间房子,为了这个新居花费4000块银元左右。当时,兄弟俩月收入共600多块银元,房价相当于他们7个月的薪金总和。房屋最初有契约,全部房产分为四份,三兄弟每人各一份,老夫人一份,上下三辈人都住在这里:鲁迅住前院南房,老夫人和朱安住中院北屋,周作人夫妇及子女住后院。现在的后院和中院改动不大,但也有修葺过的痕迹。
鲁迅在1923年就离开了八道湾,而周作人一生却都留在这里。八道湾确实是周作人的八道湾。纵观周作人的一生,1945年以后,他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扑朔迷离,兄弟反目
在周氏兄弟共处一院时,八道湾11号俨然是一个学者的高级沙龙:周氏兄弟先后邀请过蔡元培、胡适、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郁达夫等名流来此欢聚。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有时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兄弟间的欢快共处一直持续到1923年的7月。是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缘何搬出八道湾,周作人当时是何心态,兄弟失和与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多少关联,这些年诸多著作已经写得够详尽了。但,这毕竟是家事。亲兄弟失和,当母亲的都搞不明白,她对邻居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奇怪的是,兄弟俩谁也不作解释。在当时,倒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兼老友许寿裳说了一句话:“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周作人后来与友人的通信中曾暗示一旦解释开来,对鲁迅和他本人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羽太信子为什么不愿和鲁迅同住,也就成了一个谜团。
更奇怪的还在后面:已经搬出八道湾的鲁迅于1924年5月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冲突中,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没有击中……
一个月后,周作人发表文章《破脚骨》,把流氓无赖考证个底朝天,知情者说,文章是暗讽鲁迅。此后,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为笔名,宣泄内心的情绪。
半个世纪,一个“苦”字
周作人的书房原叫“苦雨斋”,后更为 “苦茶庵”。从1919年搬进八道湾11号院至1967年周作人辞世,近49个年头。半个世纪的风雨,知堂用了一个“苦”字就给打发了。
抗战期间,周作人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关键的决定:出任伪职。尽管后世有诸多说法来论证周作人的无奈,也有学者称周作人“曲线救国”,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事实是:周作人成了汉奸。
抗战胜利后,八道湾的房产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但从处理的结果上看,仍然是按照鲁迅契约执行的,仅仅罚没了属于周作人的那三分之一。前院由国民党的部队占着,部分后院仍留给了周作人的家属,实际上他们住的是产权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当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满释放的周作人再次回到“苦雨斋”时,已是心力交瘁。
解放后,北京市政府房管部门接管了这所院子,原来驻进的解放军退出,许多住户搬了进来,这里从幽雅的四合院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周作人按规矩每月交纳租金。为了维持生计,他仍然为一些报刊写文章,间或做些翻译。
与兄弟失和一样,周作人没有为“汉奸”之名辩解什么。将“苦雨斋”更名 “苦茶庵”则可看出他的心境:望苦雨,不如饮苦茶。在任伪职期间,有一次他曾对友人形容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
用“苦”字形容周作人最后的岁月十分贴切。不知是刻意使之,还是无意为之,周作人晚年花了大量的心血去研究鲁迅笔下的人物,这为研究鲁迅的学者提供了无比宝贵的资料。我们无法想象周作人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去写这样的文章。
1966年,文化大革命掀起巨浪,周作人抱着多病之体瑟缩在墙角一隅,红卫兵甚至不准家人送饭给他,他已有心绝气死之感。他提笔给章士钊写了一封求救信,章士钊派了他的秘书王益和前来致意,但并未说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了却了他多难的一生。此时他身边净无一人,骨灰也没有获准收取,如今这静悄悄的八道湾,正应了那一句“声销迹灭”。
链接
周海婴:这里不算鲁迅故居
□晓棠
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对八道湾本来很有感情,他曾经与朋友来到八道湾附近,被告知房子近在咫尺,他就非常高兴地走去看。当时周作人还在狱中,家中只有羽太信子,第一次见到周海婴的羽太信子,竟对晚辈破口大骂,使周海婴顿时厌烦,从此再未登门。
后来,周海婴在他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八道湾有过这样的说法:“前一阵有人提议要保留八道湾的鲁迅故居,我感谢爱护父亲遗迹的好意,但我和建人叔叔的后人都以为大可不必。八道湾的房屋以北房最佳,而父亲本人根本没有享受过,而苦雨斋又与鲁迅不搭界。他早年住过的屋子,又都破损不堪,而且听说现在也不是原屋了。要说北京的鲁迅故居,西三条才是。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钱独立购买的,并且也是居住过的。由此可见,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是值得国家保护的吗?”
他回忆说,鲁迅去世仅几个月,周作人竟私自换写了一份契约,将户主姓名变成他自己,还找了几个“中人”签了字,企图独吞这套房产。这份契约是被许广平的朋友偶然发现并拍照留下,直到他要编《许广平文集》,才发现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