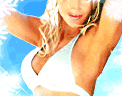|
□ 王家新
1960年初夏,美国著名的文学杂志《巴黎评论》发表了《三访帕斯捷尔纳克》,访问者奥丽嘉·卡里斯莱,一位美籍俄罗斯文学女性,她的父亲也是一位作家,并和帕斯捷尔纳克本人认识,而她的祖父为十九世纪末俄国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
多年前,我在乌兰汗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录《人与事》的附录中读到这篇访问记,便为它深深吸引。这是我所读到的最有独特价值和魅力的文学访谈。我甚至每过几年都要把它找出来看一看,就像一个人渴望呼吸到某种空气一样。的确,这不是一般的访谈,这是精神的叙事,是两个灵魂的相遇。它所散发的气息,它的那些涌动的潜台词,甚至使我想起了《日瓦戈医生》中男女主人公的这样一段道白:“现在我和你是这几千年来世界上所创造的无数伟大的事物中最后的两个灵魂,正是为了怀念这些已经消失的奇迹我们才呼吸、相爱、哭泣,互相搀扶,互相依恋”。
这也就是为什么奥丽嘉由一开始的怯生生的探访(因为帕氏住在远离莫斯科的别列捷尔金诺,而且不愿意会见来访者),到最后居然从心中涌起了一种“幸福感”的最根本的原因。别列捷尔金诺之行使她满怀感激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她不仅将她对诗人的印象,也将她自己最隐秘的个人感受不无勇气地写了出来:“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我感到何等的幸福……我们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或更久一些,我希望这种时间能够延长下去,再延长下去……”
这种情感的涌动是在第三次探访期间,当时诗人刚刚结束早上的散步(穿着一身藏青色运动服,而不是中国的文学小青年所想象的那种风衣),而她被请进阳光明媚的二楼上的书房。这当然不是那种盲目崇拜,而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相互认知上(第一次见面,她就意识到莫斯科文人圈中关于帕氏的传言是多么荒谬,什么“陶醉于自我形象”啦,什么“自我中心主义”啦……),因此,这种情感的涌动会在这次访问的最后再次出现,虽然它带着告别——也许是永别的意味:“我已经走下门廊,踏上了小路,他又叫我了一声。我趁机又停下了脚步,感到幸福,我回过头去,最后望了望帕斯捷尔纳克……”
奥丽嘉来得太迟了。奥丽嘉来得正是时候。她来得正是“获奖风波”(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随即遭到当局的严厉批判和指责)尚未完全过去、诗人有太多的话要对一个可信任的人讲的时候;她来得正是诗人步入人生的晚年,要回首历史并清点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对她自己更重要的是,她来得正是她需要理解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什么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品质的时候。因此,访问记中这种情感的坦露和涌现,虽然引人暇想,但却不可混同于一般的罗曼史。它带着一种灵魂之间无言的理解,带着一种真正称得上是“纯洁”的精神的气息,也带着人的高贵和尊严。别列捷尔金诺之行是一次精神之旅,对每一个读到它的人,也将是一种照亮和提升。
奥丽嘉就这样写下了她的访谈,同时,她也被诗歌所书写的——那远离莫斯科的雪中的开阔小镇,那座处在乡村路拐弯处的棕色的有云杉作背景的房子,那忐忑不安推开的花园与道路之间的栅栏门,那悬挂在墙壁上的出自诗人父亲手笔的托尔斯泰、斯克里亚宾、拉赫马尼诺夫的肖像画,那缓缓穿越积雪山坡和墓地(它看上去“宛如夏加尔油画中的背景的一个小角落”)时的交谈,那行经结冰路面时的细心搀扶,那由诗人本人端到餐桌上的橘子(“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我已经吃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里经常出现橘子——在《日瓦戈医生》开头部分,在早期的诗里”),那种七旬老人如同年轻人的精神焕发,那回首一生时内心的某种迸发(“茨维塔耶娃的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痛”),那种写作《日瓦戈医生》时盘居在诗人心头的巨大的“欠债感”,那走出车站、临近诗人住房时突然刮起的暴风雪(“我看到雪花像海浪一般层层飞过……再过几分钟,我将跨进他的家门,听到他那诗一般的语言,真觉得不可思议”),当然,还有那种从内心深处涌起的幸福感,那种对生命、对大地和星空的感恩之情,将伴随着奥丽嘉乘上返回莫斯科的火车,也将伴随她回到更遥远的另一个世界。这些,将成为她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它们将被书写下来,但仍将是她最隐秘的记忆。
那么,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又如何呢?也许这就是所谓“命运”:奥丽嘉的这篇访问记,诗人本人并没有来得及读到,就在它发表的前两周,1960年5月30日,诗人因癌症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逝世(“昨天无与伦比的声音落入沉默/树木的交谈者将我们遗弃/他化为赋予生命的庄稼之穗/或是他歌唱过的第一阵细雨……”阿赫玛托娃《诗人之死》)。死前他是否惦念过远方的那个访问者呢,我们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他曾写过令人难忘的诗句,来描述那种曾照亮他的、给他生命带来新生的美丽女性。
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生于莫斯科。1912年赴德国马尔堡大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191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1958年,他因小说《日瓦戈医生》受到严厉谴责,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1960年5月,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