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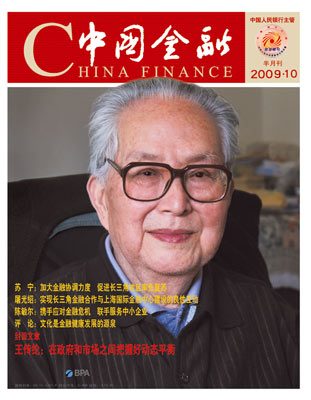
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传纶
本刊记者 魏革军
记者:王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您便毅然回国,投身到财政金融教学和科研事业中,并且一干就是将近60年时间。请您回忆一下当时您是怎样选择了财政金融教学与研究这条职业道路的?
王传纶:我1922年生在苏州,在三元坊上苏州中学,念到高二的时候抗战爆发了,就和父母避难到上海。到上海后不久,有大学招生,我就上了西南联大,专修经济学。抗战胜利后我去了清华大学念研究生,当时我的导师是陈岱孙先生。1949年我留学到了英国,在格拉斯哥大学读政治经济学系。1951年,当时负责清华校务的周培源先生有一次到英国访问,我去拜访他,经他传信,陈岱孙先生希望我能回国执教。那年年底我就又回到了清华大学,在经济系教课。
回国后很快我就随同北京高校土改工作队下到广西参加土改,一年后回到北京。不久清华大学的经济系便分出去了,成立了一个短暂的中央财政经济学院,一年后,也就是1953年,又大部分都转到了人民大学,和我一起转到人民大学的有吴景超、代世光等等,这么多年了,其中好几位都已经过世了。当时,陈岱孙先生在清华一直教授两个课程——经济思想史和财政学,到了人民大学后,他就对我说,“你来讲财政学吧。”结果这一句话就让我在这个讲台上干了56年。
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财政理论教学模式是怎样的?
王传纶: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可以说一切都在和苏联接轨:不论是专业系科设置(政治经济学、财政学、贸易、外交等系),还是教学内容,都有很重的苏联风格。我们教员当时的任务就是要把苏联的东西搬进课堂,于是组织上还派了很多苏联专家来培训教员,每个系都安排了些,小的系分到一、两个,大的院系三、四个,他们多数来自莫斯科财政学院、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等院校,态度认真,工作比较扎实。培训方法是由专家讲授苏联的情况,翻译好后,教员整理自己的教纲,然后讲给中国学生。
就我们系来说,财政学是基本课,其他的还有苏联国家预算、基本预算投资拨款、税收和企业财务等课程。我们教员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苏联的道理是可以接受的,理论部分也是可以直接讲的,但要和中国实际结合。当然,这个原则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讲苏联财政,后来内容上才开始有变化,逐步加入中国的实例,并注意和学生讲清楚哪些是苏联能做,我们现在也能做的,而哪些是我们不能硬套苏联模式的。
金融学方面由于内容的原因,西方的理论和实例可以稍微多一些。马克思货币理论与西方的关联很多,苏联在这方面做的研究也不少,比如资本主义通货膨胀和苏联的货币问题的联系等,这些内容我们当时也讲。
总的来说,这样几年的努力为人民大学的教学建设打下了一个知识的基础。虽然这样的财政金融教学安排主要是迎合当时的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而且在教学中灌输苏联经验多一些,理论分析和探讨少一些,但回忆当时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这也是一条必然的路子。“文革”之前的格局,大抵就是这样了。
记者:近60年的教学生涯让您见证了新中国财政理论的历史演变,请您谈一谈中国特色的独立财政金融理论体系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王传纶:我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接受苏联专家指导的时候,其实就感觉到苏联的学术界也一直是在变化的。根据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财政应该是国家的行为,而不仅仅是政府的行为,因此必须包含阶级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家对国内经济事务的管理,它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计划,而经济的计划、国家预算的计划、货币发行与银行信贷的计划,这是所有财经工作的三个依据。但苏联学术界自己也有一些独特的分析和研究,比如在这样的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如何来体现,如何在计划中利用好价值规律?苏联学术界在上个世纪列宁新经济政策之后就一直讨论这个问题,由于牵涉到政治问题,讨论得并不充分。当时一般的观点是价值规律要考虑,商品价格要体现价值规律的要求,但无法再细究下去;而经济核算中劳动价值量的耗费,也讨论了很久,但并不广泛。直到斯大林去世前那个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价值规律才得到了肯定。还有一个问题是苏联的通胀问题,当时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以另外一种形式来表现,是隐性的,表现在有价无市或黑市等,这方面苏联也做了深入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尚不能深刻体会苏联的这些争论,但也对价值规律的讨论有兴趣,如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在当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我们当时还特别关注货币需要量的问题。另外,我们认识到了既然财政收支、银行信贷、产品劳务交易都是以货币形式结算的,因此要保证财政、银行、物资三者的综合平衡——这也是人民大学这么多年来比较重视的领域。可以说这个阶段还是我们自己在摸索,有一些观点还不是很明确。例如,我们认识到了政府财政、企业财务和银行金融都是货币行为,要处理好各个关系,但对于微观的经济活动没有仔细探讨。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明确后,就很自然地给财政金融学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国内也逐渐开始借鉴西方的经济管理经验。1981年我编了《资本主义财政》这本书,介绍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制度、财政理论、财政政策和财政实践。我当时说过,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中,有些还是很有价值的,应当批判地吸纳,在扬弃中借鉴,不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轨’上费周折,要紧的是应当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我们的重大现实问题,充实社会主义的财政理论与实践。后来的二十多年的情况也证明了这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财政是有一些共性的;从中得出的一些概念、关系和规律是能够构成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来指导中国的财政工作的。
记者:中央政府将在未来几年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以及最近全球范围内一系列的政府救市行为又一次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您认为应该怎样把握?
王传纶:目前,中国财政和金融的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发展得都非常之快。比如财政以前单纯是政府的账房,现在政府的行为也多层次了,以前由上而下的模式也逐渐开始变成上下互动;同时财政收入结构和途径也变化很大,税收之外的土地和城市化收入占到了很大比例,财政与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微妙;金融方面,央行面临货币政策多目标和单目标的选择,金融市场也朝纵深化方向发展,微观的反馈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那么,宏观决策和微观决策的关系如何处理?根据我的理解,这实际上就是如何把握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对矛盾不单中国有,西方也有,不单现在有,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的时候就有。从根本上讲,政府经济活动的唯一原则和目标,就是和市场进行协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亚当·斯密的温和经济政策很受欢迎,直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经济流派中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活动要增多,来处理和解决市场的弊端。同时代的奥地利学派又认为凯恩斯主义过头了,在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自由主义又开始盛行……最近一两年,自由主义标榜的不干预市场原则受到了冲击,西方国家政府又开始向金融体系和企业予以财政支援,搞所谓新国家社会主义,这实际上还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处理方式。
2008年以来,对无形之手的迷信已经打破了,但是不要接受另外一个迷信。政府必须撒手一些事情,也必须做一些事情。打个比方,我们都有旅行经历,当你坐在船上,你发现当船离开港口的时候,或者是进入港口的时候,总能够在驾驶室里看到船长,他就在那里观察,看码头上的各种情况,而且他必须亲自处理出港和进港过程中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说航线有没有变化,对面有没有船等情况;而且经常地,船长还觉得不够,还要到港口找领航员,使船安全进出港。而在航道很熟悉、环境也比较好的时候,船上有很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船长往往在航海图上划一根线,然后就休息去了。所以我有时候想,政府与市场就好比船长与自动控制系统,只要自动控制系统能够解决碰到的问题,船长就可以退到后面。这时的船长不是不存在,只不过是船长不用亲自掌舵操作而已。
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三个条件,第一,政府必须出台好的政策,而不是更多的政策,就像船长不可能给每个人、每个机器订好工作规程,政府只需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正确的、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扭曲的政策;第二,政府应该是很明智的,很有能力的;第三,政府有一个很灵敏的信息反馈系统。有了这三个条件,政府就可以实现与市场的良好互动。老子说过,“圣人无为而民自化”,这里面包含了放任自由的思想。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讲的话不是说政府不做事,而是不要做错的事。还有句话说“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我理解为,经济发展很顺利的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都有一个相似之处,政府在经济中间扮演了它应该扮演的而且是很合适的角色。再放到历史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市场是个动态的平衡,不要让任何一方绝对化,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政府处理与市场关系的两个主要手段里,货币政策在衰退时期的作用有限,正如一根软绳能拉住疾走的车辆,却无力在停滞不前的时候从后推动车辆起步;主动性财政因为花钱的多少、方向、途径的选择都是由政府确定,因此更为有效。所以现在很多政府在发消费券,我个人认为这个政策的作用比较有限,还属于短期行为;要让老百姓觉得经济能安全起来,有意愿借钱投资或消费,银行的作用必须发挥。美国危机中银行信贷能力萎缩和公众普遍的失望情绪就是一个反例。
银行有和政府联系紧密的地方,也有和市场联系紧密的地方,因此银行不仅仅是破解目前经济难题的一个关键,还是实现政府和市场长期平衡的一个中枢。对于类似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银行是能够作出体制性贡献的。比如,过去几年里,在市场经济本身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用自己的信贷行为对当地政府施加影响,促使银行业的发展以及市场的完善,似乎很有效果。又比如人民银行领导全国商业银行系统的征信工作,随着逐渐积累,成果正在慢慢显现,对照同期国际评级机构的失误,我认为这是政府和市场互动的很好的一步棋。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