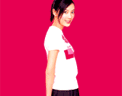转轨时期的浙江式民主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22日 11:14 经济观察报 | |||||||||
|
本报首席记者 章敬平/文 浙江不是一座孤岛。 我们论浙江的民主,当然离不开宏阔的中国语境,说浙江的民主生活,也不可能不被中国的公共生活所限定。所以,论浙江的民主,就必须回答:浙江的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未来
回答这些追问之前,还是让我们回到中国地图上那个形似海螺的狭小土地,考察它的自然人文风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这块土地上到底有着怎样的秉赋要素,竟使4600余万人的民主生活,成为世界民主化潮流中的独特景致。 七山一水两分田 人多地少,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的窘况,迫使浙江人先行一步地走出农耕时代,甘冒坐牢的风险,在1970年代,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和金器。 我们说,10000亿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那么,谁是这么庞大的GDP创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伟的32万余家私营企业700余万私营企业从业者。再问,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什么成为浙江经济的擎天柱?于是,答案开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在中学地理课上描绘中国简图的学生们,时常须在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画一个海螺,再在她的背部勾一条曲折的细线。东海岸边的这只海螺,就是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浙江,那条细线,就是无数文人歌咏过的钱塘江。钱塘江之于浙江,不仅给她注入水的灵性,还以江流曲折的特点,赋予她“浙江”的名字。 遗憾的是,女人般婉约婀娜的省名,未能掩盖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盘踞大半壁江山的残酷现实:70.4%的山地丘陵,23.2%的平原盆地,6.4%的河流和湖泊。“七山一水两分田”,在农耕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再加上人多,土地便成了浙江农民的命根子。 直到我们创设的讨论浙江民主的时间起点——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紧张关系依然没有丝毫改变。是年,浙江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这就是浙江人偶然间成为“东方犹太人”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须走出浙江,在流动中寻觅活路的生命路线图。当直接取资于土地的农业,不能让浙江人“黏在土地上”,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只得怀揣着自己的家庭梦想,像邱继宝那样挑着补鞋的家什,茫然地走向前路渺茫的东北。 “威尼斯人的进取和追求利润的精神太强烈了。对他们而言,只要顾客付钱,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紧要。他们不在乎背上贪婪的恶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如是说。如果我们将威尼斯商人面对的宗教,比喻成中国改革开放前对商业的禁止教条,将威尼斯人置身其中的“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甚至无清水可饮”的生存条件,比拟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就能明白为什么温州人在1970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的时候,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原料的贫欠,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的窘况,也驱赶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 浙江频临沿海的区位,一度也是劣势。作为海防前线,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工业布局,都过早地抛弃了它。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投资411元,全国倒数第一。回头看,稀罕的计划经济国有投资,却让他们少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没有国字号经济可以倚赖,扶持私营企业,就成了慑于政绩压力的官员们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中国古老的祸福相依的哲学,被最近30年的浙江经济再度验证。 事功的文化品格 浙江人重事功、务实效、敢冒险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一个要素。但它并非直接作用于浙江的民主,而是通过经济的成功影响到民主的生成。 惯常的说法是,永嘉学派重事功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重商务实精神的来源。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又被称作事功学派,看重经世致用,笃信“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 我们相信,重商,重事功,务实效的确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品格。只是,我们难以辨别这种文化品格的原动力,究竟是这个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的阶层所不能理解的事功学派,还是宋代以降的人地矛盾。彼时,面对4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的生产力水平,人均耕地不足2亩的浙江人,除了务实地应对生活的残酷,一粒米一颗稻地谋取生活外,还敢玩虚的吗?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振兴东北”作为新的政策兴奋点,被中央政府高调提出后,沈阳推出温州节,拉拢温州的商人。媒体传来浙江商人闯关东的新一波热潮。震撼于铺天盖地的报道,我开始了郑重其事的寻访。遗憾的是,浙江商人潮水般涌入东北,只是一场媒体“秀”。真实的情况远非传说中那么振奋人心。 没有真金白银的利益,道义上再伟大正确的事,也没有哪个浙江商人愿意去干。即便是敬鬼神这样的事,也能折射出浙江人的务实精神。从木匠瓦匠供奉的鲁班,到龙井茶商信奉的陆羽,无不表明浙江民间社会对神的信仰是务实的。 浙江人大多不在乎名分,他们在乎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官人说私营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有资本主义的嫌疑,商人就说自己是集体经济的股份制。“先生娃,后取名”,1980年代以来流行于温州的许多民谚,清晰地洞见了浙江人的避虚就实的“实惠精神”。 他们的性格中看不到硬顶,显露的是遇到红灯绕着走的商业智慧。浙江多商人,多师爷,还多苏步青、姜立夫、李锐这样的数学家。但他们在经济利益面前,多的不是精心的算计,而是敢于冒险的勇气。从1980年代被逮捕判刑的温州“八大王”,到前几年在俄罗斯被劫杀的浙江商人,无论多么悲惨的故事,都未能阻滞他们冒险的脚步。 敢于冒险,就意味着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数数浙江30年来诞生了多少个第一: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执照;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条例;中国第一个改革金融利率;中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民主创新领域,浙江人也审时度势,搞出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自费登广告征集议案;第一个给农民工以选举权;第一个搞选举公证制度…… 敢于冒险,还意味着不怕视作异端。义乌人冯志来,一个兽医,竟然在中共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前25年,写出如出一辙的《半社会主义论》,送到中央办公厅,要求与毛泽东对话。这一点倒像永嘉学派的灵魂人物叶适,在陈朱理学被尊崇为正宗的年代,敢于反对重官抑私。 开放、贸易与全球化 通往四海的贸易格局,全球化的生意往来,正在开凿一条浙江的民主通道。 蝴蝶在此岸扇动翅膀,无数次的迭加,或可在彼岸引发海啸。西方人的“蝴蝶效应理论”在浙江私营企业主看来,一点都不深奥。尤其是做贸易的商人,生意上的全球化反应,早已让他们明白了这一点。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的阴影,很快就蔓延到义乌,压得经营中国小商品的巴格达商人乌云罩面,并迫使战火中损失惨重的几个温州商人铤而走险,乘隆隆炮火声而去。 飘洋过海,是浙江人将近千年的传统。当下,靠翻译、手势和计算器谈判的浙江商人,已把中国制造的货品从国际商贸城,输送到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自北宋年间,贸易就把造船业举国无双的温州人和海外捆绑在一起。世界贸易组织,更是一条填平大海的“船”,在中国尚未“入世”之前,就牢牢地拴住了浙江人。走在义乌,汉语、英语、朝鲜语和阿拉伯语写成的醒目的广告牌,一览无余地宣告了他们的全球定位。 开放格局下的全球化视野,不仅填写了巨额的外贸出口单据,还迎来了民主的人权观念。2000年以后,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尔玛,派员去义乌浪莎集团,检查工厂的安全设备,乃至职工的厕所。当记者们还不知“SA8000”为何物的时候,浙江人就从跨国公司的小动作中,明白了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渐渐懂得消防设施不齐备,非法使用童工,违反了世界通行的生意规则。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让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更早更多地懂得了民主和人的权利。 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浙江人享受了全球贸易的好处,也遭遇了“反倾销”的不愉快。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把习惯各自为战的浙江商人团聚起来,自行解散了“跑单帮”的货郎担模式。曾几何时,他们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越过边境,和洋人做生意。现在,他们不得不学习过去毫不熟悉的“世界贸易宪法”,组建起一个个民间社团,去应对应接不暇的反倾销、反补贴。同业公会这样的新名词,改写了他们的商业行为方式。在浙江,1万余非官方的新社团组织的次第登台,让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的成员惊讶不已。 自发扩展的秩序 浙江的民主,从来就不是官方有意为之的“计划性产出”,而是发轫于民间经济的自发无序的生成。 为什么握锄头、螺丝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终能和中国领导人拉在一起?你问从小就蹲在寒风中修鞋的南存辉,问年逾不惑才开始卖冰棍的宗庆后,除了哈耶克所说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还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在支撑他们吗?为什么一个资源倒数的省份,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坐上中国经济领域的第四把交椅? 读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你发现,“私有产权的保护增进了经济组织的效率”的解读,也可以套用到浙江经济奇迹的创造上。25年来,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壮大,浙江经济总量的递增,都与私有产权息息相关。近年,他们利用在人民大会堂的参政议政权利,一次次建言国家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并如愿以偿。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反复误读的概念,它的本质不过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他认为,在合作秩序的扩展中,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不可或缺。显而易见,浙江20余年的发展,满足了这个条件。 论功行赏,我们只能将这个丰功伟绩,归于自发的民间的力量。浙江的官员相对于其他省市,要开明得多,但他们不是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前,说他们是改革的维护者,远比称他们是维护者,更为贴切。 在浙江,纵使那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生死关头支持过改革的官员,也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确实提着乌纱帽,支持过冒当时制度之大不韪的“第一个”。凡此,无不和哈耶克申述的“扩展的秩序”相吻合。要“造福一方”,又无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他们只得任由私营企业像野草般疯长。尤其在GDP挂帅的时代,数字政绩使他们无论情愿与否,都得和私营企业主坐在一条板凳上。 在“政治文明”面世前,浙江地方官员对民主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创新,所持态度远不如当下积极。如果情势不明朗,他们的态度则趋向于暧昧,或者否定了事。义乌官员最初听说私营企业主捐资参选“村官”的态度是沉默。 所以,浙江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所推动的私有产权入宪,乃至渗透其中的民主价值观的萌芽,从来都不是决策者理性的制度预设,而是渐进式民主的成功,是“扩展的秩序”的胜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么美丽地逶迤在苍穹,不矫饰,不刻意。 谨慎的乐观 浙江的民主,未必会像熟悉历史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先是资产阶级为了经济民主挤向议会,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搞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局。但谨慎,的确是我们考量未来时须臾不可欠缺的态度。 2003年,讲述寡头疯狂攫取财富肆意践踏法治的《世纪大拍卖》和《寡头》,被介绍到中国,让一度艳羡俄罗斯跑步进入民主世界的人们感到颤栗。有人不放心地问,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吗? 我以为,当下还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表明中国会重蹈俄罗斯式寡头民主的覆辙。浙江乡村新富在村社民主中的表现,确实不容乐观。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民主化的路途上,也的确不是让任何人没有风言风语。 其次,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追求的只是经济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他们对私产在宪法中的地位的期盼,也只是希望摆脱窖藏白银的锥心之痛。 再次,他们的参政心态,不是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恢复型、补偿性从政,就是想壮大企业的功利型、经济性从政。即使少数人的民主型、公益性从政,也不会超越执政党的开放条件。 最后,我们再考察他们的精神背景和心灵世界。民主须求诸宪法,也须求诸内心。浙江私营企业主内心深处规约外在行为的文化理念是什么?是“和”的精神,是儒家的文化传承。“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浙江私营企业主讲究知恩图报,他们对法律的信仰,远远没有超越友情亲情、交情,他们做事的基础是彼此信任,而非契约。 凡此,无不提示我们,浙江的民主,未必会像熟悉历史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先是资产阶级为了经济民主挤向议会,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搞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局。 我的态度之所以有乐观的一面,在于我看到一个隐约可见的公民社会在浙江的初步生成。公民社会对于民主的意义,已成人类经验中的一个共识。依我的有限观察,多样性的社团组织,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念,正把浙江的市镇、类市镇的乡村,一步步推向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公民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知识分子,是催促浙江奔向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前者用金子搞定了公民社会的“基础设施”,后者用智识铺设了公民社会的“启蒙道场”。 虽此,谨慎,同样是我们面对浙江民主时不可或缺的态度。我们不能不分好坏地拥抱市场经济下的改革,让强势群体以改革的名义,瓜分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权益,最终让我们收获一堆民主的泡沫。过去27年,浙江经济列车以平均13%的超高速度向前疾驰。但辉煌的数据,并不能遮蔽转轨时期的重重“黑点”。 贫富分化是中国的难题,也是浙江的难题。人们大多知道浙江私营企业主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明星,却鲜有知晓穷人的孩子交不起学杂费而自杀的生活真实。尽管纳税排行榜上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一样耀眼夺目,血汗工厂却没有分崩离析。东阳农民反对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农民与政府非理性的冲突,暗示浙江的民主,还不完全是庶民的胜利。 客观地说,浙江的民主,不过是中国渐进式民主道路中的阶段成果。暴风骤雨的经济民主改革,赶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却未将小农经济的思维从浙江人的思维中删除。宗族观念,族姓矛盾,官本位,这些我们不喜欢的旧思维,还在支配着一部分浙江人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生返回浙江老家,参与邻里纠纷并在大打出手中酿出命案的悲剧,折射出的民情,与我们鼓吹的公民社会背道而驰。 正如我们不能仅凭美好的轮廓,虚饰浙江民主中的惨淡印记,我们也不可以用沮丧的个案,摧毁我们对浙江民主的美好期待。我们需要的是对方向的肯定,对方法、技术和细节的改进。 对中国民主模式的喻示 假如浙江经济的今天就是落后的“小兄弟”们的明天,浙江的民主就有望成为中国民主的先声。具前瞻性的浙江的民主,喻示那些考量中国民主模式的人们:失去民主的普适性标准,我们就会堕入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经验于不顾,以美国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现实,就会陷入悲观的不可知论的迷途。 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经常发现,浙江民主制度创新的个案,正在被中国的其他省市复制重塑。温岭的民主恳谈,非但被中国其他地方复制借鉴,还启发研究民主的学人去辨析,去传播,从学术途径影响当政者,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 温岭的民主恳谈,在破解乡村社会紧张的干群关系这一难题上的价值,非但被少年时通过读书走出浙江的中央编译局官员俞可平,授予“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奖”,还把不过20年历史的“协商民主”这一西方民主概念引入中国。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我们当然不能说,人民政协制度是浙江民主恳谈影响下的产物,但我们或许可以揣测,浙江民主恳谈有望影响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的生命力。 假如我们相信,浙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领头雁,它的今天是落后于它的“小兄弟”们的明天,我就可以认定,浙江的民主就是中国民主的先声,具有旗帜性、前瞻性。 浙江民主的前瞻性,引领了中国的实践,也受制于中国民主改革的整体水平。毫无疑问,浙江的观念,已经超越了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但平均数治理的格局,决定中国民主改革的步骤,不太可能随着浙江的变化,整体推进。因为,全局性的宪政文化水平,与浙江“民情”不相匹配。浙江官方高级智囊卓良勇拿理论创新举例说,“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理论难以正确解释浙江改革实践所遇到的大量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知行不一的困惑,严重影响政府行为和社会精神气质的提升。” 浙江民主最终导向何方?保守的?激进的?渐进的?西方式的?亚洲式的?所有的追问,都仰赖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变迁。虽然劳动价值论这些挑战传统意识形态的调研从浙江开始,私营企业主入党也是从浙江破的题,但答案的揭晓,最终都要等待北京来宣布。某种意义上,浙江的民主创新,就像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一方试验田。 我在浙江的见闻一再提醒我:失去民主的普适性标准,我们就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经验于不顾,以美国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现实,就会陷入悲观的不可知论的迷途。看温州人大联姻温州三家媒体,共同监督“一府两院”的案例,对照西方的媒体独立、议会主权,我们对温州人大和温州媒体的评价就会非驴非马。 同样,如果我们以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会得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纹丝未动的结论。设若我们以此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政治稳定从不改革,中国民主的道路将曲折多变,甚至会误入歧途。 在亲近浙江民主的日子里,我时时感觉到民主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捕捉浙江民主中的细节,察看知识分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乡村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逊位于经济权威的事实,上层建筑改革和理论创新落后于民主实践的亦步亦趋,知行不一的茫然,都显示民主模式的选择不能是教条主义的纸上谈兵。 当下,我们需要商讨的议题是如何推进法治。我们为悬崖边舞蹈的民主从磐石的缝隙中生长而欢呼,我们鼓励一切向上的力量,在法治的框架中,驱除民主的敌人,迎娶民主的普适价值。但,判断哪一种模式的民主,将成我们的未来,为时尚早。 我不相信有些人所说,浙江的民主,会把中国的民主过渡到美国的版本。尽管浙江私营企业主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在全国最高,他们也确是促进民主进步的一支力量,但他们的推力究竟延伸多远,尚不得而知。 我对“后儒家民主”将成中国未来的假定,同样心存疑虑。12年前,新加坡老一辈政治家李光耀推动亚洲国家领导人发布了一个“亚洲价值”的声明,宣称人权并不局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解。我总觉得,“后儒家民主”和“亚洲价值”一样,都是含混不清的说辞。和睦家庭,尊重长辈,善待他人,热心公益这些有什么是亚洲独有的价值呢? 坦率地说,除了笃信民主会在更大范围内普遍到来外,我对浙江民主的考察,并未让我洞见中国未来的民主模式。如果我们信仰民主仰赖于“扩展的秩序”这一宗教,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建设性的姿态,认真地做,耐心地等。 (作者新书《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由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出版)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时评 > 正文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市黑马:今日牛股! |
| 开家麦当劳式的美容院 |
| 名人代言亲子装赚钱快 |
| 销售排行榜:投资必读 |
| 06年暴利项目揭秘 图 |
| 小女子开店30天暴富 |
| 犹太亿万富翁赚钱36计 |
| 韩国美味 势不可挡 |
| 100万年薪招医药代理 |
| 泌尿顽疾——大解放! |
| 最新疗法治结肠炎!! |
| 治气管炎哮喘重大突破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治高血压获重大突破! |
| 警惕高血脂!脂肪肝!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