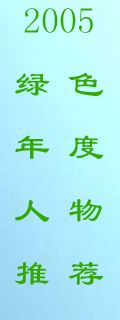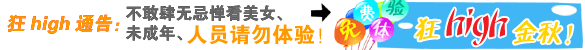|
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消费,伴随着的却是更大的压力和更少的幸福——这是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蔓延的一种精神疾患。
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定量测度幸福的增减,但幸福感的日益萎缩应该是今天中国人普遍感受到的一个经验事实。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财富狂欢之后,中国社会几乎在刹那间就跌入了一种集体抑郁。于是,由财富而生的压力、过劳、焦虑,乃至恐惧都齐齐翩翩而至。撇开现代性所必然带来的精神问题,我们可以将今天中国社会这种特殊的精神流感称之为“财富抑郁症”。简单的定义是:由于对财富的过度追求所导致的一种普遍的不幸福感。
从一个极端匮乏的社会起步,财富以及对财富的追逐变成了中国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尤其需要加以提示的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被消解并崩塌之后,财富实际上变成了官方与中国民间惟一的交集与共识,并成为越来越疏离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官方的惟一黏合剂,如此,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作为中国转型中的一种新型的大众意识形态被牢牢地确立下来。在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竞争的市场中,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在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都受到了蓄意的鼓励与持续的强化。财富,不仅成为衡量社会进步(以及改革)的惟一标尺,也成为个人成就甚至身份确认的惟一标尺。于是,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不仅作为一种动力在推动改革,也同时作为一种裹挟与强制的力量开始锈蚀我们的公共及私人生活。这种从未经过任何批判与稀释的新型意识形态外化为官方战略就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将“发展”矮化为“经济增长”继而矮化为更加狭隘的“GDP增长速度”(这实际上也是今日已经根深蒂固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意识形态根源);而体现在私人领域则变成更加粗鄙的“钱多就是硬道理”,就是将“钱”与个体的生命意义进行一对一的确认。我们被粗暴地告知:我们无需追问发展的含义,无需追问制造GDP的方式与代价,无需追问获得个人财富的手段。在这种新型的改革意识形态中,我们一直被迫接受这样一个神话:增长越多,财富就越多;财富越多,幸福就越多。然而,在经过二十多年冲刺般的财富赛跑之后,这个逻辑简单因而也就特别容易深入人心的神话开始逐渐露出了马脚。人们如梦初醒般地发现,增长并没有与财富同步,而是越来越背离,对财富的追寻也没有相应增加个人幸福,而是带来更多的压力,更多的沮丧。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这个“发现”都是相当不幸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弥漫着的普遍失望和挫折感。而这种普遍的失望和挫折感正是中国人集体陷入“财富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基础。更为不幸的是,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惯性的文化, “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就像一种精神鸦片,已经彻底地奴役了我们对财富的理解与想像力。换言之,我们很难从这种毒品中抽身自拔。在这个意义上,财富所带来的压力、焦虑,进而抑郁在中国社会可能还仅仅是开始。
关于财富本质的追索与财富本身一样古老。一种我们可以勉强接受的关于财富的说法是:所谓财富就是那些可以增加我们主观效用的东西。问题在于,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一切可以增进主观效用的东西都是稀缺的。这既是财富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类一个与生俱来的被给定困境。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为这种稀缺性付出某种成本,一旦这种成本过于高昂,比如导致了过大的压力,牺牲了过多的闲暇,增加过重的焦虑甚至失望,带来了过大的外部性,那么,财富带来的效用就是“负”的。这种情境,就是我们在定义“财富抑郁症”中所指称的对财富的“过度”追求,而其带来的必然是财富对幸福的压迫及消解。在目下中国,当财富被经济学家以及政客们粗暴地概括成“GDP”甚至纸币的时候,财富对幸福的消解及压迫则尤其深重。
容易理解,作为社会之一员,在中国转型中荣耀加身的中国企业家阶层并没有因为他们成为财富竞赛的相对赢家而幸免于“财富抑郁症”。其中原因在于,在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财富之后,财富对他们的效用正在迅速递减,而在一场更高规格(与同类人)的财富竞赛中,他们成为“输家”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成为“赢家”的概率。当然,他们可以加入消费的奢侈比赛(这是在部分中国企业家中相当流行的一种风尚),并借此向大众炫耀并表征他们的身份、地位,从而增加个人的幸福感。但毫无疑问,这是财富的流亡,而绝非精神的解放之路。
企业家是一面镜子,他们的“财富抑郁症”暗示的是,中国社会对财富的一种普遍困顿。在乐观主义者看来,这可能是中国社会一次深刻精神转型的前兆。而在我看来,我们更加需要警惕的是:在还没有开始救亡之前,中国社会就在精神上发生一次突然的“过劳死”。逃亡还是救赎?这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