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经济学的科普化生存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18日 21:55 南方人物周刊 | |||||||||
|
 薛兆丰,青年学者,深圳大学理学士,现留学华盛顿,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1997年建立网站“制度主义时代”(www.StevenXue.com)。2003年出版文集《经济学的争议》。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
——不断有人指责我专横独断,指责我不宽容异己,指责我好斗。我将这些都看作是赞扬。 ——学术的自由竞争是残酷的。我虽然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但我不能不拼命地批驳你的观点。假如我失败了,那么我的努力将立刻转化为对你的观点的信服。 ——我们要让别人说话,要始终让别人说话,但仅此而已,更多的仁慈和宽容都是有害的。 这是薛兆丰《正确理解学术自由竞争》一文的开头,带着尼采式的咄咄逼人和唐·吉诃德般的热血沸腾。 他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并挑起论战的高手,他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一书出版不久,马上就有经济学者站出来写了“对《争议》的争议”,旋即又有另一位经济学者站出来写了“对《争议》的争议的争议”,力挺薛的观点。据薛说,这两位大学教授皆与他不相识。他抱着感谢捧场的态度饶有兴味地关注了这场论战,并遗憾辩论没有吵得更热乎、范围更广一些。 “很简单,两个人对吵引起传播效果,显然比两个人的各自吆喝要更好。在网上也是如此。” 不动肝火的论辩大王 这个国内最早的论坛版主之一,1995年底,就在深圳万用网开辟“新闻组”(newsgroup)接触“网上讨论”,并开设“经济学”栏目,只是当时尚未有“版主”一说。1996年初夏,深圳数据局推出一个“BBS”站,薛兆丰在那里担任“经济学”版的版主。今天这个版虽然人气凋零,但仍可从颓垣败瓦中推想出当时激烈场面。 “论坛必须有人挑起话题,针锋相对,兵戎相见,引得看客忍不住要开口参战,这样才会热闹。”当时为了贴点上乘货色,薛花了不少钱请人把科斯等人的文章敲入电脑。远在泰国芭堤亚度假,也冒着炎热,乘车到老远的网吧看文章。在网友争论中,薛兆丰惊讶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的想法是那么不同,“如果不是这段经历,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冲动去写文章、写专栏。” “在网上表达任何观点,都可能会引来四面八方的攻击。要写出经得起考验的文字,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写以前,自己先尽量攻击自己——将所有可能的攻击都考虑在内,然后挑出有代表性的给予回答。那些低级的攻击,则忽略,也算是卖个破绽,引诱别人来过招。大大咧咧地上阵的人总是有很多,我再手起刀落,那种快感,只能意会。”他后来写专栏一稿要修改七八遍,出声朗读并反复推敲,好习惯由此而来。 他不在乎对手说粗口和人身攻击,有人大骂他,他感到兴奋,朋友也会第一时间通报。薛兆丰把这当成一种赞扬——说明对手无力还击,才出此下策。 他只动过一次肝火。一次他在宣传“交易”的好处,一位网友很不客气,要薛出个价,他要买薛的女朋友去过瘾!10秒钟以后,薛兆丰的怒火平息下来,写了张回帖,告诉对手,自己并不拥有女朋友的产权,无权卖她。“别看他粗鲁,他是有观点的,我也郑重地回他。这样的帖子,删了就是版主出洋相;摆在那里,则大方得体。” 在美国大学作为经济学教科书的阿尔钦(Armen Alchian )的著作,中文译本的翻译者即为薛兆丰,阿尔钦对薛颇为赞许,并称薛是其工作伙伴。 阿尔钦对薛的翻译给予鼓励,并告之,该书的俄文版本和西班牙文版本也在同时翻译中。4年后,薛的中文译本面世以后,另两种版本仍未完成。 阿尔钦——这位93岁的经济学专家童心不老,充满好奇,乃是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第一个使用email之人——不懂中文,他用一种十分特别的方法检验翻译。他将薛的中文译本交给UCLA的一名中国学生,命他再由中文译回英文,从还原程度来考量翻译中是否有失真或谬误。结果令阿尔钦十分满意,该译稿因此成了阿尔钦“钦”定的中文译本。 要把生命用得最好 薛兆丰幼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他喜欢看到工作成果成为实物。但是很快,他放弃了这一理想,转而想当一名精神病医生。这个曾经腼腆害羞的少年,开始意识到,物质的发展并不能给人带来太多幸福感。有能力的人可以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而精神病医生则可以帮助那些无力追求幸福的人们。高考前,他填报了两所重点医科大学。这个在父母的宠爱和严格管教双重高压下的孩子,一心想通过高考离开家庭,走到外面的世界去。 结果,考分高不成低不就,他入了深圳大学,因为离重点线差一分,他只能读不那么“重点”的数学系——开放伊始的深圳,“国际”打头的专业最吃香,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连中文系的名称都改成了“国际文化传播”,惟有数理化不“国际”——在大学里,薛兆丰重新修正了他的理想。 “我一直想,要把生命用得最好,但如何最好,得有个计划。”人类的大部分灾难是思想造成的,而非自然造成,人祸远远猛于天灾。未来还是白纸一张的薛兆丰,开始设想:有意义的人生,乃是要创造好的思想,如果不能,则传播好的思想。再后来,他又把思想,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深圳大学是特区开放而建的高校典型,北大清华的教授咸集于此,图书馆所有图书一律开架,而且开放时间之长,为当时亚洲所有大学之最。薛兆丰大学受益颇多之事如下:与女朋友共同读书,与室友尹忠东吵架。 红袖添香夜伴读,学者之福。虽然女朋友后来没有成为太太,但薛兆丰依然在博客中提出,大学的一项重要功能便是恋爱,越早恋爱就越容易心平气和,越不会大惊小怪。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对安心用功有益,因为不必再为挑选、追求、竞争、乃至舞会操心了。 与尹忠东吵架也是有益的,因为历史雄辩地证明,凡值得尹同学与薛同学大吵特吵相持不下之事,往往尹是对的。 尹建议薛在辩论中不要采用比喻手法,最终彻底影响了薛的思维习惯和文风;尹提出“人的思想是五花八门的,而人的行为却是高度一致的”,一直让薛铭记心头,最后还成为撰写投票经济分析论文的契机。 比复杂更难的是简单 薛兆丰是广东梅州的客家人,母亲是中学英语老师,父亲是大学中文教授,但他在文学上的师承,却是来自朗诵古文及背诵粤语流行歌曲的歌词。 他从小在父亲那里只学到两件事:一是写毛笔字,二是父亲在写文章时,他凑去看,被父亲教育说,别人写文章的时候在旁边看,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他的写作风格,是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老师引导的,他们鼓励他用简洁的文字表达思想,因为初中的语文老师只讲粤语,所以他当时背诵的古文,一概是用粤语。粤语与古音更接近,而且有九种音调,富有韵律。直到今天,他写专栏都要先打印出来,自己边读边改,力求简单好懂,朗朗上口。他太怕别人不爱看了,报纸上文章满满当当,文章若不吸引人,眼球那么一转就可以忽略过去,比电视换台可方便得多。 所以他的经济学专栏,深入浅出,连外行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其实简单的文章更难写。”他硬性规定自己:在专栏中不得使用经济学专门术语,所有含“把”、“将”的句式都要改成最直接的动宾结构……后来,他发现,其实大多数学术论文都根本没有必要写得那么艰深难懂,在经济学术语里,除了“边际(marginal)”的概念,他找不到其他可以替代的词以外,其它专业词汇,几乎全部可以用浅显的方式来表达。他假想的专栏读者,是“思维方式没问题,但是没受到经济学专门训练的人”。 他最喜欢的一篇经济学短文,是秋风翻译的《I, Pencil》(《铅笔的故事》),那是读来简单、但寓意深湛的经济学经典之作。他特意去把自己的车牌号码,申请成“I PENCIL”,并得意地说:“只要是好的经济学者,在路上看到这个车牌,就知道车里还有另外一位好的经济学者。” 薛兆丰爱好单纯,最经常的休闲娱乐,就是在家里踱来踱去,或者洗澡,一把澡就可以排遣许多郁闷。再有,听音乐,兜风,哄自己从小抱大的干女儿玩,去朋友家聊天、蹭饭。“去朋友家里什么都可以由人招呼,你就坐在那里不用动了。”他爱吃,给什么都吃光,因此是受欢迎的食客。然后看电视,侦破片,或者烹调频道。 他听说画家林风眠文革期间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他哭过;他听说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红卫兵打断,他哭过;他看了《南方周末》的报道——《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也同样失声痛哭。他在博客里写道,“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用不着复述他们的遭遇,用不着指出谁是罪魁。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 这个背负着“好斗”之名的青年才俊,生活中其实心思细密,体贴认真,是标准的gentleman。社科院一访问学者来到华盛顿,他见对方是个女孩子,便主动邀她出去吃饭。该女素闻薛某桀骜难处,一餐饭吃得战战兢兢,薛兆丰先行吃完,她马上起身,表示不敢耽误他的时间,愿把自己剩下的打包回去再吃。为了让她能安心吃饭,薛随即又给自己点了一份,陪她继续吃! 在我们的电话采访中,他间或停下,问我:你是否要去喝口水?提及任何专业术语或人名,他马上记下,列了个长长的清单在mail里发我参考。就连给杂志提供的照片,他都在旁边非常nice地注明:9兆,下载可能需要20分钟,谢谢。 聪明的用处并不很大 人物周刊:秋风评价您的学术来源是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这两派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您学术观点的成型过程如何? 薛兆丰:我的学术观点主要是三个构成:一是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在美国直到80年代,经济学博士考试就是要弄懂阿尔钦价格理论一书的所有问答题;二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即市场过程中的变动和互动是无数行为汇总的结果,决不是在失衡与均衡两点之间的简单来回。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控制经济汇总的巨大变动,黑板上的曲线更解释不了;三是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研究非私营机构的行为,我的导师之一比奇(Peter Boettke)即持这一观点,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也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在1986年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公共这一块存在着巨大的盲区,人们寄望引入政府来纠正市场的失败,但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引入了政府的失败。 人物周刊:您曾引用“我们已经走上改革的道路,但是还不知道这条路往何处去。”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最大问题或危机是什么? 薛兆丰:一是黑社会化。产权明晰的过程太过漫长,产权从国有到私有,中间的模糊过程太长,因为无论是物质资源、人际关系、或者组织架构,中间都有潜在的巨大的利益,这方面的法律如果再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那么黑道的规则就会建立起来。 二是短期行为。我们的GDP即使跟美国相比起来也是蒸蒸日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在耐用品的建设上却远远不够,经济是如此,学术也是如此。 随便举个例子,国外把教授养在那里,每天飞来飞去,每天无数的演讲到处都在发生,短期里看一点用都没有,但是10年、20年、30年地积累下来,就很不同了。我曾经计算过,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获奖需要多长时间,平均需要25年——最长的是哈耶克,他用了整整40年,最短的也耗费18年。中国现在有能够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吗?抛开甄别率差这样客观的原因,仅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如果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希望的人选的话,那么25年也不会有了。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计算?你有夺取诺贝尔奖的野心吗? 薛兆丰:只能说,没有了。任何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他的动机首先是学问的乐趣,至于奖,那只是一个副产品。 人物周刊:您在文章中戏称,您经常被老师骂“蠢”,“蠢到死”,“蠢得像猪一样”,这是真事吗? 薛兆丰:那是他的口头禅,但我觉得我周围比我聪明的人的确多得很,问题是聪明的用处并不是那么大。 举例来说,法拉利、奔驰,其性能比桑塔纳肯定要好多了,但是如果是作为的士只在城市里开,区别其实不大。我心算很慢,在美国通常要付给服务员15%的小费,我就算不过来,常常需要别人代劳,或者干脆给20%。蠢一点有什么关系呢,最多就是,别人10分钟能解决的问题,我可能需要一天,发表论文慢一点是不要紧的,要紧的是,论文里所包含的学问。 聪明不重要,重要的是懂得衡量轻重,所以要看最好的书,听大师的观点,观察大师们所选择的轻重。 人物周刊:您心目中,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有几人?可以展开辩论并成为对手的有几人? 薛兆丰:现在更多的是经济学人,而不是经济学家。如果说“经济学家”是我们小时候的标准,好像“物理学家”是指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标准,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除了张五常,我看不到别人。当然这不代表他的观点都是对的,比如我不同意他对汇率和利率的看法。但他在经济学领域里有过无法绕开的成就。有些人你可以说他错,但他在那里。 至于可以成为辩论对手的,那就太多了。经济学不是柔道,段位不同不能比武。在我看来,只要思维正常,彼此掌握的信息有不同,就可以形成交流或论辩。能指导我的人太多了,能教育我的人太多了。 人物周刊:您理想中的学术自由环境是怎样的?中国经济学离这个理想还有多远? 薛兆丰:在美国,同事之间的学术批评很尖锐,但是他们非常疼学生,无论学生提出多么愚蠢的问题,他们都说,啊,这个问题非常好。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同行之间则一团和气。 我虽然生长在教师家庭,但是我觉得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方式,是错的。他们太严格了,连到楼下去玩一会,都要先回答一连串的问题。我的创造力和好奇心,受了很大的压制。直到初中,我还是一个非常害羞和自闭的孩子,小升初的英语考试中,我的笔坏了,没法写,我都不好意思站起来要求借一支笔。 布坎南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别人问他,他心目的好老师和坏老师分别是谁,他说,最好的老师是奈特(Frank Knight),奈特自己虽然没有得诺贝尔奖金,但是他的弟子中有五六个人获奖,他总是非常鼓励学生,而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则恰恰相反,总以驳倒弟子为乐。布坎南说,每次我在弗里德曼那里受了挫折,便马上要到奈特那里去寻找安慰。 同行之间、同事之间的学术批评,国内的高校没有这样的批评机制,面对面的批评几乎没有。 人物周刊:您的家庭观? 薛兆丰:男女平等而不相等。男女有别,分工合作。 我很讨厌政治意义上的所谓男女平等,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马上要辞职了,据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女性在硬学科上的总体成就低于男性。这算什么?也许女性在艺术领域比男性强更多呢?在家庭中也是如此,女孩就该有女孩的样子,如果女孩比较适合做家务,那就让她做家务。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吗? 薛兆丰:Anything worth doing is worth doing well.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任何值得你去做的事情,都值得你去做到最好。但这话不对,如果我将来有孩子,我要教给他,学习不用学到最好,成绩不用考到最高,因为还要玩。我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不要做到最好,只要做到正好。 (实习生朱宝对本文亦有贡献)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管理 > 正文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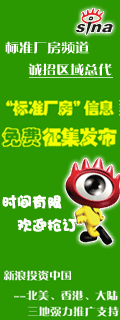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市黑马:今日牛股! |
| 小女子开店50天赚30万 |
| 介入教育事业年赚百万 |
| 新型建材 月进10万 |
| 女人钱,怎么赚 (图) |
| 2万元投入月净赚20万 |
| 韩国亲子装?日赚30万 |
| 我爱美丽招商!加盟! |
| 品牌折扣店!月赚30万 |
| 泌尿疾病!特色新疗法 |
| 拒绝结肠炎!! 图 |
| 皮炎!湿疹!荨麻疹!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糖尿病——重大发现! |
| 高血压!有了新发现!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