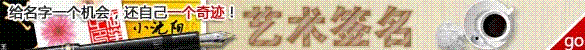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为金融危机开药方
本报驻美记者 宰飞
全球经济有多糟糕、人们对未来有多焦虑,看看最近一次媒体采访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过程也许就能知道。
虽然不在政府任职,但克鲁格曼已经成为最热门的经济人物。纽约外国记者中心组织媒体对他的集体采访尚未开始,气氛已经点燃。
外国记者中心通常会不定期给注册的外国记者发送电子邮件,通知活动安排。但是这次,除了按惯例在几天前预告采访时间地点外,在采访的当天,外国记者中心又给记者发来额外提醒:“参加这次活动的记者将非常多,会后可能没有一对一的采访机会。如果要携带摄像机,请提前到达。” 记者提前了15分钟到达,发现会场后排已被摄像机堵得严严实实。
下午2时,克鲁格曼准时出现。“噼噼啪啪”的快门声霎时响成一片。没有寒暄问候,克鲁格曼开门见山:“我没有准备演讲稿,今天只想讲金融危机,开始问吧。”记者提问也是直奔主题,第一位提问的中国台湾记者问了一般采访结束才提的问题:“请给我们一些走出金融危机的建议。”
与其说是记者招待会,不如说更像“名医坐堂”。各国记者争先恐后向这位难得一见的“大夫”请求治疗“疑难杂症”的良方,希望克鲁格曼的只言片语能够指点自己的国家走出这场危机。
中国记者问“中国如何避免经济风险”,东欧记者问“匈牙利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应当怎样利用IMF的资源”,南非记者问“经济实力较弱的非洲国家应当怎样救市”,巴西记者问“金砖四国如何增加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
面对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问题,克鲁格曼都要给出处方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难怪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克莱因说:“克鲁格曼变得越来越直率。他说的很多东西可能是错的或者未经考虑的。”
不过,记者们喜欢的正是克鲁格曼的直率。每个拿到话筒的记者似乎都要用足机会,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有两个问题”。整个采访过程,记者席上举着的手自始至终未见减少。下午3时,约定的一个小时招待会截止,主持人抱歉地说“可能再来一个小时也不够。”
(本报纽约4月15日电)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