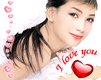|
本报记者 李明伟 上海报道
“因为一个病就可能让他倾家荡产,一个病就可能让他几十年的积累化为乌有。”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语气沉重:在5、6月份的调研中,陈走访了中部6个省,发现有35%~40%的人脱贫后,因病重新返贫。
9月5日,前一轮医改讨论热潮中的两大主角——国务院和卫生部的两位人士同时现身中欧商学院“2005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一位是陈文玲,她强调自己不代表所在部门,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她特殊身份的重视;另一位则是被中欧副院长张维炯称为“卫生部部长高强委派的专职代表”的卫生部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二处副处长雷海潮。
两人一前一后率先在论坛发言。
陈文玲认为新一轮医改必须要各方面联动、一体化设计、共同推进,其中尤其要做到三个分离:公益性医院和盈利性医院分离、逐步实行医药分离和管办分离;雷海潮则透露,卫生部联同几个部委已经起草“关于城市医疗服务体系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并几易其稿,目前正报国务院待批。
二人都认同,“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是政府的责任”,有所差异的是如何做到这一点。陈文玲提出:政府应该集中财政拨款办好公益性医院;雷海潮则认为:今后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公共财政对卫生和健康方面的投入,来扭转政府在卫生投入方面比例不断下降的局面。
“看病难,看病贵”,归根到底,是“钱”的问题,这些钱到底应该“谁来出”“出多少”正在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
支出比例:个人剧增 政府急减
依据雷海潮的研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2003年,我国每年人均卫生支出总费用从约20元增加到500元,增长了24倍;1978年时,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只有3%,到2003年达到了6.1%,算下来,已经超过7118亿元。
这说明老百姓兜里的钱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卫生医疗支出,尤其是1995年以后,这种支出增长超过了人们收入的增长幅度,雷用“与GDP的弹性系数远远大于1”来说明这个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能更加清晰地看清楚老百姓所承担的“增长压力”。
卫生总费用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居民个人花费、公共财政支出的花费、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花费。雷海潮发现,居民个人花费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占卫生总费用的20%左右,到2003年,这个比例飙升到了56%;相对应的,政府的卫生支出则从1978年的超过30%下降到了2003年的17%,余下的社会花费也是从当初的近50%下降到了2003年的27%。
这些数据说明,在过去20多年里卫生费用的增加中,多数费用的增长是由老百姓个人承担的,雷海潮据此表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样看来也不难解释。”
一直以来,我国从来没有放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并为此发展了城乡医疗保险,但是从现状看,我国医保所覆盖的人群“仍然非常有限”。1998年和2003年,卫生部有相关部门连续两次开展以入户为基础的家庭卫生服务调查,从人群看,城市里没有任何保险的人群比例反而在上升,从1998年的44.1%扩大到了2003年的44.8%,农村有所下降,从1998年的87.4%下降到2003年的79.1%,但是仍然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比例。这再一次说明,老百姓看病基本上是自己掏腰包。
另外,即使是被医保所覆盖的人群,也面临着一个问题。1999年以来,基本医疗保险方面的资金沉淀过多,据卫生部计算,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六年以来,每年资金的沉淀率高达24%~36%左右,2001年达到36%,这意味着参保职工100块钱的资金有36块钱在帐户当中沉淀下来。在当前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下,却出现这么高的资金结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公益”的异化
医院等医疗机构的收费越来越高,似乎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因素。
当陈文玲在会场上尖锐的指出:性质上是“公益性”的医院却“95%以上都变成了盈利性的商业运作模式”时,全场一片肃然——这是中央政府部门官员第一次这么公开、严厉地给医院运作模式定性。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国家现在所办的所有医院都“仍然是公益性的”——它们可以“占地不花钱、不交税,政府仍然给财政补贴”,除此外还得享三大财源:一块是药品收入,前几年最高时达到70%以上,这几年经过一系列调整还在55%以上;另一块是日益增长的高额检查费,这已经开始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第三块是高支耗材,也成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
依靠这些支持和收入,医院旧貌换新颜,陈文玲感叹:“原来医院大楼都是最破、最旧的,现在很多很多地方的医院大楼已经和金融机构的和一些最富有的行业相媲美了。”
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一直在研究医改,他直指这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异化”,而其根源则在于医改本身的“异化”——“改革的宏观目标出现偏差,不是定在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是想通过改革来为政府减轻负担,减轻财政压力。”
曾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现任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民营医院分会主任委员的于宗河对此也有同感,他清晰地记得医院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创收”之路的。
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明确提出要“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紧接着,一系列政策和来自医院自身创新的“补偿机制”开始不断涌现:分解收费、“以辅养主”、“以药养医”、承包科室、兴办“院中院”,等等,形式不一而足,但宗旨就一个:创收。
“创收”还表现为有意的隐性“浪费”。曾任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特别代表的陈洁教授记得这样一个场景:一次陪同世界银行代表到医院考察,发现一个小孩一边在吊盐水一边又在吃苹果,世界银行代表大为惊异:“能吃苹果就表明能摄取营养,不需要吊盐水。”
经费补偿机制
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陈洁教授认为,医院走上“创收”的路子不能全怪医院,归根到底还是“经费补偿机制出了问题”。于宗河也认为:下一步医改的关键在于“用什么经济政策去支持”,“归纳到一个问题,就是筹资机制”。
那么到底这已经超过7000亿元的卫生总费用应该谁来出、怎么出呢?一种观点认为主要还是要由政府承担起来,“老百姓已经交过税了,从道理上讲不该再给一分钱”;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通过各种资本大量兴办医院来形成竞争,从而实现降价和提升医护质量。
于宗河偏向前一种观点:“还是要以政府为主导,动员全社会资源,拿出GDP的5%~6%就够了。”于认为,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企业改革,不能也是搞“市场”;医疗事业也不同于房地产市场,不应该成为“暴利的”,即使是民营医院。
但是于也很清楚地知道,国家财政不可能支撑这么大盘子的卫生费用,算下来国家将比现在多支出5倍,这是不现实的。
与相关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都有接触的于宗河设计了如下的解决思路:
第一,个人支付20%。于认为,为了防止“小病大治”等浪费,让老百姓承担20%也有一定道理,政府需要做好宣传和解释;
第二,政府在现在17%的基础上,逐步将比例提高到20%,而这个拨款不光来自中央政府,各级政府都必须承担一定比例,除非贫困地区;
第三,医保在现在24%基础上,随着医保面的拓宽和商业性医保的发展,可将比例逐步提高到30%;
第四,剩下的30%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通过加强管理减少浪费,以前的测算是在卫生支出中将近20%是以乱开药、乱检查、“小病大治”等方式被浪费掉了;另外10%则通过社会捐助、慈善事业等方式来筹集,也可引入民间资本兴办盈利性医院,其赚钱的部分通过税收方式截取并转回公益性卫生事业部分。
“有退有进”的路径
汪亮的观点与于宗河类似,他提出了基于现实状况的“有进有退”的改革路径。
其提出的三个概念和相应承担者是:
第一,“公共卫生医疗”,这是广覆盖的、每个居民都可以享受的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由政府集中财政承担全部投资并委托管理,其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目前所有的社区医院、部分二级医院、部分三级医院。
所有的社区医院构成一个有效的前沿卫生网络系统,承担常见病防治、妇婴保健、传染病防控等;二级、三级医院大部分逐步退出,由社会来接手,但是政府依然要办好几家必须的二级、三级医院,比如每个地方一家综合性医院、几家专科性医院(如精神预防中心、妇婴保健院)等,与社区医院形成转诊机制,从而实现小病到社区医院,大病可转诊的体系。
第二,“公益性医疗”,由慈善机构来投资并运作,不以盈利为目的,尤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卫生救助。
第三,“经营性医疗”,由社会资本以市场方式运作,满足基本医疗需求之外的那些个性化、特殊性的需求。对于这部分医院所产生的利润进行征税,并把税收返还到第一部分的公共卫生医疗事业中去。
汪认为,那些航运、邮电、铁路、防治等行业性医院,实属“重复建设”,应该改制,交由社会来承办。
与陈文玲的观点相同,汪认为医改的重要保证是要实现“管办分离”,那些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的管理要同步改革,必须打破卫生部门既管人又管资产导致改革难以推进的现象,路径就是将这些资产交由国资委管理,卫生部门承担市场环境的建设和维护,而在医院的具体管理上,则由国资委公开招标,交由那些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经营管理。
陈文玲在发言时指责:“一些地方的卫生部门实际上还是国有医院的总院长,还在代表医院招标、采购,代表自己原来所隶属的医院,甚至维护某些既得的利益。”
于宗河认为,以前医改“不成功”的关键还在于“落实不好”,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类似问题已经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中央政府于1996年时以空前档次和规模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大会,明确了卫生事业的“国家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公益事业”性质,并具体提出了40条决定,“如果这些决定都得到落实,就不会有今天这些问题了。”
陈洁也建议,新一轮医改,如果能成立直属国务院的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委员会,以此来领导和协调改革,“可能效果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