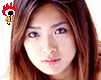稻谷第一县四年之变 新三农政策下的湖北监利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07日 22:38 南方周末 | |||||||||
|
 监利,有中国“稻谷第一县”之称,被认为是反映“三农”问题最典型的农业县。2000年2月,一封从这里直接寄给国务院总理的挂号信,一度成为检讨本地农民生存状况的蓝本:农村青壮年流失,粮食生产亏损,粮田抛荒,农民生活极困窘困苦……典型事实中所蕴含的中国“三农”问题症结,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自此以后,关于“三农”的新政策和新措施不断出台,从“税费改革”,到“粮食流
这些变化,如何发生?如何演变?记者四年后再次来到监利。 种养结构调整之后 这是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曾描述过的村庄: 时间:2000年春节,正月初四。 地点: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角湖村。 不管是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统统塞满了人。我开着的桑塔纳也被农民拦下,车里一下子上来了5个农民。一个四十岁的农民说:他家去年种了40亩地,一家三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忙了一年,交了各种税费和两万多斤粮,自己只剩下3000斤谷子。谷子收完了,老婆也累倒了,住院7天花去了2000多元,把自家的粮食卖光了,还借了2000斤。……禾苗刚栽下,干部就来收钱,每亩地200多元,1分不能少。闹不好就关人罚跪。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仅580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着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税费还差着近一半。(相关报道参见本报2000年8月24日报道<a href=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08-26/120802.html class=akey target=blank>《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a>) 2004年“一号文件”简介 2004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了“一号文件”,其中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这份被人们称为“高含金量”的文件,将着力点放在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上,抓住了多年来农民收入最难提高的部分。《意见》强调,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意见》确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四年时间过去了。2004年9月,记者踏进今天的角湖村。 村子静悄悄的。记者见到的是连片的水塘,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泥腥味。稻田,满打满算还剩300亩。 几年前,村集体已经进行了农田重新发包,在当时不少青壮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未离家的壮年村民和老人分包了剩余土地,从十余亩到近百亩不等。“ 2001年开始,监利县提出“以工兴县,以水富民”。调整涉及面积5万多亩,都是成片开发。很快,棋盘乡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种、养业比例由61∶39剧变为3∶97.把鱼稻共生和蟹稻共生的面积也算在内,整个棋盘乡的稻田面积还有2.5万亩,占总田地面积的一半。 角湖村村民李六平2002年种植30亩稻谷,2003年开始将大部分土地用来养殖河蟹。20-30亩的面积,在承包土地农户中属于中等水平。他的四口之家三年来经营收支状况见“附表”。 依靠水产养殖,角湖村村民渐渐开始摆脱粮食生产折本经营的境况。“吃穿之外保个本”,是许多村民对自身经营状况的概括。到目前为止,农业生产基本没有剩余。 角湖村村民感受到的好处主要来自负担的减轻。就监利县全县而言,政策性因素增收的3.49亿元中,减负增收的部分是8500万元,占到了近四分之一的比重。 此外,角湖村村民还很快感受到了饲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 这正是监利县委副书记傅先明所说的“三个担心”之一:担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随之上涨,可能抵消农民获得的一部分实惠。 然而,靠种粮无以为继的日子,毕竟已成过去。 在今年的价格和政策带动下,很多农民打算对自己经营的中小规模进行种植结构微调,这个效应累积起来,全县预计早、中、晚每季增加粮食种植面积5万-6万亩。 随着一定程度上规模经营的实现,随着必要的产业结构调整,稻谷在本地农民的收入构成中比重下降,村庄的喘息刚刚平定下来。 棋盘乡的经济水平在监利县处于“中下游”,3.9万人口基本是农业人口,计税土地面积4.7万亩。角湖村人口数量为1290人,计税土地面积1460亩,各项指标在该乡“属于中等”。 土地:突如其来的升温 税费负担从亩均200多元降至45元,而承包价格由一度的40至50元上升到了130元——这组对比关系的变化,显示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土地经营权的含金量在上升。 这与以往形成极鲜明的反差:1999年,李昌平对种粮大户诉苦:“全乡6万亩地,有4万亩包不出去。这是大事,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呀!” 那时找不到人种地,角湖村当时的村支书李先进找到乡里、找到县里,甚至想找中央有关部门,但最终仍无结果——当时粮食太贱,没人要田。 无奈之下,他自己包下100亩,前后亏本1.5万元。2001年,他放弃了承包,离家到株洲做生意至今。但当年的草,成了今日的宝。此时田地成了人人都抢,李先进想回乡重新承包土地,却已无田可分。 桥市镇南唐村会计唐敦贤说:今年有五六个外出打工的村民回来要地种,“一开口就是50亩”。村里打算先把机动地整出来。据唐敦贤估计,回来要地的明年还会增加。 “我们一家老小,现在一分田都没有了。”70多岁的李老汉坐在角湖村杂货店门口,很生气。李老汉儿子全家外出打工,自己在家靠农忙时节帮人出工维持生活。 另一村民对记者说:“他们老两口都70多岁了,儿子外出打工,他有地也没能力种,但包出去就可以赚钱。” 农民纷纷想把土地的经营权,拿回自己手中。“他们看中的,是转包产生的效益。” 正如一家媒体报道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湖北各地实地调研后认为,争地纠纷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的重要问题。 监利县现在最大的种粮大户朱思亮,在三个自然村承包着600亩左右的农田。他不担心别人会分他的田,因为有协议,承包时经过了村民会议和公开决议,对方完全找不出什么“口子”。 村民要地,但地在承包人手里。监利县委副书记傅先明感到头疼,他说:“有些合同是经过司法部门公证的,相当规范,有的签了5年10年,这就很难办。但我们国家有规定:在大的政策调整背景下,合同可以变更甚至终止。还有的承包户已经在土地上投入了不少资金,这个补偿标准该怎么制定?” “接下来我们主要的精力,得放在处理土地纠纷上,”傅先明说,“前不久湖北省专门召开会议,准备采取比较大的动作,主要是重新落实责任田。” 用汴河镇农民吴龙宝的话来说:“现在好多人还在看着,到明年如果价格不跌,地就更俏了。” 像角湖村这样产业结构调整比较彻底的地方,这家挖3亩,那家挖5亩。 打工与回乡的矛盾心理 打工还是回乡种田,这在以前不成问题,但现在却让村民们费思量。 9月这天的角湖村,数村民李开梅家最热闹——十几个乡亲在帮她家拆旧屋、盖新房。新房子的开支是4万余元。这是用十年拾荒生活换来的。 李开梅夫妇1994年离乡前往长沙,“早上不到四点就起来,到晚上八九点,到处捡废旧塑料。拉着板车,不停地走。” 而村民李先汉夫妇则在那里把拾荒者捡来的废旧塑料简单分类,再卖到加工厂。他们在长沙虽然过得不算好——来自角湖村的七户人家容身在三间房里,拉道布帘当屏风——但“每年刨去吃穿,能拿回万把元”。 一年上万的纯利润,当时在农田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当地人眼里,打工在经济收益上的优势是明显的。村里原来有六成的青壮年,经常或者断续在外打工。 但是,现在的村民并不是只有一个选择。由于家里负担重,父亲病弱,打理不了6口人的7亩2分责任田。李先汉夫妻已经不去打工了,而向村里包下30亩地,另外零星地种些蔬菜、养少量黄鳝。他说:“我家这样负担重的不多,父亲头年看病住院一下就是3000元,两个初中生每年6000元。我今年38岁,看来是没机会再出去了。如果这两年能连着这样干,也差不多。” 外面的生活经不起回忆。李先汉说:“那些塑料垃圾很脏,住的地方都发霉,苍蝇蚊子叮着转。倦了,说实话是倦了。” 人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村庄从震荡与窒息中,开始回归平静。 入秋以来,村里却又开始泛起小小的涟漪。要种地的人,多了。 不时地,会有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来“探消息”,乡亲邻居用“蹦蹦车”把他们载到村卫生室门口,在台球桌上一坐,围个圈子拉上一阵家常。 聊的话比从前多了,说外头粮食贵哩,家里稻谷到底能卖个咋样? 今年河蟹和黄鳝的行市咋样?村里还有没有可包的地? 一个村民回来住了几天,带着一肚子气恼和无奈走了。他想回来种地,可是“没有地了”。 几十公里外的汴河镇尹桥村,村民匡春和刚离家几天,他的哥哥还留在家帮农忙。这个庄户汉子肩上扛着打下来的稻谷,笑得很无奈:“春和年纪也有点大了,老在外面干也不合适。可是没办法,向村里要不到地了。” 等这个秋天的农忙过去,匡春和的哥哥也要再次踏上外出的路。 “如果能包上几十亩地,规划好了,再精心点,现在行市不错,也能过得去。农村就这点好——吃粮吃菜不求人。咋说也还是自家好呀,要不是地里实在出不来钱,谁愿意出去?” 在一户人家的大门上,贴着这样一副“两头都好”的对联:“出外求财添富贵,归家创业永兴隆”。 乡镇改革后 经过几次大的政策和经济环境变化,乡镇已经与四年前不一样了。 乡镇干部挤满办公室,月底工资难发的情形曾被媒体多次报道。 下午的秋阳中,某乡政府大院一片静悄悄。 办公区里没有多少人,党委办公室里只坐着主任和另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收音机开着,飘出文艺节目的声音。 在转包压力最大的1999年-2000年,拽着农民的袖子也留不住人,不少乡镇干部只好“带头”当上了名副其实的“种粮大户”。开始他们情绪特别大,但是2002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下半年该乡的土地慢慢开始“走俏”。首先瞅准这个时机的,正是乡镇干部。于是开始出现到外乡承包土地的情况。 适逢税费改革。今年6月,本报曾以《湖北试解“后税费时代”乡镇难题》为题,报道过湖北省今年17号文件所尝试作出的机构改革。这项改革试图对乡镇党政机构进行大幅度撤并,大多数乡镇干部甚至面临着被“买断”干部身份的可能。 “17号文件”无异于悬在他们头顶的一把剑。随着9月26日县委专题会议的召开,“机构配套改革”终于开始推行。 “一是担心岗位,二是担心后路。自己会下岗?分流?还是买断?”一位乡镇干部如此形容自己目前的心境。星期天,他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忙活了整整一天,售粮数万斤。在面对是否打算让出一部分田地的提问时,他毫不犹豫地摇头。“现在我70%的精力都花在那百把亩地上了。” 以棋盘乡为例,乡干部在本乡及其他乡镇承包的土地规模,达5000亩左右。此类现象在其他乡镇也普遍存在。 他们坐在办公室或饭店里,拨打或接听着手机。“喂,喂,那批种子到了是吗?拉进去吧。”事实上,用一位当地观察者的话来说,他们是新一代的“农庄主”。 他们见面后说不上两句话,就马上开始揣测、试探“机构配套改革”的话题。 他们无法平静:“眼下一个月就600元,搞生活都搞不赢。” 他们也承认:“现在不怎么去上班。” 但村民说,乡镇干部不像以前那样收这个费那个费了。 村民也说,乡镇干部不如以前吃香了,人也少了。 乡镇干部扰民的状况已有明显好转,但是乡村公共建设却在现实中遇到不小的难题。 几乎每个乡镇普遍有数千万元财政的债务存量。“好多是前几年转包‘掉税’欠下来的。”监利县每个信用合作社网点门前,都打着大横幅:“严厉打击公职人员逃废信用社贷款行为”。 然而,这些公职人员个人名义的贷款,多半是头几年乡镇干部“满谷满坑”时借出来发工资的。 以棋盘乡为例,用于此类的贷款约有500万元。 1999年,经过角湖村的公路修通了。从那以后村上和乡上都没有增加过什么公共设施。 到2003年为止,整个棋盘乡的债务存量是2000余万元。好在1997年之后,全乡村级债务化解了1200万元。其中以土地承包的形式抵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发烫的粮食流通链条 在粮食价格上升的情况下,粮食流通链条红火得“发烫”。 而在1997年到2000年,监利县汴河镇上的20多家米厂却先后倒了17家。 李德宝在该镇开的米谷加工厂是1995年开起来的,头半年赚了钱,接着就被“套进去”。到2001年,他已积累了十余万元债务。但是好景来得这么快——“几个月来的利好,赚来的已经弥补了大多半损失”。 李德宝说:“今年汴河有300来户在收粮食,往年大约也就几十户。 加上工人、司机什么的,有千把人在忙这事。“ 他们起的是“粮食中介”的作用,是走村串巷从农户手中直接收购,再转手给加工商或更大的购销企业。他们灵活,如果农户缺乏运力,他们就上门收购。 李全有属于农村里“脑子活”的那种人。他开过杂货店,开过小饭馆,卖过水产饲料,开过中巴,什么有利就做什么。他是瞅准今年的行情才进入粮食中介这个行当的。“往年卖30多块40块,100斤也就赚个块把钱、两块钱;今年自然不一样了,愿意下力气搞好的话,能70元收进来75元卖出去。”最小的粮食中介,大约也要实现10万斤以上的流通量。 据监利本地的一些加工商估计:以汴河一个镇的粮管所库存为例,因为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价格上扬,在春粮销售中就有多获利400万元的空间。 政府的托市行为,在客观上要为流通环节的利润支付相当一部分成本。与最终落入农民手中的实惠相比,这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午后,李德宝的米厂来了两辆大卡车,以至于费了不少功夫才转过小村镇路口的弯——这是车主所能弄到的最大的卡车,他急急赶来,是因为沙市一个国有储备粮库已经出到8角钱一斤了。 发烫的粮食流通链条吸入越多的人,市场的主导作用就越强。全国政协委员姚志彬在3月的政协会议上曾提出:国有粮食流通企业也是企业,一样会首先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很可能会囤积粮食,无法在必要的时候对平抑物价起到关键性作用。而政策希望给予农民的利益,会因此而打折扣。 监利县委副书记傅先明说:“今年基层干部和农民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政策能不能持久,全国粮食产量几百个亿的增长,粮多了以后国家还能不能继续保护?由基层埋单的部分还能不能付得起?二是怎么想办法减少流通环节,把利润尽可能集中在农民手里?三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随之上涨,可能抵消农民获得的一部分实惠。” 这几个“担心”,都来源于市场规律。 一位市场研究人员认为:“期货市场不完善,就无法锁定远期价格、控制风险。”姚志彬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尽快建立粮食市场体系期货市场的必要性。他认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惟有藉此才能消除。 有研究者指出:保护粮食生产能力,需要长效机制。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陈锡文接受《光明日报》采访,他的部分观点被概括为:“保护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需要制度创新。” 告别角湖的时候,一户人家的对联映入眼帘:“红日照山亦照水,春风惠我更惠人”。 记者 徐楠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国内财经 > 关注“三农”问题 > 正文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3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