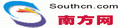|
|
成思危:一个学者型政治家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0日 11:21 南方周末
别了,成思危 卸任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专访 南方周末记者 文平 成思危,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传奇人物,一个叫人难以忘却的参政党领袖,在北京的春天里,退休了。 3月13日下午四点,在北京市朝阳区吉祥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机关大楼,在成思危位于三楼的新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媒体专访。 他的幕僚说,他的办公室原来在四楼,两个多月前他在民建九大上退休,而后执意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继任者,还表示不要办公室彻底回家。经不住旧日同事的劝慰,他搬进了三楼那间小办公室。 依照中国政党制度的规则,他在结束11年民建中央主席使命之后,还要告别全国人大的政治舞台,从担任10年的副委员长高位上卸任。“后天我就离开人大了,新的副委员长就要出现了。”他跟我说,这是自然的事,某种程度上是件高兴的事。就职务对应的责任而言,他愿意我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描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他说话时的淡定和从容,就像说别人的事。 他尊重组织意图。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是非功过任群众评说。回顾他的个人历史,他的荣辱进退的确是组织决定的。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民建会员,从民建中央主席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一步都打上了组织的烙印。 但个人的选择同样不可或缺。16岁那年,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越过罗湖,“投共”到内地,是他自己的选择。“文革”中他和一群来自香港的理想青年受尽屈辱,很多人离开祖国,而他却选择留下。46岁那年,弃化工学管理是他自己的选择,学成后没有留在美国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问他为何会离开父母来到内地,他把自己比喻成巴金《家》中勇敢热情的觉慧,并用我的年轻和他的年轻解释说:你们年轻,不懂得那个大转折的时代。他说,那时候在香港,不少年轻人像他一样,受左翼进步作家的影响,揣着报国情怀,拥抱了新中国。 一时的冲动或许容易理解,难的是虽九死而犹未悔。他的父亲,一代著名报人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大名鼎鼎的开拓者,在和汪精卫的冲突中,说过一句报人没齿难忘的话:“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你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么。”他的母亲萧宗让,留学法国,攻读法国文学,性情温婉。他的四个姐妹都在各自的领域功成名就,如大姐定居法国,曾三次竞选过法国总统。他本来就可过上世俗意义上的体面生活,无需当革命党人改变命运,更不需要遭受生离死别的苦楚。离开香港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与父亲的相见还是28年之后的事。 在一个理想主义变得奇货可居的年代,听他说少年时的理想冲动,看他额头上的老年斑,我似乎感受到理想主义情怀的触手可及,体味到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他“自强不息”四个字。他说,他对这几个字的理解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 逆境时不沉沦,难。“文革”的屈辱岁月中,他烧锅炉时学习锅炉学,无事可做时,自学了几门外语。 南方周末同日报道:
【 新浪财经吧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