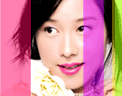张晓晶:经济学须从历史关怀中获得批判力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16日 09:40 新浪财经 |
|
 张晓晶,新浪专栏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中国图书奖。著有《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金融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向为开放、增长与宏观稳定。 1月16日-1月20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张晓晶。----编者按 经济学须从历史关怀中获得批判力 1月16日 星期一 文/张晓晶 在一次网上冲浪中,看到一位国外大投资银行的著名分析师,最近正在研读罗马帝国兴衰史,颇有感触。尽管在吸引眼球的时代,不排除这是一种炒作,但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并且对这位分析师表示敬意。毕竟,在一个从理想到行动都越来越短期化的时代,对于以跟踪宏观经济为己任、为格林斯潘们的举手投足或神魂颠倒或惊惶失措的分析师们而言,捕捉市场的瞬息万变才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至多只是他们紧张生活的外衣上一件奢侈但并无多少实用价值的配饰。 分析师或许是一个极端。然而,对现实问题分析的短期化,却因为凯恩斯的名言“长期而言,我们都将死去”,似乎一下子获得了合法性的依据,变本加厉地普及起来。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在1945年之后,大规模的、长时期的社会变化问题已经从学者的视野中排除出去了。摇滚歌手们更是直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面对这样的世界,分析的短期化似乎是一种必然与无奈。然而“短期在所有的时段中是最多变的,也是最有欺骗性的”(布罗代尔语)。注重当下,缺少历史透视,必然导致对现实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经济分析中的短期化倾向,正在丧失它应有的解释力、说服力与批判力,并且导致对经济生活中“真正问题”的忽视。 写到这里,一定会有人马上站起来反驳,认为我的说法太片面,或者是孤陋寡闻,因为经济学里有的是长期分析呀。的确,现代增长理论的出现,就是对于此前短期分析的一种“校正”,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增长理论也正是在凯恩斯短期分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增长理论的出现,复兴了经济学关注长期的情怀。而这一复兴显然与历史关怀有关。 人类历史从最早期直到19世纪初左右,世界人口以及商品服务的产出量(或者以现代流行的GDP来衡量),均以大致不变的速度缓慢增长。18世纪欧洲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准与同时代的中国人或古罗马人差不多。然而在最近的200年中,世界人口和产出的增长都急剧上升,其中产出的增长要远快于人口的增长,于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第一次开始持续提高,从根本上突破了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在新增长理论奠基者之一的小罗伯特•卢卡斯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并且,正是这样的一个发现,使得关注增长问题比任何其它问题都变得更为重要。只要一想到增长问题,其它问题就都靠边站了。这和凯恩斯那句名言有点针锋相对的味道。也正因为如此,宏观经济学就不再只有短期宏观稳定分析,而是开篇即从增长讲起了。 卢卡斯曾经是学历史的,他的理论充满着历史关怀。比如,他通过工业革命以及20世纪下半叶的研究,对于二十二世纪的人类作了大胆预言:工业革命在两个世纪中以令人惊异的方式推翻了这些导致平等的力量(即在工业革命前,人们的生活水平差不多。笔者注):这就是我们称其为“革命”的原因。但这些力量在20世纪下半叶卷土重来,我认为各社会之间收入恢复平等将是未来世纪中的重要经济事件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工业革命。在1800年所有社会都处于相同的贫困和萧条中;如果到了2100年,我们处于相同的富裕和增长中,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原地踏步! 历史的透视,让卢卡斯的研究一直处在高屋建瓴的位置,其研究的恢宏大气可见一斑。 尽管新增长理论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历史关怀,但是,当它沉浸在理论想象中的时候,形式化(formalization)的努力就逐步将现实的复杂性与历史关怀抽象成诸如内生技术进步等几个简单的变量了。在模型越来越精致、形式越来越漂亮、变量越来越多地被内生化的过程中,新增长理论还能找到当初那种历史关怀的冲动么? 二战以来,直到19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历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所谓“黄金时代”;而从70年代初直到90年代中后期美国新经济的兴起,这中间,整个西方经济就陷入了一个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衰退或者说缓慢增长。 东亚一些国家在20世纪末的那场危机前也保持了长达30年(有的甚至超过30年)的高速增长,但1997年遭遇了金融危机。尽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现实的理由来解释金融危机的爆发(比如制度不完善情况下过早的金融开放、经济结构的问题、投资高增长而TFP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东亚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段的高增长周期,积累了一大堆问题,必然会遭遇这么一场危机呢?事实上,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就强调了市场经济本身会不断积累问题,然后以危机的形势爆发出来。资本主义经济正是以这种消极而极具破坏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继续前进”。 再看中国,已经保持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9.4%(GDP调整以后,这个数字会更高)。我们仍然希望有下一个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增长。不过,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会遇到周期问题,在下一个20年是否会出现经济增长的放缓。实际上,当我们把未来20年的增长目标设定为7%的时候,按我的理解,这就是对于经济增长自身规律的一种认识和运用。不过,现在看来, 7%的增长速度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雄心。 以上的现象或问题,不能说没有人涉及,不过,无论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也好(强调技术冲击),新增长理论也好(强调内生技术推动),都没能给予足够的关注,甚至可以说是把这些问题给忽略了。缺少了历史关怀冲动的“技术决定论”,能够解释复杂的经济世界和历史发展吗?或许,问题还不在于答案本身,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去寻找这个答案。罗伯特•索洛认为,经济学并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以它对世界运行方式的量化理解那样累积起来。那些黄皮的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工作论文就说明了这一点,它们从未解决任何问题。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它们都与研究经济学的方式及其问题的性质有关。 作为NBER论文的忠实读者,看到索老先生这样愤愤不平未免偏激的评论,颇觉震惊,很受打击。但我想这并不会影响我对NBER论文的跟踪阅读。只是,我需要关注,它们是不是只追求漂亮的逻辑形式,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或者,我们的经济学真的丢失了什么。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经济学(家)应不应讲道德争得不亦乐乎,这实际上涉及到所谓“立场”问题;最近又出现“穷人经济学”、“富人经济学”之争,也是关乎“阶级感情”。所有这些,不过是说,经济学不应是冷漠的,经济学需要道德关怀。而我在这里呼吁的,是经济学更需要历史关怀。这不是指经济学要强化对历史的研究(如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更不是要挑战历史,而是强调在经济分析中要有历史眼光、历史透视。没有历史,就无法理解现实,更无法预知我们的未来。很多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透视中才变得明晰起来。 比如“新经济”,并没有像一些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打破了经济规律(经济周期),只不过是使经济周期暂时换了一个面貌。回顾一下工业革命以来的种种重大发明创造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变革,或许我们更能理解,所谓“新经济”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曾出现过。 再如华盛顿共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它不过是发展经济学思潮中的一支而已。华盛顿共识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比此前的激进主义、结构主义或新古典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更少,相反,可能更多。对于华盛顿共识,老朋友胡永泰(Wing Thye Woo)教授称之为一种“会计方式”。他认为,华盛顿共识关注的只是产出、价格以及国际收支在中短期的稳定,却没有关注长期的可持续增长。这是一种会计方式,不去考虑各国的不同特质。因为会计报表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尽管产生同样结果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 今天的金融全球化,很容易让人想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情景。当时也是金融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象著名的如维克塞尔、希法亭、凡勃伦等(当然还有列宁),都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出当时经济社会的急剧变迁,特别是金融的“浮出水面”以及金融大发展对原有经济运行方式的挑战。毋庸置疑,今天的金融全球化无论在规模、程度与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当时,不过,有一样东西始终未变,那就是,资本在不断寻求新的积累模式。 历史关怀可以让经济学更加贴近我们的现实世界,解释我们何从来、何处去,就如高更的那幅名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所要表达的那样。历史关怀,可以让经济学分析不囿于就事论事,不会在形式化过程中抽象掉问题的历史本质。 记得黑格尔说过一句话: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恩格斯说,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历史关怀,能使经济学不仅仅停留在描述、理解与顺应现实,而是在历史的透视中去获得批判的精神和变革的勇气。一直记得是在当年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知道了经济学的批判力,也知道了什么是“庸俗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更注重其建设性,把批判性丢在了一边。以我的陋见,失去批判性的经济学,其建设性也将是非常有限的。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评议学人 > 正文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市黑马:今日牛股! |
| 做女人事业,赚女人钱 |
| 06年暴利项目揭秘 图 |
| 网络招商首次揭秘 |
| 2006年最赚钱的行业 |
| 年薪百万的财富之路 |
| 360行赚钱惊天内幕 |
| 二折提货,千元做老板 |
| 2006药界金矿招商指南 |
| 泌尿顽疾——大解放! |
| 最新疗法治结肠炎!! |
| 治气管炎哮喘重大突破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治高血压获重大突破! |
| 高血脂!脂肪肝请留意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6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