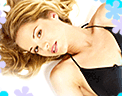秦晖:切实保障农民地权 发展乡村社会民间组织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03日 17:15 《财经时报》 | |||||||||
|
地权是农民公民权益的最低保障,但不是农村社保的药方。应发展乡村社会民间组织,以民间组织的合作、互助保障,弥补政府保障之不足 秦晖 土地权是多层次的,到底哪些层次的权利应归农户,哪些归社区(集体),哪些归国家
当前地权政策的主导方向应当是切实保障农民的地权,不一定是“所有权”,但至少是现行政策已允许给予的那些层次的权利。 地权:农民公民权的“底线” 在当前条件下侵犯农民的公民权益,往往是通过侵犯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表现出来的,因而保障农民地权不受侵犯是维护农民公民权的一个重要“底线”。在这个意义上,地权与其说是“最低福利保障”不如说是“最低权利保障”。如果农民签订的承包合同可以被权势者随意撕毁,农民可以被随意赶出他们享有合法权利的那块土地,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目前我国的公民保障机制并不健全,公共权力的运作机制不够规范,尤其农民更是权利易受侵犯的弱势群体,我国目前推行的村民民主自治计划的提法本身,也表明了乡村民主仍在建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给农民的公民权设置一些保障的“底线”,划定一些行政权力不宜进入的领域,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以牺牲一部分“土地配置最优化”效益为代价也是值得的、利大于弊的。 而以所谓规模效益为理由来侵犯农民权利则必须避免。如果扩大干预农民地权确属必要,也应当在公共权力运作机制改革后、在法治状态下再来考虑这类问题。 此外,尽管保障农民地权未必会导致农地资源配置的优化,但它在经济上仍有正面作用。如受保障的地权可以作为抵押,有利于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弥补如今日益突出的乡村金融服务真空等等。 把推动农业规模经营作为变革土地制度的目的是不合适的。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农地配置优化,或者说农地规模经营的主要限制条件在于,农民非农化就业前景不明。这一前景如果没有很大的扩展,无论什么样的规模经营都不可能有多少发展空间,不管是通过土地“私有化”以市场方式搞规模经营,还是通过“反私有化”以行政方式搞规模经营。 驳斥“土地保障论” 目前条件下我国多数农区农业经营的不经济,已使土地丧失了产生“农业利润”的资本功能,而成为一种生存保障手段。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农民可以用自己耕作的份地为自己提供“保障”,“社会”要做的只是行使权力禁止农民自由处置份地、削减农民持有份地的年限、强制农民承担“保障”自己的义务。把“社会保障”不是看作政府的义务、公民的权利,而是看作政府的权力、公民的义务,这是一种颠倒的看法。这等于是政府让农户自己保障自己。 在社会无法承担“社会保障”义务的情况下,农民依靠自己的土地维持生存是很自然的。问题是,这些土地真能提供“保障”吗?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农民流离失所、形成流民群乃至发生“农民战争”都是因为没有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保障”。事实上,历代农民战争发生时的社会危机中,常见的并不是很多农民无法获得土地,而是相反的情景:沉重的负担、恶劣的吏治以及种种天灾人祸使农民有地不种、弃地而逃。 今天,在东部富裕地区农民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不太依靠土地(土地在这里更多是资本),而西部贫困地区,土地也无法提供社会保障,土地在这里更多地成了负担。换言之,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无论现实中的富裕地区还是贫困地区,“土地社会保障论”都是难以成立的。 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是某种社会组织的事,而不是某种要素的事,因而“国家保障”与“土地保障”并不构成一种并列的选择关系。国家(政府)财政如果无法承担保障义务,替代的选择可能是社区、企业、家族、教会、非盈利组织等等来承担这一义务,而绝不可能是“土地”来承担,正如不可能是“资金”、“劳力”来承担一样。 我国如今仍然是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一样还比较低,社会保障网尚不能惠及多数农民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并不丢人,而如果自欺欺人地把事情说成是:我们没有“国家福利”,但有“土地福利”,却有可能使人误以为我们的农民已有了“另一类型”的社会保障,从而取消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 同时,从上述社会保障的定义也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乏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有关,更与社会组织资源的贫乏有关。官办的组织无力或无法提供社会保障(即所谓国家保障缺乏),民间的组织又没有,无怪乎只有“土地保障”即农户自我保障了。 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要靠发展经济增加财政实力,同时要以开明的态度鼓励乡村社会各种民间组织,以民间组织合作、互助弥补政府保障不足。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经济学人 > 经济学人--秦晖 > 正文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12月大黑马免费送!! |
| 投资3万元年利100万! |
| 美国保佳教您赚百万! |
| 中国1000个赚钱好项目 |
| 开男士品牌名店赚疯了 |
| 名品服饰 一折供货 |
| 肾病、尿毒症怎么办? |
| 特色治失眠抑郁精神病 |
| 瑜珈美容俱乐部太赚钱 |
| 高血压治疗上的飞跃! |
| 开个咖啡店赚了几百万 |
| 拯救男人,还你健康! |
| 法国美容 浪漫赚钱! |
| 好男人更强,更自信! |
|
|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