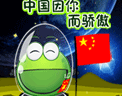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
本刊记者 张志峰 李 霞
7月22日,中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位孜孜不倦的开拓者——薛暮桥永远停止了思考。这对于毕生都倾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践、研究与写作的他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因为薛暮桥的生命轨迹是与中国经济曲线拧合在一起的,而晚年严重的帕金森症已使他无力继续这一生的事业。
薛暮桥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跨越了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由于他始终身处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线,可以说,他的思想体系是在实践中逐渐完善的。薛暮桥又是一个十分超脱的人,尽管始终从事具体的经济工作,但他的理论研究却从不被身边的环境所羁绊。曾是薛暮桥秘书、现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的李克穆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评价说:“薛老是一个求真务实的经济学家,他从不会为站不住脚的结论而自圆其说,他始终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得出结论。”
薛暮桥平静地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长期执著的探索精神,以及淡泊名利、坚持真理的大师风范永远为我们铭记。在改革步入到攻坚阶段,每一项决策的做出都需经过各种利益集团博弈,一系列市场取向的观点都面临巨大压力的大环境下,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的精神和风范显得弥足珍贵。
身陷牢笼志更坚 一代大师初长成
薛暮桥(原名薛与龄)的一生都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给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和研究,而他的这种理想和信念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扎根于心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还未满15岁的薛暮桥就跟随高年级学生上街游行演讲。暑假期间,又与几个同学创办了一张油印小报,每期发表几篇批评列强、军阀,宣传爱国救国的文章,提倡抵制日货等。每份报纸售价一个铜元,销路很好。有了收入,再买纸出下一期,就这样坚持办了一个暑假。“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薛暮桥开始阅读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革命思想的火花闪耀在他还略显稚嫩的心灵中。1927年初,薛暮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时,人生的命运往往被一个关键的人、一件关键的事所改变。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当时任中共杭州区委工人部长的薛暮桥与其他几位工会领导人一起被捕入狱。在狱中,他遇见了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张秋人,张秋人自知必死,但每天仍要读书五六个小时。在临刑前对薛暮桥说:“共产党员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读书就是为着革命。”这几句话对薛暮桥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教诲,他的一生从此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坚定的信念。
薛暮桥开始了狱中的学习生活,他在艰苦的环境中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同时还刻苦地学习了英文和世界语。三年半的狱中生活,使他获得了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这为他以后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9年,薛老访美时,一位美国教授问他毕业于哪所高等学府,薛老诙谐地回答:“我毕业于旧中国的牢狱大学。”李克穆告诉记者:“薛老的学习动力完全源于强烈的求知欲望,在狱中这三年的苦读对他的成长相当重要。”
薛暮桥在狱中的学习积累很快派上了用场,出狱后不久,他与孙冶方、钱俊瑞等人一起在共产国际党员、历史学教授陈翰笙指导下,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1933年,陈翰笙推荐薛暮桥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任“农村经济”教员。薛暮桥说我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怎能到大学去教书?陈翰笙说不要紧,我为你假造一个履历,为此薛老将名字从“与龄”改为“暮桥”。薛暮桥到广西后不久立刻发电报回来说:不好,如果按照履历上的介绍,我和这里的校长就是同班同学了,要穿帮。陈翰笙说没关系,你和校长说是我推荐的就行了,“牢狱大学”毕业的薛暮桥开始在正规大学任教。而关于“暮桥”二字的由来,还有一个小故事。在1958年春节期间,毛主席有一次和薛老闲谈,问他“暮桥”二字出自何处,薛老回答说,“暮桥”的名字是陈翰笙因革命工作需要为他起的。主席听后随口吟出了陆游的两句诗:“朝发云根寺,暮宿烟际桥。”然后说:“陈翰笙喜欢陆游的诗,大概是用的这个典。”关于“薛暮桥”名字的由来,薛老夫人罗琼曾经讲到:30年代初,陈翰笙推荐刚出狱不久、处境困难的薛老到广西的一所大学去讲授经济学,他自己政治处境也很困难,不久便出国了。当时陈翰笙说过:“末路穷途,有桥可渡。”暮桥二字应源于此。
就这样,薛暮桥开始走上了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之路。当时,薛暮桥是《中国农村》月刊主编,《中国农村》月刊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从事有系统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活动的重要阵地。薛暮桥在《中国农村》上发表了大量论文,证明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薛暮桥的经济学思想日趋成熟。新四军建军之初,薛暮桥受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之邀,参加筹建新四军教导总队,并主持政治教育工作。他利用行军的间歇期间,在膝盖上写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政治经济学》两本教科书。这两本书成了新四军抗大学员的教材,在革命人士中广为流传。李克穆说:“如今很多老同志都说他们是薛老的学生,因为他们读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出自薛老之手。”
敌后抗日施巧计 小小货币立大功
1943年,薛暮桥在奉命去延安的途中,被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留在了山东解放区,协助进行对敌货币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在没有硝烟的经济战场上也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更能感受到当时对敌斗争的艰辛、体验到薛暮桥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济学家的坚韧与智慧。
早在1938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就自己发行货币,称作“抗币”,作为“国民政府”规定银行发行的钞票——“法币”的辅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其占领区排挤法币,造成法币币值大跌,物价猛升。那时,山东分局和省政府不了解货币和物价规律,仍允许法币在市场上流通,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与抗币的比价。但由于法币能在全国流通,抗币只能在根据地流通,人民乐于收藏法币,黑市上法币的币值反而高于抗币。日本扶植的伪政府所发行的伪币,可以禁止流通。但在敌占区的黑市上,伪币币值又高于法币。在游击区,三种货币同时流通,伪币币值最高,法币次之,抗币最低。
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劣势?薛暮桥大胆地提出,要稳定根据地的币值、物价,惟一的办法只有驱逐法币,使抗币能够独占市场。山东分局和省政府于1943年6月初在报纸上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使用法币,动员人民把法币兑换成抗币,或到敌占区换回物资。消息一公布,市场上法币立即下跌。排挤法币使根据地换回大量物资,能够用于支持抗币,在物价上涨时抛出物资,回笼货币,提高抗币的币值,物价就自然回落。
驱逐法币后,由于抗币的流通数量满足不了市场流通的需要,物价从稳定趋向下落。薛暮桥指出物价上升是坏事,物价大幅下跌也是坏事,报告分局应当增加抗币,大量收购农产品,制止物价下落。就这样,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而是用物资来作储备。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
根据地内可以停用法币,但对敌占区的贸易仍然要用法币、伪币,因此,必须明确它们同抗币适当的兑换比率。起初,根据地与敌占区接壤的银行往往强压法币、伪币的比率,引起贸易入超,法币、伪币供不应求,比率回升。薛暮桥建议要按根据地和敌占区物价的变化和各种货币的供求情况,来灵活规定兑换比率。抗币与法伪币的比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的入超与出超。1942年前为保护物资,根据地盲目禁止土产品出口,引起入超。后来改为鼓励有多余的土产出口,主要协助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以减少日军扫荡时的损失。
当时山东丰富的出口资源主要是海盐和花生油,这是上海人民的必需品。薛暮桥建议食盐由工商局专卖,这样对外贸易出超,法币、伪币供过于求,它们对抗币的比率可以完全由边缘地区的银行和工商局操纵,更有利于保持根据地的物价稳定。花生油也由工商局收购,以私商身份运到上海销售,换回军需民用的重要工业品。上海日军也知道这些花生油来自山东抗日根据地,但因市场必需,暗中保护。根据地印钞票用的纸张、器材和部分军用物资,都是用出口花生油的收入从上海采购来的。
薛暮桥在后来总结这段经济工作的宝贵经验是:提出货币斗争、贸易管理、生产建设三大任务,从货币斗争入手,并用贸易管理支持货币斗争。只有首先争取货币斗争胜利,完成停法(币)禁伪(币)的工作,保护物资,稳定物价,克服经济危机,才能进而谈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可以说,如果不是货币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经济将受到很大的损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国有个经济学家来山东访问,问薛暮桥山东的货币既无金银作储备,又无外汇作储备,为何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薛暮桥回答说我们有物资作储备,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薛暮桥还告诉他,在实行纸币制度以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流通数量。我们的物价相对稳定,原因是我们适当控制货币流通数量。这个道理现在已经是经济学常识,但当时欧美各国还保持金本位制,这个货币理论似乎还是创见。这位经济学家问薛暮桥美国能不能实行这样的货币制度,薛暮桥说美国现在掌握着世界三分之二的黄金,还可以实行金本位制。而薛暮桥万万料想不到,这次谈话的30年后美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来稳定物价,并因此产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央把薛老调到西柏坡,协助周恩来处理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工作。周恩来习惯于晚间办公,规定处理财经、后勤工作的时间是晚上10点至次晨2点。于是,薛暮桥每天晚上都要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处理日常工作。当时国民党报纸上有一句话:周恩来手下有两个人,一个负责发炮弹,一个负责发货币。“负责发炮弹”指的是军委总后勤部长杨立三,而“负责发货币”指的就是薛暮桥。
求真务实屡建功 超脱淡泊看人生
在建国后的四十年中,薛暮桥先后担任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等重要领导职务。
虽然薛暮桥一直身担要职,但李克穆告诉记者:“薛老是一个相当淡泊超脱的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开始给干部定职定位,给那些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干部委以重任。当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的薛暮桥,却做出与众不同的举动。由于长期工作劳累,薛老在1951年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为此,他向中央提出自己身体不好,要求辞去中财委秘书长等职务,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理论研究。薛老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尘俗,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诗句贴切的表达了薛老超凡脱俗的心境。
像薛暮桥这样难得的经济人才,中央难以同意他专做研究,不担任领导工作。此后,政务院任命薛暮桥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就是在这个岗位上,薛老开创了新中国的统计事业。李克穆说:“薛老在对待名利上非常超脱,但在工作中却十分务实,他从事经济理论研究都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薛暮桥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60年代他主持建立了我国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为成功地调整物价,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70年代末他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鼓励长途贩运,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
“薛老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特别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若干建议,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薛老对于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从不随风而变,这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很难做到的。最值得钦佩的是,当时代或实践证明他的一些观点有问题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去修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汲取新的知识,更新自己的观念,使薛老的理论观点始终站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前列。”李克穆评价说。
李克穆至今还记得薛老和钱学森的一次讨论。有一次中央开会,钱学森找到薛老,说:改革开放了,经济研究应该运用数学模型。薛老说:“很好,但一定不要搞成‘数字游戏’。如果输入计算机的数据不准确,得出的结论就有问题,因为计算机缺乏‘测谎功能’”。对此,钱学森也十分赞成。当时,李克穆随手在一份《人民日报》的空白处,把这段对话记录下来。后来,《半月谈》杂志把这两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巨匠之间的对话刊登出去。尽管这番对话的原始记录已经难觅踪影,但类似的讨论如今仍在持续。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老一辈学者对国家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而让李克穆感触最深的还是薛老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所做的细致入微的调查工作。印数达1000万册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就是薛老去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区作了深入调研写成的。李克穆开玩笑对记者说:“我和薛老一起出去调研很有压力,他在研究问题时太专注,有时眼睛一直盯着某个事物,脚还在移动,我得随时保护。”
薛老有一个十分和睦的家庭,他与夫人罗琼相识在上世纪30年代进行农村经济调查时期,1935年结为伴侣。罗琼长期从事妇女工作,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一书记等职。他们有三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女儿薛小和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并继承了父亲研究经济问题和善于写作的才能。
薛老在晚年仍然笔耕不辍,曾有记者问薛老如此高龄,为何还每天坚持长时间写作时。薛老的回答很简洁:“如果我不写作,不思考经济发展问题,那么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