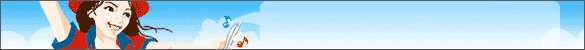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
周其仁
作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邮箱:zhouqiren2005@yahoo.com.cn
五年前参加一个座谈会,主事人问:多年来,税收增长比GDP增长快很多,究竟什么原因?问题明了,但自己一直没有答案。不久前讨论土地制度,正听人论证物业税之时,突然就“看到了”一个理由——政府闻税则喜,而各路专家提供了源源不断增税的根据。
倘若税制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机构决定,那么政府的偏好和专家的理由,都不能直接推动税收增长过快。但当下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税收项目的出台和税率的确定,基本由政府决定。这样,闻税则喜的政府偏好,加上善于论证加税必要性的专家系统,珠联璧合,就足以推高税量、增加税种了。
难怪有关税收的学问源远流长。古代中国的传统,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都是“王土”,大家就要缴付租金——“租税合一”是也。这也许是由于那时的市场经济蛮有基础,民间买卖租赁关系发达,说黎民百姓“租用”国家公器必须缴付租金,非常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统治者贵为天子,接受各方的“上贡”是天然的秩序。讲来讲去,传统中国的税,无非是租金与贡献的合并。
启蒙时代后的西方,不再接受基于“君权神授”的理由。1776年《国富论》的第五编——熊彼特称之为“一篇自成体系的财政学论文,后来成了19世纪所有财政学论著的基础”——题目是“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却先从“君主或国家的支出”谈起。原来,斯密心目中国家收入的合法性,是由国家承担公共职能——国防、司法、为便利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等——所必要的开支来界定的。为什么人民要缴税?就是为了购买国家的公共服务。
这就是说,税也是一个“价”——政府提供服务之价。所谓“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要点不是宣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那是因时势变而变的——而是在任何时代都要谨慎地比较不同途径获得公共服务的效用差别。试举一例,为了国防和司法,国家非合法拥有武力不可。但是常备军好还是民兵好?猜猜斯密的答案是什么?常备军。理由是常备军更经济!
这种朴素的税收理由后来“退位”了。新的时髦是剑桥大学庇古教授的福利经济学。这门学问可以搞得很复杂,但基础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享受私家车的舒服,却把废气排在空气里,那他的驾车行为就有了“负外部性”,或者就是他开车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一致”。这时,由于这位仁兄无须为他的驾车享受支付全部代价,其“需求”失去有效的成本约束而膨胀,后果——空气污染——必定格外严重。
在庇古看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市场无法做到使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市场失败”是也,解决之道呢?征收空气污染税吧。后来的文献上甚至把这类税命名为“庇古税”!是的,哪里找不到外部性?从邻居的狗叫到太空垃圾,从道路拥挤到大海捕鱼。从此,只要懂得“庇古税”的各种变型,任何一个立志改造社会的人都容易如愿以偿。
更后来流行的就是关于税的“社会观点”,即把税收广泛地用于矫正各种社会问题的观点。据说这种学说起源德国,我自己知之不多,希望熟悉的读者有以教我。不过很多现代的税种——诸如高额累进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奢侈消费税等等,让我们不难看到“社会观点”的强大影响。
与凯恩斯的名字挂在一起的,是宏观调控产生的税收需要——至于凯恩斯本人究竟说的是什么,好像并不重要。简言之,过热时加税,过冷时减税,经济气温不就得到调节和控制了吗?与此类似,对需要优先发展的产品、行业、部门、地区给予税收优惠,反之则反之,就是“产业政策”需要税收的理由了。
我们远远没有穷举税收的专家理由。即便如此,读者已经可以看到古今中外关于收税的专家理由实在蔚为大观。事实上,不少税种是被逼出来的,其理由也是被逼出来的。比如香港至今还在征收的酒店房间税,据说是1965-67年由港英政府财政司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决定开征的。郭当时的理由特别令人欣赏:政府大力推介香港旅游业,酒店的得益多于其他行当,要不特别抽一下酒店的税,对其他产业不公道!
近年我们在本土听到的加税理由,倒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先有专家别出心裁地把税收占GDP比重的高低,定义为“国家能力”。就是说,有本事加税就表明国家能力的强大。粗看起来,这像一个自我循环证明的命题,进一步推敲其中包含某种概念上的混淆。不过,这都是小节。哪一个爱国公民会不赞成增强国家能力呢?那就加税吧。
最近的例证,是运用税收调控经济达到进退自如的境地。一方面,诸多专家论证利率和汇率皆不可轻动——或者动了也无用;另外一方面,加税停税闹得市场中人无所适从。坚守汇率不变而开征纺织品出口税,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建议,政府礼贤“下士”,决定开征;不料欧美国家仍然要搞什么特保之类,最后还是商务部长宣布取消尚未开征的纺织品出口税。物业税和财产税,是几位香港教授的热门话题——顺便说一句,近年大行其道的“卖地财政”,也来自我们的东方之珠。政府卖地收入,也是税赋。
这么说吧,无论出于学说的推理,或者是糅合各家之言,还是逼出来的急就章,反正政府要抽任何一种税,都不难找到“证明合理的理由”。政府本来有权强制收税,行政主导的税制少受节制,而各方专家可以证明开征任何税种的理由——齐了,形成一个“万税”经济似乎易如反掌。
危险就在这个地方。数之不尽的证明抽税必要、合理的理由加到一起,可能加总出一个谁在事先也没有“计划”过的局面:税收总量过大,政府承诺过多、开支过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销蚀人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意志;税种过于复杂,征税成本高,则刺激腐败和寻租活动。转来转去,事与愿违、南辕北辙而又不能自拔,岂不糟糕?
解决办法当然不是抽取“累进的加税建议税”。我认为可取的办法,要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机构来决定最高税负量,然后在税收总量的限度内,开放税收专家意见之间的竞争。建议增加任何一种税吗?先问总税量还有没有“房间”。如果没了,那就先回答,你建议哪一项现存的税收取消或减少?
|